李長聲: 面臨滅亡的,何止方言
關於語言的瀕危,我們想到的往往是土語方言,但日本女作家水村美苗擔憂一國的語言——日語也面臨滅亡的危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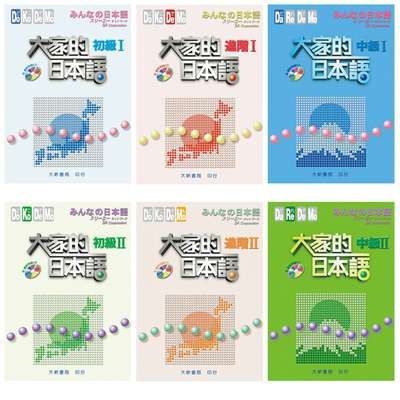
2008年她出版一本書,那年是“國際語言年”,書名叫《日語滅亡時》。自稱隨筆,但內容堪比論著,主題是英語這種“普遍語”的意義是什麼,面對其力量,怎麼樣才能保護日語作為“國語”充當優秀的書寫語言。當時有人説此書“是現在所有日本人都應該讀的書”,我非日本人,偏巧在日本,所以也讀了,覺得確實有意思。
日前逛書店遇見2015年出版的文庫版,書名多了“增補”二字,隨手買回來。所謂增補,幾乎只增補了一篇長跋,絮叨些出版英譯本的問題。至於不加修改,理由似乎也足以服人,那就是出版後引起論爭,若加以修改,讀者就奇怪當年爭什麼爭啊。不過,這理由的底下潛藏著作者對己見的堅持與驕傲,甚至都不想淡化被譏為對當代日本文學不懷好意的印象。好書重讀,自然又獲益。
水村美苗提出了三個概念:普遍語、現地語、國語。
她説,人類大部分場合並不是用自己説的話直接讀寫,而是用“外來語言”——覆蓋那一帶的、古已有之的、偉大文明的語言來讀寫。地球上到處有一些這類文明語言,她稱之為普遍語。不論用什麼樣的語言説話,如果住在地球上的所有人用一種書寫語言來讀寫,那麼,人類的睿智就能最有效地積累。普遍語最本質地表現了書寫語言與説話語言的不同。例如日本近代以前千餘年使用東亞的普遍語——漢文,這是“追求睿智的人”用於讀寫的語言。
與普遍語相對的概念是現地語。現地語以口語俗語為主,在那個地方通行,一般是人們的母語(日語有“母國語”一詞,多一個“國”字,用在這裏不準確,除非理解為川端康成的名句“穿過國境的長隧道就是雪國,夜的底下變白了”的“國”)。現地語也可以書寫,但寫起來宂長,擴散範圍有限。
近代以前日本沒有國語。奈良朝宮廷、貴族、文化人使用漢文。平安朝初期創出假名,日本便有了兩種書寫語言。假名又叫女文字,男人也用它給女人寫和歌調情,但辦公、社交完全用漢文漢詩。在德川家康開立的江戶時代,學問即漢學,漢學即學問。語言與教養為三層結構,上層的知識階級即“追求睿智的人”用純正的漢文即普遍語讀寫,中層公務員用近乎洋涇浜的變體漢文——“候文”供職辦公,下層的民眾用土語方言説話做事過日子。
漢文最具權威性,《源氏物語》不被文化人看在眼裏。松尾芭蕉響噹噹代表江戶文學,這是輸入了西方觀念以後才形成的文學史觀。重看歷史,變成以日語寫作為中心,從《源氏物語》《古今和歌集》到松尾芭蕉、井原西鶴成為文學史主流。常説江戶時代識字率很高,婦孺皆識,但他們識的是假名,並不是漢字。很多農民請主子或教書先生給自己起了姓甚名誰,卻不認識那漢字的大號。歷史小説家司馬遼太郎懸想:明治維新時志士們各操各地的現地語,交流需要用漢文“筆談”。高杉晉作到上海考察鴉片戰爭以後的中國,靠的是“筆談”。孫中山也是用“筆談”和宮崎滔天等日本友人交往。公文自古是漢文,破天荒使用現地語書寫語言是1868年改元明治之前發佈的《五條誓文》。日語由漢字和假名混搭而成,核心是漢字。昭和天皇的停戰詔書用現地語,但其中漢文難解,聽他宣讀以為在號召全民玉碎呢,卻原來一舉瓦全。日本戰敗,被美軍佔領,漢文的餘威消失殆盡。
國語不是自然所賜,而是人工的產物。作為made in Japan,國語怎樣造出來的呢?按照水村的説法:“追求睿智的人”翻譯普遍語,使原來只是現地語的語言具有了和普遍語同樣的水平,不僅審美上,而且智力上、倫理上都擔起達到最高水平的重任。這種語言和國民國家誕生的歷史交織,成為國民國家的國民語言,這就是國語。所謂追求睿智的人是“二重語言者”,不是會説雙語(bilingual),而是能閲讀和自己的説話語言不同的外語。從歷史來看,翻譯並不是對稱的行為,水往低處流,從普遍語向現地語搬運睿智。日語在翻譯普遍語——漢文的過程中產生了書寫語言,但沒有成為國語,始終屬於現地語。
福澤諭吉是日本向近代轉變的象徵,而夏目漱石在國民國家成立時,簡直像魔法,象徵其歷史過程於一身。他們是“追求睿智的人”,對打造國語起到了巨大的歷史性作用。但國語建立也多難,出於民族及文化的劣等感,明治維新後第一任掌管教育的文部大臣森有禮曾主張用英語當國語,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敗後,以日語文章被譽為“小説之神”的志賀直哉提倡用法語取代日語,雖然他不懂法語。1950年被稱作“憲政之神”、“議會政治之父”的尾崎行雄也提倡用英語當國語。此公號咢堂,上過福澤諭吉創辦的慶應義塾,呼之為先生,在《咢堂自傳》中寫道:“那時先生一邊用鑷子拔鼻毛,一邊用古怪的眼神斜視我的臉,問道:著述什麼的打算給誰讀呀?我不高興他那種態度和用詞,但壓住怒氣,一本正經地回答:為了給一般有見識的人看。先生便訓斥:你這呆子!要寫給猴子看!我寫總是抱著給猴子看的念頭寫,世上這就正好。還做出誘人似的笑。”福澤諭吉寫《勸學》,文體平易,在三千萬人口的日本賣掉三百萬冊,應該用的就是這種“給猴子看的念頭”。
福澤諭吉自學英語,夏目漱石大學讀英語專業,作為二重語言者,他們製造了一些西方語言的譯詞,如演説、贊成、討論、版權、浪漫等。與夏目漱石並稱文豪的森鷗外也是造詞兒的高手,造出了空想、民謠、長篇小説、短篇小説等。常聽説,現代中國語七成是日本製,甚至説“沒有近代日語,就沒有現代中文”。然而,在此話之前,似乎應該説“沒有漢文,就沒有近代日語”。有兩點也值得一提,以免太滅了自家的志氣。
一是譯詞的方法,這是跟中國學的。先有“地球、幾何、對數、顯微鏡”等中國譯詞的傳入,然後才有日本人源源不斷的仿製。日語研究家陳力衞教授揭示:“通過中文的書籍和英華字典來汲取西方知識是日本近代化進程中的捷徑之一,這是因為日本知識分子一般都通漢文,而當時能直接讀懂英文的人又少,魏源的《海國圖志》、傳教士等用中文寫成的介紹西方文化歷史地理知識的書籍便成了他們的必讀之作。於是乎,從這些書籍中了解西方,並且將書中用來表現新概念的漢語詞彙直接就可以用於日語中了。”還指出:“迄今為止好多被認為是從日本進來的詞實際上早就存在於英華字典中或西學新書裏了。這一事實在中國國內的漢語研究領域內恐怕一直沒有得到重視。”
1860年江戶幕府派遣使節團,鹹臨號護衞,福澤諭吉充當艦長的隨從赴美國西海岸,大開眼界。歸國後把在美國買來的廣東語和英語對照的《華英通語》加上日語,刊行平生第一本書《增訂華英通語》。好多人不看過程,特別是打鬼藉助鍾馗時,更只問結果,有意無意地忽略乃至抹殺了這個歷史過程。
再者,當初日本人並不是把西方語言翻譯成他們的現地語,而是翻譯成普遍語,即漢文。例如日本第一本譯書是1774年刊行的《解體新書》,原為德國人醫生撰寫的醫學書,從荷蘭語轉譯,當時叫蘭學,譯成的是漢文。尤其是譯詞,都譯成漢字詞語,所以我們中國人才能隨手拿過來,幾乎和他們同步理解並運用。
例如“動機”是motive的譯詞,譯者用中國古文來解釋:《列子·天瑞篇》有云: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機者,群有始動之所宗云云,今取其字而不取其義。不消説,能做出如此解釋,是身懷普遍語知識。這裏所謂不取其義也是虛言,真若不取其義,何不隨便譯作狼心或狗肺。最近新天皇登基,年號更新,彷彿早忘卻漢字造語功能的日本人又造了一個新詞“令和”,我們照用不誤,而且比他們更明白其出處及用法似的。
水村美苗的立論基本受美國的政治學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書《想像的共同體》影響。她説:此書至今猶是必讀書,因為其核心仍然有意義,那就是分析國民國家成立之際,國語、國民文學、民族主義是如何關聯的。安德森認為:近代國家這東西完全是人為製造的文化性產物,並不是從以往歷史的必然性歸結的,因應這種人為的近代國家還製造了國語。一旦這樣確立了國語,國民就覺得國語像是深有根源的東西,常常被當作國民(或者民族)的民族認同的證明。那不過是“想像共同體”製造出來的東西。
水村拘泥於近代,可能原因也在其經歷。她出生東京,十二歲隨家移居美國,但始終不適應美國和英語,通讀《現代日本文學全集》以慰鄉愁,就這麼僑居二十年。這套全集是1920年代出版的,六十三卷,幾乎可説是近代文學全集。曾留學法國,又上耶魯大學專攻法國文學。修完博士課程後回國,並且在美國的大學講授日本近代文學。吃外語飯的人往往厭惡那個外語,水村算不算吃外語飯呢?她用日語寫小説,1990年為夏目漱石未完成的小説《明暗》續貂,並非狗尾,獲得藝術選獎新人獎。在她眼裏近代淨是“範兒”,國語就是以夏目漱石為代表的近代日本文學所表現的語言。
評論家加藤週一2008年去世,水村覺得“近代日本知識人的一個寶貴的‘種’終於滅絕了”。加藤本來學醫,日本戰敗後留學法國,但回國後放棄血液學研究,轉而當文學評論家。水村説:這不單因為日本戰敗後還沒有科學研究的環境,還因為日語的豐富,讓人想用日語認真地讀寫。他是迴歸了日語。今後像加藤週一這樣的日本人還會認真用日語讀寫嗎?今天的日語仍然是能夠讓加藤週一那樣的人放棄科學之路而回歸的語言嗎?這個問題是當今所有非英語圈的人的宿命。
《日語滅亡時》一書還有個副題:在英語世紀中。水村寫道:“日本人住在被大海圍繞的島國,不必抱有自己的語言説不定消亡之類的危機感,連綿地生存下來。然而,現今闖進了英語這種普遍語通過因特網,翻山越海,在全世界橫飛的時代。21世紀英語圈外的所有人都被置於自己的語言從國語淪落為現地語的危機。儘管如此,日本人,包括文部科學省在內,卻懵懂地活在英語多些、再多些的大合唱之中。”
所謂“英語世紀”,並不是説全世界的人都用起了英語。現地語在哪裏都繼續存在,但世界上大部分“追求睿智的人”把英語作為普遍語使用。日常生活中使用現地語,智力活動選用普遍語,這就是“英語世紀”。非英語圈國家面臨三個選擇:把國語改為英語,所有人都會兩種語言,一部分人會兩種語言。如今國語已定型,通常不再有把日語替換掉的想法,而是大力推行所有人都會兩種語言(bilingual)的國策,人人“兩把刀”。
水村認為沒必要全民懂英語,只要有精通兩種語言的少數人翻譯就足矣。學生應該把用在英語上的時間用來學國語。然而,日本完全沒有把國語教育的重點放在代代閲讀優秀的近代文學上。近代文學的古典就是國語確立以後的作品羣,普通人也能沒有太大困難地閲讀。從英語圈來説,例如莎士比亞的戲劇。
日本的現實是國語課時少,課本薄。一種中學校使用最多的三年級課本,所選文章多是活著的作家的。東京大學一般學三個學期英語,但國語一個學期也不學就可以畢業。莫非以為人人都會説日語,文學就是口語,人人都是文學家,不必在課堂上學。長此以往,日語“滅亡喲”。
夏目漱石對於日本盲目地憧憬模仿西方不以為然,小説《三四郎》的主人公三四郎從熊本前往東京上大學,在三等車廂裏遇見一個鬍鬚男——
“這樣的臉,這麼弱,即便日俄戰爭獲勝,變成一等國,也不行呀。不過,看看建築,看看庭園,哪兒都跟臉相稱。你頭回去東京,還沒見過富士山吧,過一會兒能看見,看一看。那是日本第一有名的東西,除了它以外再沒有讓人得意的了。可是,富士山自然天成,早就在那裏,沒法子,不是我們造的。”他説,又冷冷地笑著。三四郎沒想到自己在日俄戰爭之後碰上這種人,覺得怎麼也不像日本人。
“但往後日本也漸漸發展吧!”三四郎辯解。於是那男人一本正經地説:
“滅亡喲。”
《日語滅亡時》的書名就是從這裏來的。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