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号房”事件——正义之外,我们还能看见什么?
“N号房”事件闹得沸沸扬扬,媒体和民众关注的议题主要有女性、隐私、色情产业、网络犯罪等。在这场讨论中,被反复提及的26万人和声张正义的民众仿佛站在正义的两边。
本文希望暂时搁置以上议题,谈谈正义以外的事情。
一、监视概念
在进入正题前,发生在“N号房”内外的“监视”或许是一个需要被解释的概念。

“圆形监狱”(panopticon)是最早由边沁在18世纪提出一种监狱设计方式。这种设计方式推翻了监狱建造的传统原则——封闭、剥夺光线和隐藏。它只保留下“封闭”,其他两个则被舍去。充分的光线和监督者的注视比黑暗更能有效地捕捉囚犯,因为黑暗说到底是对囚犯的掩护,而可见性才是捕捉器。

这个概念被福柯发展为“全景敞视主义”,作为现代纪律社会的隐喻,圆形监狱提供的监视模式“少数观看多数”(the few watch the many)被理解为一种权力机制和政治技术。
两百多年前,边沁的监视想象脱离不了砖石的基础,但今天大众媒介的兴起完全改变了这一切。先是“单视监狱”(synopticon)被提出,尤其适用于电视冲击下“多数观看少数”(the many watch the few)的模式。之后杰弗逊·罗森提出“全视监狱”(omniopticon),即“多数观看多数”(the many watch the many),而这毫无疑问是互联网赋予的权力技术。
互联网时代,一根网线便可以带我们抵达任何人,砖石墙壁不再成为传播的限制,只要时间尚存,信息的流动就不会中断。与此同时,我们也在承担着任何人都可能抵达自己的风险。这样,我们再也不知道自己在观看谁,谁又在观看我们,观看者和被观看者的界限被模糊,多数人对多数人的观看也由此形成。
二、26万人的观看与百万人的正义
“N号房”事件中,我们不难看到犯罪事件与“全视社会”的拟合。
聊天室管理人的目标对象是在推特上发布淫秽色情推文的未成年人,管理者通过冒充警察或使用其他欺骗手段获取受害人的身份信息,以达到继续索要“性剥削”内容的威胁目的。是互联网提供的技术权力使任何人都可以低成本地接近他人的隐私,明目张胆的骗术或许也只是其中最低级的方式之一。
迭代两轮的管理人背后是一场参与者高达26万人“观看”。会员不仅接收内容,也参与讨论、分享内容,甚至其中的一些高阶聊天室只允许内容贡献者进入。在这里,他人的隐私作为私人物品被加工、被传播、被用于交易,内容量在互联网的开放自由精神和技术空间下以指数倍扩充,更多的眼睛被吸引至此,在匿名场域下成为黑暗中的观看者。
此事件激起韩国的民愤,在N号房的三号管理者“博士”被逮捕后,有人在“青瓦台国民请愿”系统上发表了题为《公开Telegram n号房嫌犯身份并公开照片》的请愿文章,当天就获得了166万人的支持。此后又有民众提出,不仅要公开管理人的信息,26万加入过该组织的用户信息也应当被公示,该请愿同样获得了数百万韩国民众的支持。
事件发展至此,“围观”这一概念被引入。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描绘了前现代社会里“惩罚剧场”的样貌,对罪犯肉体表演式的惩罚化身为剧目在那里轮番上演。尽管惩罚剧场的存在更多地是在展示统治者的淫威,但是民众作为观众也在围观中享受着见证的权利。“在这种恐怖场面中,民众的角色是多义的”,民众不仅作为观众存在,某种程度上,民众也是惩罚的参与者。
英剧《黑镜》第二季中的“白熊正义公园”正是对惩罚剧场的复现。本质上说,惩罚剧场是在声张一种“表演正义”,也即面对表演式的惩罚,围观者出于对正义的信念,坚定地站在惩罚的一边,并且这个惩罚越近于逼真就越近于观众心中的正义。

N号房”事件中26万会员的身份信息同样作为隐私存在,暂且搁置“看黄片自由”“我付钱看黄片哪里有错”的说辞,没人能够否认,在信息社会公示身份信息和“被扒光了衣服展示肉身”实际上别无二致。
围观者通过观看惩罚表演获得了内心正义感的声张和愤怒的释放,但这种对犯罪者造成终身痛苦的剧场审判是否也有值得警惕的成分?
三、向隐私开战的正义
值得注意的是,“博士”被逮捕后,民众反应中首先应该落实的行动是,公布其身份,公布26万会员的身份。
坊间讨论之外,官方也正在行动。据韩媒报道,韩国警方将与FBI合作调查“N号房”案件的26万名全部加害者,并组成数字性犯罪调查小组前往Telegram公司进行调查,但Telegram公司目前并未给出回应。
作为一款即时通讯软件,Telegram因为使用“端对端加密”(E2EE)等信息安全技术而广为人知,大批用户出于对信息安全的考量而选择它。相比于以Facebook为代表的商业模式中体现的“监视资本主义”(surveillance capitalism),或许Telegram真正贯彻了对万维网和隐私权的尊重。但面对如此引起民愤的案件,Telegram应该协助警方调查吗?
互联网自诞生始就不断将社会向全视状态推进,福柯所警示的“全景敞视主义”似乎在被互联网消解。乐观者认为互联网是由旧金山湾区的工程师、黑客和企业家集体发明创造的,是真正自由的创造物,事实果真如此吗?
肖沙娜•朱伯夫在《监视资本主义时代:在权力新边界为人类未来斗争》中的讨论使监视资本主义成为热议话题。越来越多的新闻揭示着无处不在的监控才是大科技巨头们商业计划背后的核心原则。与肖莎娜如出一辙,亚莎·莱文也在《监视谷:互联网的秘密军事史》一书中指出互联网自创建以来从未失去和军事的联系,毕竟互联网最初就诞生于美国军方资助下的摇篮。
或许商业利益裹挟下的偷窥和由政治手段加持的监视从来没有退场过。可尽管对“全景敞视主义”的描绘是让人不寒而栗的,在“N号房”事件中,民众也并非一味地拒绝监视。
是“逃避自由”的心理使然还是陷入群体暴政的不自知?此文并不想在这个问题上盖棺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互联网何以至此”的发问背后决不止是政治势力或科技巨头的单方面作俑。我看到更多的是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的预言,人们在信息的汪洋中失去了对自己的掌控力。如果今天的“隐私权”只能作为口号高呼,那么隐私的具体所指变得若隐若现似乎也是可以理解的。
四、黑暗与窗
在监视概念中,我们看见光明与黑暗的数次博弈。圆形监狱里,囚犯生活在“希腊哲学家的玻璃房子”中,光明的背面即是无止尽的注视;单视监狱里,囚犯被困在电视荧幕里,但这些大人物呼风唤雨的景观下,看电视的人何尝不是囚犯?而在全视监狱,观看与被观看的长期存在使人人都想躲进黑暗,住进无窗的囚室,却又想在墙壁上挖一个窥视的洞。
建筑师柯布西耶曾转述奥地利建筑学家阿道夫·罗斯的话:“一个有教养的人不往窗外看;他的窗户上是覆了霜的玻璃;窗口的存在只是为了获取光,而不是让注视穿透。
“N号房”事件中,既然有讨伐Telegram不配合警方调查的人,就必然有支持Telegram坚持捍卫隐私的人。监控与隐私权之间的拉锯、协商与角力正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光明蚕食黑暗”又或者是“黑暗吞噬光明”的荒诞景观也会长期存在。
如果N号房果真是至暗的存在,我们又该为它安一扇怎样的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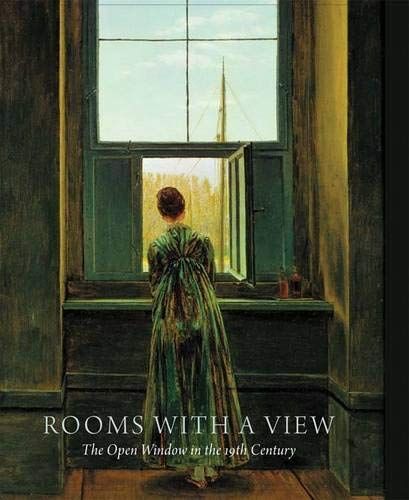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