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1 | 欧洲以东,亚洲以西:后冷战世界下的中亚(上)
在新冠疫情肆虐的当下,近期吉尔吉斯斯坦政局的动荡,让很多只通过新闻认识世界的人们意识到,“中亚”——欧洲以东,亚洲以西,这块广袤的欧亚中部腹地,似乎一直处在隐而不发的沉寂之中。至少在西方学术界中,这是一个长期被忽视、但也从未被忘却的地带。2015年,历史学家Peter Frankopan在新书《丝绸之路:一部新的世界史》中,将叙述世界历史的中心重新挪回了欧亚中部。在他的新书成为畅销书的同时,中亚也随着“丝绸之路”成为了全球学术界的新宠。在后冷战的全球化格局下,中亚的战略重要性不言而喻。但讽刺的是,似乎也正因为这一原因,中亚在西方和中国学界得到关注,往往也局限于其政体和地缘政治的变化。然而,中亚远远不止这些。
本篇综述的作者Morgan Y. Liu,目前在俄亥俄州立大学任教。作为一位研究中亚的文化人类学家,他长期关注全球背景下的中亚经济精英、前共产主义国家的穆斯林群体、中亚地区的非正式社会网络,以及伊斯兰体系中的社会公正概念。在这份对后冷战世界下中亚研究的综述中,Liu清晰地勾划了中亚复杂的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地理,探索超越国家、民族、语言边界的各种可能性。在Liu看来,关注流动、不确定性和日常生活的民族志,是讲述中亚故事的极佳载体,“这些故事会复杂化、乃至对抗中亚的宏大叙事”。面对中亚驳杂的人文地理,研究者需要熟练掌握不同的亚欧语言,这也为培养类似Joseph Fletcher(1905-1991)那样精通超多语言的中亚学者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与此同时,Liu也不断提醒中亚学者和对中亚感兴趣的读者,需要不断回到深历史、全球化、后冷战的视角中去理解中亚的复杂性,不仅是当作提供案例的地区,更是激发理论对话的起点。
本文译文将分成两部分发出,在第一部分中,你即将读到“从人类学角度定位中亚”、“后社会主义的经济和生活现实”、“超越苏联的中亚‘悖论’”。第二部分中,Liu会接着探讨“宗教观察”、“国家性的逻辑与表达”,并提供一份未来中亚研究方向的结论。
原文作者 / Morgan Y. Liu
原文标题 / https://www.annualreviews.org/doi/full/10.1146/annurev-anthro-081309-145906
译者 / 啸风、焦巴弓、丁旖
原文发布时间 / 2011年6月
编校 / 叶葳、曾毓坤、林子皓、王菁
整合校对 / 王菁
01.
从人类学角度定位中亚
中亚地区,在世界上是一个多方力量汇集的要津,却又未得到充分研究。在西方学术版图上,这是一个被忽视的空白点。它位于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受到中东、中国、俄罗斯、南亚(这些地区被研究得更加充分)的复杂影响。这个地区往往被视为某种别的东西,而非它自己。
例如,它被视为相对于中东腹地的伊斯兰边缘地带;它被视为前苏联、俄罗斯、中国的帝国主义工程的对象;它被视为从古至今大国地缘政治的棋局;它被视为有待开发的炭烃化合物来源地;它被视为需要贷款、技术专家、新自由主义实践的帮助对象;它被视为小布什政权全球“反恐战争”的战略性阵地。
中亚地区为人类学提供了机会,来讲述这些源于社会、基于民族志的故事。这些故事会复杂化、乃至对抗中亚的宏大叙事:如今所谓的后苏联转型、民族主义复兴、伊斯兰激进主义等。中亚地区也提供了一个交汇点,让我们重新思考更广泛的议题,比如现代性的社会主义模式、国家和情感、后社会主义的动荡、后殖民的国家身份、后9·11的伊斯兰想象。这些都与民族、阶级、宗教、性别主体性的独特结构关联在一起。Chari & Verdery (2009)认为,在后冷战世界的全面框架之下,任何地区的这一系列关切,都应该得到研究。它将让后殖民性主义和后社会主义的学术进行富有成效的对话,从而揭示20世纪以降全球范围的比较人类学问题。

英语世界关于中亚的人类学文献,才刚刚担负起这一职责。关于1989年、1991年东欧和前苏联的国家社会主义解体后的生活,已经有了浩繁的人类学研究(参见康乃尔大学出版社的“社会主义之后的文化和社会”系列书籍,由Bruce Grant和Nancy Ries编辑;参见Buyandelgeriyn 2008, Wolfe 2000)。可是,关于中亚的人类学研究在数量上还很少,而且刚开始参与当前的学术争论。不过,尽管培养这项工作的学者面临诸多挑战(比如学习多种语言,缺乏学术专著和专业导师),可是一些激动人心、价值非凡的研究已经出版了,更多的研究也会陆续出现。
本篇综述所涵盖的文献,主要与今天中亚地区的重大议题相关,特别集中在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吉尔吉斯共和国)、塔吉克斯坦、阿塞拜疆这几个前苏联共和国,同时也对新疆(中国所统治的这块中亚区域)做一些对比的关注。
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独立的亚洲前苏联国家在进行各种改革和国有化时,很快就普遍出现两种现象:为了成功度过经济危机而开展的种种新策略;展现苏联统治下受到压制传统的复兴。当这片地区突然开放给外部的田野工作者,中亚的人们往往喋喋不休地向外国人讲述这些动态。人类学家开展民族志调查——以追赶而非挽救的节奏,记录下这片西方学术未曾踏足的处女地。这种档案记录的意图仍然是这个领域的主要推动力,虽然当前的文献已经显示研究框架和对知识政治的反思正迈向成熟。结果是,学者们远离了对乡村生活不顾语境的描述,转而从苏联的民族文化生产和后苏联民族主义的角度来理解本土实践(以及关于本土实践的话语),直面暗藏于中亚地区的大部分学术都里的西方政治议程,来认真定位人类学研究。
02.
后社会主义的经济和社会现实
大部分后苏联的中亚研究,都普遍受到某种后冷战意图的推动。它们追问的是,国家社会主义如何“转型”为民主和资本主义?这种转型的前提是新自由主义的胜利(Chari & Verdery 2009, p. 30; Liu 2003)。与大量这种学术研究相反,人类学展现的是特定文化下形成的政治组织形式间的复杂遭遇,而非两个相互陌生的经济体系的碰撞(Humphrey & Mandel 2002, p. 2)。
随着国家与公民之间重新分配的社会契约的终结或剧减,随着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消费价格的自由化、福利供应的减少,中亚的人们日益依赖社会网络来寻找工作、现金、资源,来照料儿童,日益依赖贸易、私有农业、工艺品生产、新的服务这些新的收入来源(Werner 2004)。在后苏联时代,一个家庭的生存能力和经济能力不仅事关确保收入来源和食品供应,也事关(在大规模失业、工资和退休金缩水的情况下)对获取商品和服务的网络的维护、巩固、扩大(Werner 1998a)。虽然家庭办一场满意的婚礼有很大的社会压力(e.g., Zanca 2011, pp. 106–19),可是,这种礼物交换的仪式经济,跟广泛的经济交易有着密切的联系(Werner 1998b)。
事实上,对于农村的哈萨克人,围绕一生重大事件举行的固定宴会和礼物交换是很出名的。他们这样做,完全是抱着回礼的期待。他们的礼物也具有实用价值,因而消解了经典人类学交换理论对礼物和商品的区分(Werner 1999)。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市场自由化,没有导向喀什维吾尔人之间关系的大规模商品化,而是重新激活社会经济关系的本土模式,并增加了这些模式的复杂性(Beller-Hann 1998)。
网络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在乌兹别克斯坦乡村,不能维持互相帮助的互惠关系,成了一个家庭日益贫穷的明显标志(Kandiyoti 1998)。在这个地区,合会(rotating credit)十分盛行。在合会上,一个社区或网络中固定的一群社会成员,定期向一个集体的池子提供定额的钱,这笔钱陆陆续续用到各个成员身上(Arifkhanova & Abdullaev 2002; Beller-Hann 1998; Berg 2004; Kandiyoti 1998, 2000; Koroteyeva & Makarova 1998a; Liu 2012; Rasanayagam 2002; Werner 1998a)。这是一种非银行、国家看不见的收集大量现金的渠道,用于婚礼、家族企业和其他开支。
西方的发展项目对这些本土社会经济关系的忽视,也许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通过外来的(通常是腐败的)机构向社会各阶层发放贷款的努力很少取得成功(Pelkmans 2003)。虽然全球机构将庇护网络视为发展的阻碍,可他们推动反腐斗争,其实主要还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投资,避免学习陌生的商业实践的麻烦(Werner 2000)。
后苏联的经济转型影响所有人,不过对女性和男性的影响不同,从而把研究者的关注点导向了特定的文化领域。这些领域里,公共/国家领域和私人/亲属/家庭领域互相建构,并被赋予不同的价值。因为农业改革迫使许多妇女脱离农村劳动力市场,进入家庭领域,所以妇女是特别脆弱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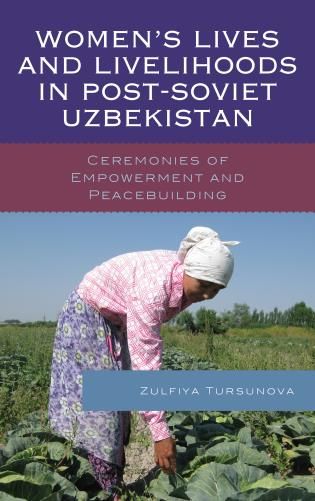
在社会主义和后社会主义的农村经济中,性别意识形态有着惊人的连续性,这种意识形态错误地看待女性劳动的价值;不过,实际上,由于共同义务网络内的家庭经济在家庭生存中起着关键作用,所以,女性的劳动仍然得到男性某种形式的认可(Shreeves 2002)。一种强烈的男性焦虑,来自男性时常无法履行供应者的角色(Dautcher 2009)。性别化的媒体对“英雄企业家”的描绘,造就了这样一种理想(Mandel 2000)。很多女性也做点小生意,在市场上卖东西,使集市变得女性化。这是因为人们认为男性更适合男性化的工作,不适合处理金钱,缺乏销售的沟通技巧,也没耐心坐一整天(Werner 2004)。做生意的女性在家里的责任减轻了,也有新的出行机会。在阿塞拜疆,人们仍然觉得做小生意丢脸,主要让女性承担;而大型生意(包括这些生意的资本、和政府的联系、获得的名声)主要交给男性。不过,这种情况也许会发生变化,因为越来越多女性开始参与中等和大型的市场活动。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受了西方女性榜样的鼓励(Heyat 2002)。
我们可以把集市本身视为后苏联的中亚普遍生活的缩影,夹杂着自由市场的混乱感、巧取豪夺、野蛮的投机主义、对公利的不屑一顾(Nazpary 2002),夹杂着振奋人心的财富、消费、全球品位、野心的各种可能性(Liu 2007, Zanca 2011)。讽刺的是,相比与苏联统治下有意的非市场的现代化,后苏联的社会经济变革,以及新的富有商人阶层和政治精英的挥霍消费,可能给本土社区结构带来更大的威胁(Kandiyoti & Azimova 2004)。
03.
超越苏联的中亚“悖论”
在中亚研究中常常被讨论的一个基本问题是,苏联国家对所谓的保守穆斯林群体的改变有多彻底?这里似乎存在一个悖论,因为我们既能给出中亚社会“顽固抵抗”的证据,也能找到深刻变革的证据(skillfully summarized and cited in Kandiyoti 1996)。然而,西方学术的这种悖论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冷战斗争的影响,冷战关心的是揭露苏联社会工程的残酷和失败(无论悖论的哪一边是对的,西方都是最后的赢家)。
目前的历史学作品和人类学作品,通过引起对苏联统治的独特生产力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文化静态和疯狂殖民”两种立场看似的矛盾(Kandiyoti 1996, pp. 531–32)。在国际主义(塑造进步的“苏联人”)和民族特殊论(肯定民族的社会现实和政治价值,肯定其他族群范畴的等级制度)之间,苏联达成了一种特有的平衡(Hirsch 2005, Martin 2001, Slezkine 1994)。虽然族群(ethnicities)不是凭空捏造的,不过它是由国家的民族学者在1920-1930年代定义的:他们把从前流动的混杂性和情境化的认同过程固定下来,让它们自然化,放到特定的模型里,让每个群体都有确定的历史、面相特征、思维模式、物质文化、语言、领土。然后,他们把这些定义制度化,成为以民族编码的领土-行政机构(联盟的15个共和国,以及某些特殊的次级区划),成为70年日常生活的常规,包括护照、民俗舞蹈大会(Doi 2002)、音乐(Levin 1996)、文化宫、教育部门。

这种人类学,最好地服务于国家,服务于福柯式的生命权力(Ilkhamov 2004, p. 318)。它同时产生了社会融合(苏联生活方式、苏联文化)和差异(各民族特性)。这种人类学塑造了今天中亚的人们看待自己的样子。它反映在后苏联国家所倡导的咄咄逼人的民族主义之中。这种民族主义的“光荣的过去,伟大的未来”的叙事,跳过俄罗斯人的统治时期,把它仅仅视为一段插曲。可实际上,这种叙事重复的还是苏联的意识形态形式,甚至包括它的内容(Adams 2010)。因此,1991年以来,中亚的文化“复兴”代表的不是压抑的民族情感,而是国家统治技术的产物(Adams 1999)。简单地说,在日常生活和思维范畴上,今天的中亚人们受到的苏联影响比他们承认的更多,苏联统治的遗产不光是表面上的(Kandiyoti 2002a, p. 252)。所以,苏联的现代化工程的特殊性导致了这一悖论,民族文化和民族意识既是国家的产物,又是对国家的回应(Kandiyoti 1996)。
任何后苏联的中亚人类学,无论关注点是什么,要想避免现代性-传统、殖民-被殖民、俄罗斯-中亚这些二元论走向绝对化(such as found in Harris 2004, 2006),就得承认这些习惯和认识论的多样关联,承认“苏联制度和本土文化形式的相互融合”(Kandiyoti 2002b, p. 291)。我们必须揭开随处可见的传统复兴的话语,说明它们是发明出来的,说明它们背后的政治。
阿克撒卡尔(长者)法庭就是一个例子。这是1995年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卡耶夫设立的推行“习惯法”的机构,职责是依据吉尔吉斯人的道德规范进行判决。而现在,它已经成为吉尔吉斯乡村生活的常规特征(Beyer 2006)。虽然村里的长者一直充当着纠纷的调停者,不过,之前不存在这样的法庭(因为游牧的吉尔吉斯人的权威基于个人而非机构),而现在却被后苏联国家推崇为一种向前苏联生活方式的回归:这些法庭可以说是前苏联的,也可以说不是前苏联的。当阿卡耶夫总统在2003年宣布“吉尔吉斯建国2200年”的时候,他对历史的宣称同样也是问题重重的。宣称吉尔吉斯在2000年前就作为统一、有意识的民族群体,甚至已经有一个“国家”,我们先不说这样的宣称有多可疑。即便如此,我们也能看到,这场运动的意图是在紧张的政治僵局(阿克塞事件)之后用祖先的道德价值把国家统一起来——尽管共和国仍然陷入了“郁金香革命”,在2005年推翻了阿卡耶夫 (Gullette 2010, pp. 156–76)。
在关于中亚的人类学论著中,Adams(2010)的民族志可谓迄今为止构思最为精妙且扎根现实,他详尽地研究了文化发明中跨越更广泛领域的一个例子,那就是乌兹别克斯坦定期的奥林匹克式演出。这种演出,在现代主义的框架之下,展示传统的舞蹈、音乐、服装、主题,从而传达国家对丰富内亚遗产的宣称。Adams把1990年代的乌兹别克斯坦展示为一种“景观国家”(spectacular state)。在这样的国家中,政治主要通过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的政治景观在象征层面展开。这种做法表明,后苏联国家一方面推动后殖民文化的复兴,另一方面也在全球层面寻求尊重。这些景观背后雅努斯式的目标(双面目标),反映了苏联统治技术的二元性:一边构建的独特遗产和本质化民族(后苏联时代的乌兹别克斯坦政府也在旧瓶装新酒),一边提倡进步、和平、国际主义这些普世观念。作为一种国家权力策略,景观所实现的是,建构一种单向的交流领域。在这个领域,国家向人民提供一种包容的感情,甚至是涂尔干所说的欢腾(effervescence),而人民没有回应的可能性。这样的技术试图借助独白对意义进行垄断,从而揭示这个区域主导的民族国家(它的压迫统治人尽皆知)如何对公民行使权力,如何在后冷战世界定位自己。
乌兹别克斯坦还试图通过复活一项前苏联的乌兹别克机构,来扩大它的控制和监视。这项机构是马哈拉(mahalla),一种城市居民区的形式。虽然在苏联统治期间及之前,马哈拉以不同的组织形式存在,而且具有不同的意义,可是,独立的乌兹别克斯坦1993年设立了新的行政单元,仿佛这个单元是从苏联所压制的民族传统中自然演变出来的。马哈拉委员会直接向上级部门汇报,成了所有公民与国家打交道的最初地点。一方面,它的职能包括税收、征兵、投票、护照、社会福利发放、犯罪调查、国家意识形态宣传等等,代表了国家垄断日常社会生活规范的企图(Koroteyeva & Makarova 1998b, Massicard & Trevisani 2003)。另一方面,作为居民社区,马哈拉擅长制造社会等级,以及共同利益的观念。

民族志关注社区的日常惯例,把这种惯例视为根植于一定空间的具体活动,和马哈拉的形态和感官性质密关联在一起。这种关注,揭示出不经反思的实践同关于恰当权威和恰当个人的社会想象之间的互相建构(Liu 2012)。马哈拉成了某种半公共的场所。在其中,国家希望居民采取性别化的民族生存实践,进行民族的自我认同,来维持一种本质化的性别意识形态(Saktanber &Özataş-Baykal 2000),并且把女性作为真正文化载体的形象作为范例(Fathi 2006, p. 308; Harris 2004; Megoran 1999; Tohidi 1997)。不过,在乌兹别克斯坦,马哈拉委员由老年男性主导,他们越来越多地掌控了社会福利的发放,离异和被抛弃的妻子这些社区边缘人群,正面临被排除在合法权利之外的危险(Kamp 2004)。即使乌兹别克斯坦的马哈拉代表了把国家的视线和控制延伸到每个家庭的企图,可讽刺的是,国家职能的下放,可能使缺乏社会资本的人无从寻求正义。
(待续)
结绳志团队特别感谢本次的译者团队——啸风、焦巴弓和丁旖。 如果你对加入我们的团队感兴趣,请在后台联系我们,也可以将你感兴趣的选题或译文发到我们的邮箱tyingknots2020@gmail.com。若要转发本文,请在本文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或者邮件联系。
欢迎通过多种方式与我们保持联系。
独立网站:tyingknots.net
微信公众号ID:tying_knots
【倾情推荐】订阅 Newsletter
成为小结的微信好友:tyingknots2020
我们来信、投稿与合作的联系地址是:tyingknots2020@gmail.com

目次(持续更新)
- About us | 一起来结绳吧!
- 进口、洄游与误归:三文鱼的驯养经济与后新冠时代的多物种认识论
- 口罩为何引起热议
- 结绳系疫 | 错过新冠革命:后见之明与民族志知识
- 结绳系疫 | 后疫情时代的后见之明与具体研究
- Corona读书会第23期 | 医疗基建 Medical Infrastructure
- 新冠疫情会长久地改变洗手习惯吗?
- Corona读书会第6期 | 动物、病毒与人类世
- 非男即女?:生物学家有话说
- Graeber | 中文里的格雷伯
- David Graeber | 萨林斯悼念格雷伯
- David Graeber | 论飞行汽车和利润下降
- Graeber+Piketty | 劫富:关于资本,债务和未来的交流
- David Graeber | 傻屌:解开“领带悖论”
- David Graeber | 过于关怀是工人阶级的诅咒
- Graeber | 互助也是一种激进:恢复“冲突与和平之真正比例”
- 国际聋人周的礼物:一份人类学书单
- 「修车大水,就是我想要的生活」——自我去稳定化(self-precaritizing)的「三和大神」
- 算法文化与劳动分工:启蒙运动中的计算
- Graeber | (反)全球化运动与新新左派
- 书讯 | 英文人类学新著 | 2020年9-10月
- 欧洲以东,亚洲以西:后冷战世界下的中亚(上)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