犬儒主义的起码定义:当代中国的日常社会批评和“生活”的些许意义
犬儒主义的起码定义:当代中国的日常社会批评和“生活”的些许意义
A MINIMAL DEFINITION OF CYNICISM: EVERYDAY SOCIAL CRITICISM AND SOME MEANINGS OF “LIFE” IN CONTEMPORARY CHINA
作者:汉斯·史坦穆勒(Hans Steinmüller,LSE人类学系)
译者:陈*钢
受篇幅和审查制度限制,原文内容有所删改,脚注和参考文献已省略。
犬儒主义者是传教士。他们传达的信息是,人们可以以任何时代所强加的方式生活。
——唐纳德·达德利(Donald Dudley,1937年)
2013年9月的一个晚上,我和我的朋友陈容(音)在他位于云南省澜沧县的家中收看电视节目。作为当地成功的商人,陈容结交社会各界的朋友,包括有权有势的地方官员。
这天,中央电视台的晚间新闻再次聚焦重庆市某政府官员的案件审理,该名官员因贪腐的指控被罢免职务。他的案件审理过程在9月份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头条新闻。
随着时间的推进,和该名官员有关的堕落腐败的生活细节被逐渐披露,包括他在法国的别墅照片,儿子在牛津大学和哈佛大学学习期间的费用清单,包养情妇的指控,以及他妻子的婚外情细节。即使以前很多人对该名官员的评价很高,现在他的公众形象也被彻底摧毁了。
我和许多观察人士都认为,该名政府官员的庭审在电视台上每天播出,既摧毁了他的声誉,也让普通人相信他将永远不会回到政治精英阶层。那些称赞中国“法治”(“rule of law”)因此不断进步的人,也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作用。
“但每个人都知道政治精英们有法国别墅和情妇吧?”我问陈容。他回答道:“当然。”不过他又补充说:“但实际上,很多普通人并不知道。”
每一个中国人都了解腐败吗?这取决于你问谁了。陈容表示自己了解,但普通人不见得了解。我又问了别的朋友,他们大多给出了相同的答案。
的确,有些人相信上面这位官员比其他官员更腐败,做过更堕落的事。但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审判开始前只听说过他的名字,并不知道他是谁——至多知道他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地方官员,处在漩涡之中。
如果许多中国人都认同腐败是普遍现象,却又认为看上去透明而公平的审判标志着中国“法治”的进步,那么除了“犬儒主义”外,我们应该如何给这些大众贴标签?
在这篇文章中,我想讨论一下当代中国的犬儒主义。将犬儒主义作为日常社会批判“起码的”(minimal)定义也许有利于民族志研究。本研究建立在我早年对“反讽”(irony)的研究之上。
本文的思路也来自最近我和苏珊妮·布兰德斯塔德特(Susanne Brandst?dter)组织的一个题为“反讽、犬儒主义和中国政制”(Irony, Cynicism andthe Chinese State)的项目。以下内容包含我在中国农村的田野调查和民族志案例。
* * *
“犬儒主义”一词来自希腊语词汇“狗”(κ?ων)或“像狗一样”(κυνικ??)。雅典人说,哲学家第欧根尼(Diogenes)表现得像一条狗。但第欧根尼并不以为然,他接受了这种看法,还把狗称赞了一番。他说,狗不关心社会习俗,因为徒劳无用,但狗既诚实又忠诚。
第欧根尼拒绝了社会价值,过着一种违背所有习俗的生活。他在澡盆里睡觉,在公共场所做任何事(小便和自慰),像一条狗一样。第欧根尼把这种羞辱转变成一种恭维。狗不是本能的象征,而是忠诚的象征。

显然,古希腊哲学中的“犬儒主义”和现代意义上的犬儒主义有很大差别。如果我们忽视历史细节,我们可以认为犬儒主义的古典意义与现代意义的差别,和第欧根尼与雅典人阐释狗的差别如出一辙。
也就是说,狗诚实而善良,但它们因不理解道德和社会习俗而令人感到遗憾。犬儒主义意味着站在社会价值和时代价值的对立面。反对社会的人赞成某种比社会更“本真的”(“authentic”)“本性”(“nature”)。
类似关于“狗的哲学”的暧昧说法也可以在中文里找到。但雅典人指责第欧根尼的行为与中国人对狗的鄙视不一样。狗可以是肮脏的,也可以是忠诚的。即使是忠诚的意义,狗也被否定为盲目和被动的追随者。
还有很多和狗有关的脏话,其中最严重的是骂人“狗娘养的”或“狗日的”,暗示别人的母亲是狗,或与狗性交过。有俗话说狗认不得祖先,但根据习俗每个人都应该尊重自己的祖先,这样狗就逾越了普罗大众的行为和社会习俗的基本界限。
因此在中文里,把犬儒主义称为“狗的哲学”很有道理。和英语语境一样,中国犬儒主义者的道德评估取决于狗的隐含意义。
积极地说,它们不会被社会和文化“宠坏”。或者说,由于缺乏“文化”和“社会”的某层意义,生活就是它们的本质。犬儒主义者是批评当代社会的人,并拿这种生活和一种“基本层面的”生活——或“生活本身”(life itself)进行比较。
我希望犬儒主义的起码定义是拿狗的生活与社会习俗进行比较。这个隐喻可以有不同的含义。犬儒主义者可能被视为生活的被抛弃者,或者被誉为虚伪真实的反对者。我对这个隐喻的社会用途特别感兴趣。
称某人为犬儒主义者意味着这些人知道社会习俗,但是决定拒绝它们。我在这里不打算解释别人脑海中发生的事情,而是要解释这种阐释是怎么做出的。也就是说,我要解释这个隐喻在现实中如何作用于社会交往。这个隐喻允许我们对社会行为进行定位和多元化的阐释。
接下来,我将阐释如何利用这个起码的定义来描述当代中国的日常社会批判。但在那之前,我将比较犬儒主义的起码定义和人类学、哲学中的其它犬儒主义理论。
* * *
研究犬儒主义的人类学家常常提到彼德·斯洛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和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i?ek)。在畅销的《犬儒理性批判》(Critique of Cynical Reason)一书中,斯洛特戴克反对理性和现代性的启蒙话语,并将其谴责为“极权主义”(“totalitarian”)和“非人化”(“dehumanizing”)。斯洛特戴克认为,这些话语导致了一种毫无生机的犬儒主义,一种“被启蒙的错误意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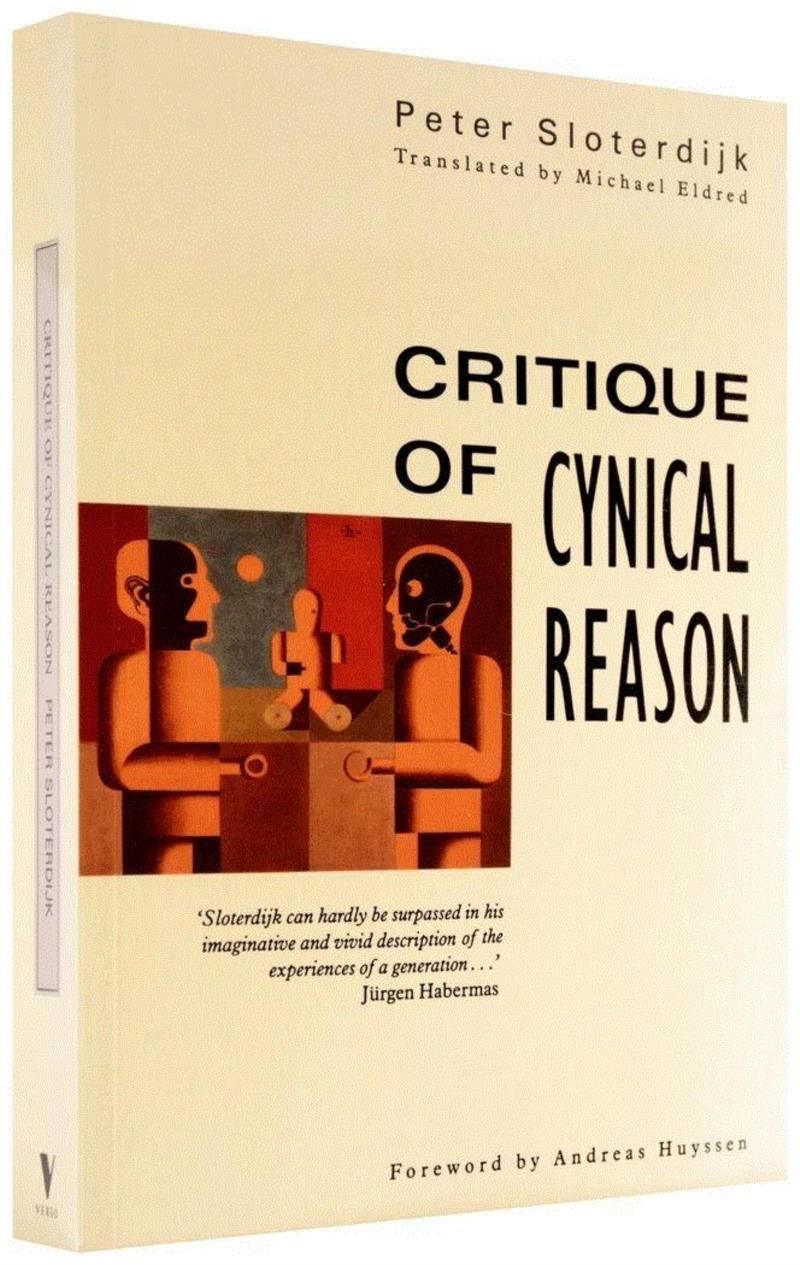
传统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批判的观念意味着“揭开”事实真相,即隐藏在意识形态错误认知背后的社会现实。齐泽克受拉康的启发,认为意识形态本身是社会现实的构成部分:“他们知道他们在活动中跟随着假象,但仍会这样做。”
如果有人在公开场合假装自己坚持崇高的理想,然后私下跟你谈论的全部都是“金钱、权力和/或性”,那么这可能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犬儒主义者。根据齐泽克的观点,这种犬儒已然成为当代意识形态的一部分。
因此,对意识形态简单而天真的批判已经不再适用了——例如揭开资产阶级理想的意识形态面纱以发现剥削的意义。需要另一种更根本的意识形态批判,将假象批评为“我们的行为”而非“我们的知识”的一部分。
因此,如果当代占据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乐于承认“权力、金钱和性”就是一切的话,那么齐泽克会坚持通过拉康和马克思的理论来进一步解释“权力、金钱和性”的驱动力。
也就是说,有必要了解意识形态假象是身份认同和身份交换的组成部分之一,这也是渴望权力、金钱和性的先决条件。
齐泽克对“犬儒主义”的道德评价复杂而模糊,但本质上是消极的,这也完全符合这个词的日常使用。对齐泽克来说,犬儒主义也意味着“像狗一样”的误认。
犬儒主义只是对意识形态假象的建构能力视而不见的方式之一。即使我们不认真对待事物,即使我们保持着一种反讽的距离,我们仍然在做这些事。
即使犬儒或反讽的距离只是意识形态的形式之一,但齐泽克在其它地方已将其视为当代意识形态的中心形式。当代犬儒主义的起源问题被广义的“我们”(“we”)和“现在”(“now”)掩盖。
这种一般性是有问题的。但是犬儒主义通常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在社会主义晚期和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都是类似的情况。
许多讨论犬儒主义的人类学家也在特定的地点和时代对犬儒主义提出相似的论点。他们通常认为,意识形态的犬儒主义和无权力的犬儒主义相吻合。
例如,雅艾尔·纳瓦拉—亚辛(Yael Navaro-Yashin)和阿列克谢·尤尔恰克(Alexei Yurchak)辩称,犬儒主义已然成为过去数十年苏联和当代土耳其主流意识形态的核心。
纳瓦拉—亚辛断言,犬儒主义是土耳其“在国家权力领域普遍且普通的管理方式。”在她的论点中,犬儒主义不仅是土耳其人民与政权最普遍的关系方式,也是政权复制自身的一般模式。
阿列克谢·尤尔恰克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苏联发现了类似的犬儒主义。尤尔恰克描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幻想破灭的笑话。这种犬儒主义与公共话语中僵化的“霸权形式”密切相关。
这是一种缺乏内容的公共话语。每个人都知道,公共话语的僵化形式只是一具空壳,但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提及它。晚期社会主义出现犬儒主义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最后一代苏联人”从容安逸地接受苏联终结的原因。


纳瓦拉—亚辛和尤尔恰克强调官方叙述和个人信念之间的差距。他们指出了国家的阴暗面,这种阴暗面与崇高的国家话语相矛盾。这种张力可能让人难以忍受,导致幻灭和偏执。
正如我所说的那样,在他们两人的理论纲领中,存在着一个“极权主义”要素,前提是所有人都以可悲的状态分享着现实,并且广义的断言取代了民族志实例。
中国的文艺批评家和异见人士也有类似的论断。80年代末年离开中国的知识分子胡平就在一篇谈论犬儒主义的文章中提出过和上述引文相近的观点。在《犬儒病:当代中国的精神危机》中,胡平对中国社会和政治环境作出了令人信服的描述。
他认为,犬儒主义是共和国普遍存在的一种参与、感知政治的方式,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是如此。这种犬儒主义的根源是空想社会主义和现代中国普遍经验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
虽然中国长期以来都有公开宣扬政治阴谋论的传统,但20世纪的暴力史从根本上加剧了虚幻理想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张力。从某种程度上说,内化的偏执已然成为当代政治生活主体的核心特征。
犬儒主义和偏执表明了私人与公共、自我与他人、内与外的巨大差距。不可否认,在特定的地方和时代,政治主观性以这些方式划分开来。
但是,所有人都如此犬儒吗?我不这样认为。我怀疑作为一个社会概念的犬儒主义具有累加倾向。在我看来,这些对待犬儒主义的方式提出了一种“非此即彼”的逻辑,即硬币的两面完全分离、相互对立。
犬儒主义者是生活在偏执中的分裂人格。他们体验着内容与形式、感觉与表达之间的张力——这是一个极深的鸿沟。犬儒主义是极权主义的另一面,和总体需求比起来,真正的承诺和参与杯水车薪。
同时,对极权主义的自由主义嫌恶感不应让我们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某些地方和某些共同体最能被这些词语描述。另一个事实是,社会行为者总是声称自己是一个整体。
我认为,从民族志和历史的角度来看,人类学家研究犬儒主义的方法是对犬儒主义的指责。这就是问题所在。谁是狗?像狗一样的行为是不是好事?
换言之,对生活本身的各种社会批判和主张,剥夺了社会习俗的表层,这是对犬儒主义的陈述/表达的揭示吗?这些陈述/表达的道德后果是什么?
下面我将讨论一些人们在中国社会公共道德危机中定位自己的方式。贪婪和暴力被视为这个社会的特征。
有一些著名的新闻案例:2008年的奶粉丑闻中,一家大型乳业公司在奶粉配方中掺入廉价化学品,导致众多婴儿死亡;广州(佛山)街头的路人对被面包车碾压的孩子视而不见;逐级政府官员的腐败问题是日常最好的谈资;经济上的成功也受到各种可以手段的影响……

在这种公共道德的感知危机之下,当代中国的日常道德生活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80年代以降的“改革开放”经常被描述为从“稳固”、“统一”的道德规范向市场经济社会多元化道德规范的转变。在毛泽东时代,日常生活服从于社会主义的英雄主义道德。在当代社会,日常生活中各种形式的快乐和选择都被规范化了。日常生活的选择和快乐伴随着持续不断的道德挑战。
犬儒主义的修辞手法提供了描述道德危机和应对日常生活中道德挑战的极好方法。犬儒主义者拿当代社会的颓废和“狗一样的生活”作比。
接下来,我将讨论一些例子,这些例子试图谈论“关系”、“灰色社会”、“面子工程”和地方官僚机构的运作逻辑。在所有例子中,我都用“狗一样的生存方式”来论证犬儒主义最起码定义的使用。
* * *
犬儒的顺从和新的真诚
考虑到中国20世纪的暴力史和80年代意识形态的180度大转变,人们很容易发现那些犬儒主义者对自己的历史持怀疑态度。要找到一种将社会习俗、理想和现实结合在一起的叙事,并不简单。
约翰·费劳尔(John Flower)和帕梅拉·伦纳德(Pamela Leonard)讲述了他们在四川的一个村子做田野调查的故事。
“革命”开始时,郑国(音)曾是一名理想主义的年轻党员,但随着运动的推进,他幻灭了。与此同时,他广泛阅读了毛泽东和马克思的著作,并从批判晚清社会的书籍中找到了兴趣所在。但是他失去了理想主义:
我读得越多,越看到宣传和现实之间的矛盾。然后我开始读很多跟中国历史有关的书——《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但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揭批晚清社会的《官场现形记》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状》。读完这些书我意识到,一切都是为了权力。读完这些书之后,我失去了理想。然后毛主席去世,打倒“四人帮”……我真切意识到,这一切都是为了获得权力。
郑国自称在“革命”期间“看穿”了社会主义理想的套话。费劳尔和伦纳德指出,他的自我描述和许多城市知识分子有很多相似之处。这在他的叙述中获得了强调。
郑国时常谈起自己“对政治、宗教和理想的信仰都不坚定”。然后说:“我今天没什么事做,就是打发时间。”“太无聊了!”“为什么我们这么穷?”他甚至说:“工作不好玩,在家也不好玩。”“我没有希望,没有理想,没有信仰。”
在对其他人的深入刻画中,费劳尔和伦纳德描述了对过往痛苦经历的其它可能反应,以及人们根据“什么”推断这是一个失去了道德观的世界。
不是所有人都有郑国那样的犬儒主义观念。例如,一个名叫广兴(音)的农民在相对主义和腐败面前坚持寻找道德上的确定性。当他意识到同样的道德困境时,他的答案是寻找一种“新的真诚”,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重新发现一种旧的“真诚”,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正名”。
这种呼吁要求用恰当的称呼给人以尊重,并回归旧有的等级道德。这个农民对当代社会的分析在很多方面与他的犬儒主义邻居类似,都在指责年轻人只关心钱和权。年轻人被指责不关心生命的基本范畴,这些范畴正体现在正确使用亲属称谓上。
然而,这个农民有不同的结论。他不接受混乱而放弃自己,而是努力去纠正它。虽然俗谚说“狗不认祖先”,但广兴会通过追溯一种道德的“黄金时代”来纠正这种情况。我认为,这是对于今天的“生活本身”为何的另一种看法,或者从隐喻层面讲,是对“狗一样的生活”的另一种看法。
但实际上,两个人说的都不是简单的权力和金钱,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联。也就是说,人际关系——中国人的人际关系,毫无疑问是成功的关键。
灰色社会
然而,中国人常常把“关系”的实践视为道德预设前景背后的“真相”。“灰色社会”中,“黑色”的犯罪与“白色”的合法性/合道德性混杂在一起。约翰·奥斯堡(John Osburg)描述道:
灰色的做法将合法与非法、道德与不道德、值得尊敬的行为和应该谴责的行为结合起来。灰色的例子比比皆是。从工厂到出版社,不计其数的生意都涉及技术上违法但实际上可以忍受的行为。在这种灰色的语境下,表象不再再现真实(名实分离):企业雇佣外国留学生充当合伙人和投资者;妓女假扮成处女大学生揽客;反腐官员根据行贿自己的潜质而非实际贪腐数额来确定侦查目标,裁判和运动员往往是同一个人……
奥斯堡认为,这些做法形成了一种“后信仰社会”(“post-belief society”)。再现与现实之间的脱节成了理所当然的事。
我个人对奥斯堡的“后信仰社会”概念有些怀疑,因为这个概念认为目前没有信仰。并且它提出了一种信仰社会,就好像真的存在一样。因此,说“后信仰社会”就是要求一种整体性,而且是犬儒主义者的那类要求。
奥斯堡讨论了社会实践的道德含义,混合着自我再现的“颜色”:“灰色女人”——“二奶”或情妇;“灰色社会”——半黑半白的“兄弟”组织。
高官情妇用一种犬儒主义的观点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每个人的目的无非都是金钱、权力和性。成都的“兄弟”组织则相反,他们用人际关系的道德作为“唯一重要的法律”,以此占领道德高地。
奥斯堡指出,这两种话语最终是互补的。女人的犬儒主义和“兄弟”的精英道德都可以视为对抗充斥着“灰色”的社会的“道德的反话语”(moral counter-discourse)。
然而,尽管两者都是犬儒的,但他们对“生活”基本层面的解读却截然相反。“灰色女人”用一种本能的叙述来验证自己的行为——权力、金钱和性的三位一体。“兄弟”则声称亲密人际关系的道德性才最重要。在一种更“根本的生活”层面上,这两种人都面临着对“灰色”的普遍谴责。
一些政治经济背景
奥斯堡所描述的“灰色社会”在中国改革数十年的具体政治经济进程中有特定的历史背景。虽然存在合法的私人企业和公司,但每家公司都需要设立党支部。许多公司则由政府直接拥有。
在所有权结构中,“私人”和“公共”的资产系统性地纠缠在一起,进一步加剧了地方政府的财政自主权。由于不能完全依靠高级别政府,地方政府不得不寻找其它收入来源。许多政府部门已经成了公司,或创立附属公司。
例如,我在巴山镇做田野调查时发现,那里的村政府经营着多家茶叶加工厂,乡政府经营着一家农具厂,地级市政府的财政局下有一家汽车租赁公司。
某种程度上,这些组织模式可以归结为悠久治理历史中的“贤人治理”模式。官方的首要任务时树立“道德楷模”,官吏不应该是专家或技术官僚,而应该是道德上正直的保守派。古代的地方官吏拿着朝廷微薄的俸禄(做道德楷模),却可以动用地方权力轻松疏通财路,包括受贿、礼品和内幕交易。
20世纪的一个主要变化是共产主义革命,官员人口和官员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呈指数级增长。然而,共产主义时期的官员工资水平相对较低的情况下,其它收入来源也相当有限。
1994年,朱总理领导的国家税制改革迫使地方政府将大部分税收收入转移到更高级别的政府。并且根据财政辅助原则,地方政府的财政更独立于中央。
这意味着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和官员的收入都要靠自己的活动来补充。这恰恰发生在中国许多地区进行本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时候。工业化和城市化为地方财政创收创造了两个崭新的机会。税收只是地方政府可能收入的一小部分,其余还有内幕交易,尤其是房地产行业的内幕交易。

许多人都清楚这些情况,但他们会不会对此报以犬儒的态度呢?
有人指出,大家的反应各不相同。有时候是愤慨的语气,比如我在巴山镇的一个邻居经常抱怨当地官员:“就凭他们的工资,他们怎么可能买得起汽车,怎么抽好烟?”
一名与当地政府关系要好的农民和他一些当兵的朋友在家庭聚会时对我说:“腐败是必要的。你会发现到处都有政府。这不是坏事,或者不是问题——事情就是这样的,一直以来就是这样的。”
这样的评价在与地方政府所谓“面子工程”的关系中极为普遍。许多政府创造了“装点门面的村庄”(Potemkin village,为了取悦女王叶卡捷琳娜,波特金下令在她巡游时会经过的地方都搭起外表光鲜、造型悦目的假村庄),对普通人没什么影响,也没啥目标,只是满足了当地官僚阶层的需求罢了。政府层级内的低级别官僚主要向直属上级负责,他们并不害怕辖区内的人口。

“面子工程”和官僚游戏
田野调查中,贵州省乡镇一级的地方官员正在忙着做所谓的“政治农业”。据说该项目能够改善当地农业生产,但实际上那是不切实际的,也不会增加任何产量。
地方官员的核心目标是创造一种“形象”,一个地方发展的表象。他们可以通过这类做法讨好上级领导。
例如,地方官员强迫当地农民在县道两旁种上庄稼,这样就能给人一种农业发展取得成功的印象。然而,这种“标准化”在增加收成或节省劳动时间方面没有实际效果。它的唯一目的就是创造一个美丽的发展形象。
与此同时,农民和地方官员都非常清楚,这种“政治农业”的目的实际上不是农业发展,而是关系到个人关系和自己在党内的事业。
在更私下的场合,他们为自己的行为作出了解释。一名地方官员用一句中文谚语解释了他的行为:“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字面意思就是你在江湖上,由不得自己。“江湖”就是社会关系的世界,这个世界外在于“家庭”。
这句谚语还可以灵活地解读成“在家庭之外的地方做事,你就不能随性所欲,而必须做出妥协。”在这种情况下的妥协是指在政府的等级制度内维持个人网络的必要性。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社会网络中,“身体”是不自由的——你不可以用你的身体做你想做的事,而必须根据社会需求来行动。
这里的官员性格各不相同。他们承认,自己在某些场合不能乱说话,需要保持形象。跟官员打交道的农民也知道在恰如其分的时机表达犬儒主义。这里农村的“面子工程”很好地表现了反讽和犬儒主义在行动中的不同影响。
犬儒主义的反应一般只在较为私下的场合才表现出来。然而,人们并不总是犬儒的。这取决于意向性的解释。在反讽中,外部社会传统与更深刻的意义(即“生活本身”)之间的差距较小;而在犬儒主义中,这种差距就变得很严重。
反讽和犬儒主义有着不同的互动后果。具体而言,反讽更多地是为了创造共谋共同体,因为在这里社会公约和“生活本身”之间的差异可以被承认和淡化。然而,如果每个人总是犬儒主义者,那么成立任何共同体都不可能。外在表达与内在意义的差距不断被强调,因而任何建立认知共性的努力都可能导致偏执和精神分裂。
也许在某种程度上,犬儒主义揭示的日常社会批评在许多地方和时代都是常见现象。但是,也有一些特定的社会选择是道德认同的基础,比如现代中国的情况。
可能的道德框架和意识形态的丰富性导致了一个人需要不断调整道德人格,适应“情境现实和现实意识形态”之间的差距。这种调整会产生反讽或犬儒主义。这也从根本上标明了当今中国道德人格的多元性。作为这种多元性的例证,王斯福(Stephan Feuchtwang)引述了刘新的商人的民族志。
刘新表示,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成为了企业家的政治经济学教授。这名教授只是平常当老板赚钱,但他必须解释自己一边当教授一边赚钱是为了赡养老母亲。他对中国的情况采取了犬儒主义的回应,毫无顾忌地成为了日常机会主义者(迎合道德人格)。他的第二道德人格使自己成了孝子的角色。
类似的例子不难找。比如我开篇提到的陈容声称“我们”知道中国的精英政治不过是关系网络和派系斗争,但又会跟我讲很多自己跟他的“兄弟们”(与官商很熟)的故事,觉得人际关系应被一种关乎个人道德的义气和正义所支配。当他谈到他的家庭关系——包括夫妻关系时,一些道德原则会显得更加明显。
结语
犬儒主义会令人失望,也会让人勇敢地接受环境。它就像人对狗的解释,要么是忠实的朋友,要么是恬不知耻的畜生。
在社会交往中,狗的隐喻暗示了人对共同社会习俗的批判。也就是说,将当前的人类社会生活放在一个更基本的层面上,正如我在这篇文章中所研究的隐喻及与之并置使用的多种情况。
我曾描述过一些对犬儒主义的指责或犬儒主义者的自我描述——“狗一样的存在”。不断的咒骂和抱怨可能意味着对价值的不同态度:从属、逃离或挑战。不同人反应各不相同。有些人声称自己是卑贱的,另一些人则借助时间的价值来原谅自己的不道德,还有一些人做着积极的挑战。
所有这些行为都意味着对“社会”的价值进行某种评估,并在更基本的层面上与“生活本身”进行比较,超越了表象和假设。
关于“灰色社会”的讨论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并表明对犬儒主义的描述可以用于各种目的,包括用作道德的基准线。“灰色女性”可能用犬儒主义为自己辩解,半黑半白的“兄弟”组织却用犬儒主义挑战普通社会的双重性。
通过对社会习俗和“生活”的解读,人们采取自我反思和道德立场。正如我们在“面子工程”中看到的那样,这些阐释和道德在社会层面上演,并且能够指向对中国官僚机构的日常运作至关重要的内部人群。朱迪斯·奥丁(Judith Audin)就北京当地居民和居民委员会之间的日常互动提出过类似论点。
对不同社会习俗的批判和对生活观点的批评——这些批评即使出自一人之口,有时也是相互矛盾的——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窗口,让我们了解到当今中国日常生活的自我反思,以及现在人们在不同情境说不同话的能力。
我并没有把犬儒主义作为一种总体性的意识形态来描述,而是提出了一种对当代中国不同类型的犬儒主义的“正式”分析。受这个词最初含义的启发,我试着向人们展示,犬儒主义的话语和行为如何把当前的习俗和价值观与更基本的人类生活方式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他们会对潜在的动机提出要求,或者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应该清楚的是,这些主张在中国是极其多样化的。我引用了一些民族志案例。其中,“生命本身”是从社会习俗剥离的第一个“生命”。这一点从常识性概念延伸出来,即狗(吃屎、不认祖宗)在一个由权力和金钱统治的世界里过着悲惨的生活。
但还有其他一些“犬儒主义”的说法,这些“犬儒主义”藏在人们对更基本的“关系”网络的诉求背后,藏在正式法律条款之后,藏在“面子工程”之后。这里的“生活本身”是关于社会关系的。
我们可以说,犬儒主义意味着各种社会批评。即使这种“社会批评”是相似的——比如把“灰色社会”和“关系”都看作中国政府和企业的逻辑——人们从中得出的道德后果却是多种多样。
这种“正式”或“起码”的犬儒主义有两个关键优点:
- 第一,我们可以对“当前中国是极权主义还是曾经是极权主义的问题”避而不谈。对犬儒主义的正式定义,并不是对犬儒主义的普遍定义,也不是对它的总体性的定义——这种说法经常出现在对犬儒主义错误观念的讨论中。
- 第二,在我看来与这个定义的民族志方法论相兼容。民族志非常适合用来描述和分析各种各样的日常社会批评,以及“生活本身”的隐含意义及其道德后果。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