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香港詩到香港詩人,祛魅的觸動——談許鞍華《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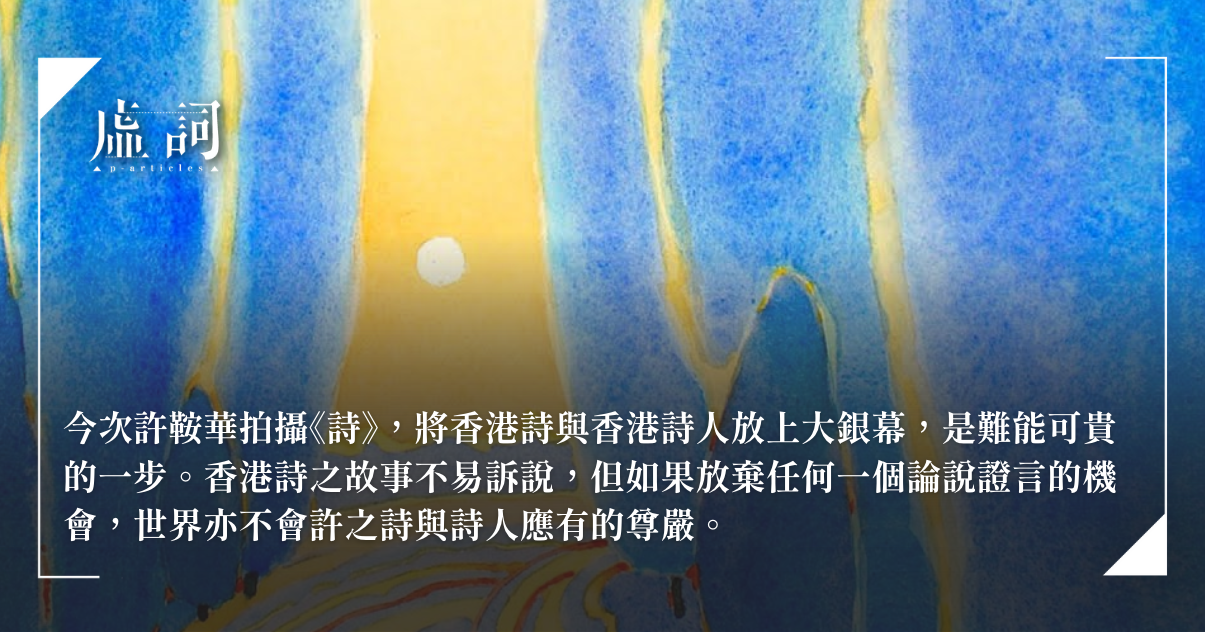
文|李顥謙
即使近年風氣改變,一說到香港的現代詩與詩人,還是可以感到一些文青或評論人的蔑視針對,更徨論當下很多詩人不為人所知的邊緣處境。是故許鞍華的紀錄片《詩》有著一個非常關鍵的意義——香港詩與香港詩人,不僅值得由一位名導演拍進電影,而且更應該獲取一個被公開注視、公開討論,通行於時代與歷史的資格。
有趣的是,身邊不少看過《詩》的詩人文友,對電影沒有太強烈或激動的感受;一些不留意詩與詩人的朋伴,則覺得電影比想像中好看,自言完場後增加了對香港詩與香港詩人的認識及興趣。兩種觀影反應,反映《詩》這部紀錄片的甚麼特點?香港詩的故事難說,許鞍華這次處理文學素材與議題的成效,又是不是一樣難說?
快閃又缺席 香港性的呈現
《詩》主要篇幅落在黃燦然與廖偉棠兩位詩人身上,偏偏電影又在開首的十數分鐘訪問或觸及六位詩人(依出場序計:淮遠、西西、飲江、梁秉鈞(也斯)、鄧阿藍與馬若)的作品與詩觀。熟悉和重視香港文學史論述的朋友不免會冒起一堆問題:為甚麼一部談香港詩的紀錄片,著墨最多的會是兩位青年時從內地移居、現今又離港生活的詩人?如果《詩》要拍的就是兩位詩人的故事,為甚麼又要蜻蜓點水地略提其餘六位詩人?《詩》覆蓋的香港詩人,足夠反映香港現代詩的傳統與多元嗎?
要求許鞍華在個半小時的片長裡搬現一種文學史的論述,無疑不設實際。畢竟《詩》不是一部香港文學史、詩史教材,甚至亦不是詩人紀傳;許鞍華亦多番在訪問提及,不是每個詩人都願意受訪、適合跟訪詳訪的現實。現在《詩》的焦點放在黃燦然與廖偉棠兩位詩人,固然出於許對二人的掌握、詩作的鍾愛,同時受制於不少執行及人事上的局限;與其強行超譯,不如以追訪詩人日常的方式,拍一部思考詩、詩人、香港之間關係的電影。《詩》的結構定調,最後又恰巧地對照一種屬於當下,無可奈何而微妙的香港性。物理上與香港的缺席、割離,反證今日在地詮釋香港的虛無、困難。
開場幾位詩人的出場,表面上是散漫隨心的分享、故友舊情的憶緬,細看卻可窺見許鞍華的心思與功力,簡單幾幕,為香港詩、現代詩辯解,甚至掃盲。比如淮遠一開場就表明不喜語言過於晦澀的詩作,又認為撩鼻毛這等事情照可入詩,向那些總說現代詩詩人賣弄晦澀、漠視生活與真實的言論摑了一巴;接著播出西西在《他們在島嶼寫作:我城》朗讀〈啟德舊機場〉的片段,說明了香港詩人早在六、七十年代就以詩寫城市日常的傳統,勾勒香港詩早有以來的本土性、香港性。電影亦藉鄧阿藍解釋自己粵語入詩的心得、馬若在現代詩裡寫山水言志的想法,同時回應那些批評香港詩、現代詩總是不夠地道傳神,又不具古典詩詞裡自然主題唯美意境的雙重質疑。
祛魅的詩人 同患難與共的凡人
許鞍華為香港詩、現代詩祛魅,到黃燦然與廖偉棠兩位詩人的部分,她亦有意為兩人刻劃較鮮明可感的形象。黃之瀟灑孤傲相對廖的入世勞碌,在銀幕上流露出放大了的張力,可堪比讀,同時更向觀眾強調詩人的真實感——所謂詩人,不過也是充滿著矛盾、需要同生活患難與共的凡人。
電影先呈現黃燦然在深圳洞背村的生活。許鞍華一邊與黃燦然討論詩人何為,一邊跟著黃燦然坐車、到茶餐廳,觀眾得以一直思考詩人獨有玄奧的人生觀、創作觀,一邊感應他生活的樸實,兩者不會違和排斥。像寫詩「搵了自己最大的笨」、從香港搬到洞背是「經濟流亡」這些句子,閃爍住睿智洞見又具黃子華金句式的幽默,令人會心微笑。在人物刻劃的鋪墊下,黃燦然的瀟灑孤傲,那些「詩不能虛榮」、翻譯糊口來達到「努力不賺錢」的生命追求,就變得具厚度、實感的理解基礎。
黃燦然對詩有崇高的想像,他抗拒當下時代流行的、以感人為尺度的詩歌審美標準,言談間強調詩的無用之用、詩神的不可觸及。許鞍華向黃燦然反問了一句:「即是你在追逐追逐不到的東西?」之後亦自覺地點到即止,不再渲染批判,而是以更具象的生活細節,形象化呈現黃燦然的堅執。就如他拿褲到補衣店,指示店員要將褲補得跟舊的線條一樣的片段。那份追求完美無瑕的古典主義精神,從詩藝理想溢染到生活物事之上。
在許鞍華的觀察、敏銳的剪接下,黃燦然更能流露一種脫俗又風塵的人格觀感。他一方面說對香港沒有留戀,另一方面又在將軍澳老家找藏書、念舊親;老像孑然一身,腳上卻刻有女兒名字的紋身。就黃燦然這部分來說,許鞍華已經很成功地塑造一個祛魅可感,矛盾而真誠的詩人形象。
相較而言,《詩》呈現的廖偉棠部分,更著眼於刻劃外在環境對詩人生活與心志的拉扯。廖偉棠比黃燦然年輕十年有多,面對的時代、社會與文化處境盡然不同,即使在台灣疫情最嚴峻的期間,廖偉棠仍得隔離在家講課、開比賽評審會議、照顧兒子。身為詩人、作家的廖偉棠跟大部分普通人一樣,疫裡居家辦工都得面對隨時沒有WIFI的問題。這些日常裡的折騰無奈,很能與觀眾共感。
廖偉棠顯得入世勞碌,身為詩人的他一直清晰地投入以文藝及教育工作主導的生活形態,他自己就在鏡頭前笑言,平日就是不停去開會、寫文、網戰、參與社會活動。這種生活模式令人感到瑣碎、顛沛、耗損,卻是當代華文作家常見的狀態,只是在空間狹隘的當下香港愈見稀有。友人以「紀律」形容婚後維持作家生活狀態的廖偉棠,當中沒有宣之於口的,其實是今時今世,具香港意識的詩人或作家,深層的存在焦慮。
從廖偉棠身上,觀眾還能看到一種逐漸消逝的香港詩人活力,多棲豐富的文化身分特質。在寫作以外,廖偉棠玩音樂、攝影,認識相關場域的創作人朋友,甚至參與保育運動。過往香港詩人流動、自由、隨意累積的特質,甚至香港歷史、文化的重要碎片,都藉廖偉棠的身影,及時地在許鞍華的鏡頭裡留下註腳。
詩的影像化 時代的硬翻譯
作為一部討論詩的紀錄片,許鞍華不得不面對將詩作句子、意象、語境等「影像化」而不失藝術意韻的難題。《詩》選拍的兩位詩人作品大多篇幅較短,指認描述的多是具體的城市空間實景,詩的意與境均不難解,不需要以太大膽驚喜的視覺影像輔以表達。導演嘗試藉這些詩作反映兩位詩人的語言風格與特色,以成效來說不過不失。
以黃燦然為例,黃燦然詩風質樸有力,寫實取向與去修辭化的語言不會給人過於晦澀的印象,許鞍華可以直接地透過演員、處境式的鏡頭,拍出其詩作的質感,令觀眾透過畫面喚召出感情的共鳴、詩意的連結與想像。如處理〈在茶餐廳裡〉時,一邊拍著茶餐廳男人照顧家人進食,一邊伴著黃燦然朗讀「這是知沒有希望的男人/他下輩子就這麼定了」聲音的反諷畫面;〈患難〉拍著黃燦然與許鞍華、家人爬山的辛勞卑微,再嫁接山色與鳥瞰城市的空鏡,鋪墊出呼應「穿透塵霧,向你輸送強光,/我突然感到我一直和你,/並將繼續和你患難與共」的氛圍,深情而堅定。
廖偉棠詩作語言強烈,意象晦繁緊密,時刻扣問個體與社會的關係,在媒介差異與當下語境的影響下,不難想像許鞍華「影像化」其詩作時會遇上的挑戰。廖偉棠朗讀〈皇后碼頭歌謠〉時,銀幕播出當年保育皇后碼頭行動的片段,聲畫交匯,像「我共你煮雨焚風,喚一場熔爐中的飛霜。咄咄,我是一個人,在此咬指、書空。」這種屬其簽名式的狂放尖銳語言,得到具象有力的渲染;而處理〈大角咀尋春天花花幼稚園不遇〉時,鏡頭呈現一系列舊區街景,用以對讀「那些透明的身體裡有心/那些燒鵝有靈魂/窗有撲翼聲」、「他拿著一塊磚頭/敲擊彩虹」的魔幻語境詩句。詩人對社會與流行文化符號的挪用取涉,加上超現實意象與日常事物的拼貼,當中的結合為何、又如何可記認成具現代感的詩意? 《詩》沒有藉詩人之口,解釋更多現代詩語言與意象符號間的操作奧妙,確是可惜的地方。
《詩》還拍下了廖偉棠講解策蘭與布萊希特的片段,最後有點突然地請來九十後詩人黃潤宇談詩於此時的情感力量,甚至連許鞍華自己也現身於鏡頭,表明詩給過自己的慰藉與救贖;而無論是藉二戰外語詩人的苦難寄意、略為直白煽情地強調詩可共感,許鞍華種種勇敢的勾勒,未嘗不可視為對這個失語時代,無可奈何的硬翻譯。
香港詩與香港詩人所受的無以名狀創傷,與城市的變化有著密切關係,奈何始終欠缺一個具能見度的窗口,向外尋話展示。今次許鞍華拍攝《詩》,將香港詩與香港詩人放上大銀幕,是難能可貴的一步。香港詩之故事不易訴說,但如果放棄任何一個論說證言的機會,世界亦不會許之詩與詩人應有的尊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