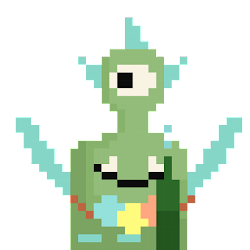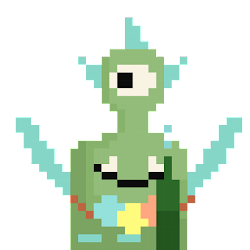進教室,跟台灣高中生聊「港台/社運/書寫」
新課綱的轉變,高中就有多元選修課。張道琪老師策劃了「報導文學」是整學年的課,要培訓高中生去採訪「在台港人」。其中一堂課,便找我去分享經驗。正是今天早上。
為什麼是我?因為 2019 年 6 月,我未有太多準備,就衝去香港做訪調,這種「不專業報導者」的經驗,說不定對同樣「不專業」的高中生而言,會有幫助。
但說到為什麼會去香港做訪調,不得不提到自己參與社會運動的經驗。提到要如何增進受訪意願時,我拿出照片說明「我們希望香港的示威者接受採訪,所以要表示我們對抗爭是友善的,就決定穿這件衣服。你們知道這是什麼嗎?」

我接著說「這是俗稱『太陽花學運』的衣服,那時候,有一群人去佔領台灣立法院,這件上衣也是當時印製,上面的口號是『自己國家自己救』。因為那時香港跟台灣的運動者經常交流,猜想我們這樣穿,會顯得比較友善。佔領開始是三月十八號,剛好今天是八週年。」
張道琪問了學生說「那時候你們幾歲?」
「八歲。」
我問「有印象嗎?那時候有看到新聞?」
他們說「那時候看不懂啦,後來才知道。」
好的,且讓我娓娓道來。
那時候台灣有很多社會運動,也有很多大學生、年輕人投入,我們在台灣參加社運,又看到香港有雨傘運動,那再後來看到反送中運動,其實很自然會想要參加。
但是我們幾副肉體到現場能做的事情很有限,所以我決定做點採訪、問卷,當初是想做點研究,後來便寫成報導。其實我不是專業的記者,可是我能寫,也受過學術訓練,你們問「我是一個社運參與者,還是一個採訪者?」實在問得很好。
我首先是一個參與者,做採訪也仍然是一個參與者,只是位置變了,行動準則的優先順序也變了,重要的是你盡量去聽懂,知道自己在做什麼,然後接受自己在做的事情。

同學們最好奇的問題,仍是「為什麼你這麼勇敢?」「為什麼你會去?」其實每個階段我都有答案,但答案也是永無止盡。
我不擅長在拿麥克風時講一些好高騖遠的話,也不覺得自己有什麼為人師長的條件,能夠去說教別人,但是這種素樸的「為什麼參與行動?」「為什麼想去現場做記錄?看新聞不就好了嗎?」等等疑惑,突然使我腦海裡的一則記憶跳出,這是原來沒有想過要說的。
大學時,我聽學校一個老師叫做廖本全,他參加環境運動,也常跟學生來往。有次他演講,說明當時發生很不公義的事情,最後同學也是對著他問「那要怎麼辦?」老師就往下看了每一個同學的眼睛,說「我就賭你一個。」他說,他就賭下一代、未來的年輕人,可以讓社會變得更平等一點。
我說,或許不是站上街頭做什麼,可是你們選修這門課,你們在升學體制底下,仍然選擇修這一堂報導文學課,也許你們能寫,也許你們喜歡文章,或是喜歡「人」。那就好好對待受訪者,認真地寫字,寫出一篇報導。我不是專業記者,這個時代人人都能寫公開的內容,那就是一種詮釋的力量。我們為什麼還要上課、還要看別人的報導作品、還要一再練習去對人做訪談呢?海量的影片、圖片、文章......你們要慎重對待你們的力量。
結束後我心想,我二十九歲,你們十六歲。我們會老,你們會大。很久沒有這樣說話了,很久沒有想到過自己有這件上衣,很久沒看當時拍的影片,很久沒有回答過這種問題。可是其實在什麼場合,就做什麼行動。再怎麼不擅長,畢竟也是上了這個台。
這(只)是一個高中的講台,它很小,也很大。在這個台上,我終究是扮老了、說教了、理想化了,簡化了許多東西,就像我以前聽過一些不以為然或毫無印象的演講。但這個相遇能催化什麼,或許也要八年十年才能被驗證,而見證的人,或許也不是我們了。
「為什麼明明知道是暴力,還要去面對呢?」有同學課後還這樣提問。
「我們無法消滅暴力,但可以處理『因為暴力而恐懼的自己』。」
「你說個人經驗裡也有暴力,那是什麼?」
「其實家庭、學校、升學這套玩法,對人也可能是一套暴力,只是程度不同,形式不同。有些暴力,你會知道必須站出來抵抗,或者,你在這些經驗裡,能夠學會去抵抗恐懼。」
穿著高中制服、戴著口罩的同學,悠悠從我身旁走過「原來大家都經歷過這些。」
十六歲有十六歲的苦,與那種苦難的深度。而我只能暫時說出我的這些。
年齡與位置可能確實有鴻溝,但希望在不同宇宙裡,我們的精神能夠交會。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