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隔离的与被损害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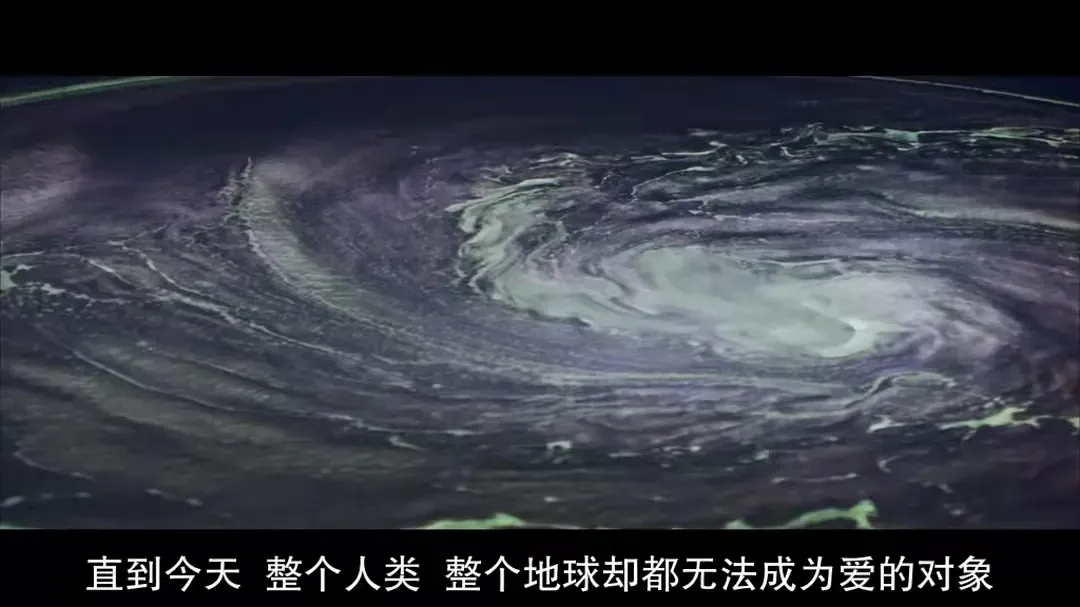
>01 隔离
我觉得自己随遇而安的能力越来越强了,像一只能够钻进任何缝隙里的蟑螂一样,在陌生和不陌生的环境里存活下去。
从西安回来的火车上就在想,如果真的被隔离了,会是什么样?我只是有点心疼隔离费用,至于被锁在房间里,似乎并不是什么难以忍受的事情。在大部分时间里,我也是这样待在宿舍,如果不是生理上的饥饿磨人,可能一天都不会踏出房门一步,然后在手机里留下三位数甚至两位数的步数记录。
但终归是幸运的,彼时,西安还没有特别严重。回来的第二天,西安的朋友发来消息,已经准备封城了,所有人居家办公上学。“非必要不外出”的意思是,你就不要外出了。
我好像有这种逃离事件第一现场的“能力”。五月份广州疫情严重,我也是在封校前不久去广西工地的。出来没几天,朋友圈便是各种排队核酸的消息,以及各种写着“广州加油”字样的图片。而我们呢,在中国南部一个偏远的村庄里,虽然被村干部拉着去打疫苗,但平日里连口罩都不用带。
我不知道自己心里隐藏的对于失序的期待是如何而来,或许是一直有一种渴望“在现场”的机会,像是自己参与了什么似的。
如果此刻我还在西安,会发生什么?青旅还会留人住宿吗?一日三餐能保证吗?是不是和当时武汉那些无家可归的人一样,只能住在桥洞里?但我没有,我的第一现场是此刻,学校里干净明亮的留学生宿舍。一进门,便看到光线肆无忌惮地充溢在房间的每个角落里——比起我住的那个终日阴暗不见光的宿舍要好太多了。米白色的柜子,铺的整齐的床,坐式马桶,桌上还摆放着新的洗漱用品。打开阳台的门看出去,视野非常开阔,而我第一次发现,原来广州市区是能看到山的——之前只是我站的不够高而已——隐藏在高楼后的不连贯的轮廓,阴天里,山体蒙上了一层浅灰色的雾气。
或新或旧的楼,掩映在树丛之间,傍晚或凌晨的时候,阳光会像波光一样闪烁在高楼的玻璃外墙上。到晚上,不同的窗户会投射出不同颜色的光,惨白刺眼的,或暖烘烘的,偶尔能看到人影穿梭。在这个地方,我失去了方向感,除了远方的广州塔,其它的风景都很陌生,而我又实在没有机会多个角度观察以确定自己的坐标。
疫情防控办的工作人员很温柔,并没有为我回来后没有第一时间隔离而责怪我,只是和我交代了注意事项,当我询问是否可以居家隔离的时候,她说,我问问医院那边,你等我通知。
很平淡的一件事情,我连收拾行李的速度都比平时快了很多。
隔离宿舍楼的宿管阿姨问,你是来干啥的?
我哭笑不得,来隔离啊。
她倒是不紧不慢,记录信息,拿钥匙。这时来了一个拿着麦当劳的男生,让阿姨给送上楼,阿姨说,外卖不给进。男生说,这不算外卖吧。阿姨说,这种都不给进的。男生说,XXX(应该是另一个管理员)说可以啊。于是两个人陷入了一场没有止境的扯皮中。阿姨态度坚决,不给进就是不给进。转头向我,“这是温度计和消毒液,你拿好了。”她开始和我说,快递和外卖都是不给进的啊。此时,那个男生开始出去打电话。不一会儿,有人出了电梯拿起了放在外面柜子上的麦当劳,阿姨呵斥到,都说了不给进的啊。我也很诧异,隔离的人是能够随意下来的吗?于是开始了新一轮的扯皮,那个男生一边陪着笑脸一边上了电梯,而他不管说什么都不愿意说出自己的房号。阿姨正在帮我办理入住,一时无法脱身,只能在前台后面低声抱怨,“我一定要和学校反映的,外卖不给进是学校的规定,可不是我的。”我分不清她是和我说话还是在自言自语。这时,另一个管理员走了进来,阿姨的话锋开始转向他,是你和他们说外卖可以进来吗?对方自然是否认,阿姨说,她(指了指我)刚才就在这儿,不信你问她。我顿时有一点懵,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是听到了身后又进来一个人,应该也是来办理入住的,脸上是和我一样的茫然表情,场面一度有些混乱,我只能脱身似的拿上钥匙便上了楼。
不久便有校医院的工作人员来核酸采样,这样的“上门服务”让我有些羞愧,甚至想要发一条“抱歉占用公共资源”的微博。

>02 当下即合理
从出门到现在,发生的所有事情已经足够说明我的幸运了。
那天去火车站,才发现进站需要四十八小时核酸(我承认是我心存侥幸),两点半的车,上午的核酸结果尚未出来,我便坐在外面的长椅上等待,每隔五分钟刷一次行程码。最开始还会期待下一次就会出现新的检测信息,但是渐渐的就会觉得,出不出来一点都不重要,无外乎是退票,损失一点退票费。而在两点十分依然没有结果的时候,我已经在脑海里盘算好了等一下去宾馆吃点什么。我想得到,如果是在以前,这样超出计划之外的事情会引发我最大程度的焦虑,但此刻,我总是能找到另外一些东西转移注意力。
前段时间找出《天真的人类学家》开始看,书记录了作者在喀麦隆多瓦悠人村落田野调查的经历,入境的冗长手续,路上的意外(入室盗窃这种事情都能被作者碰上),永远不会守时的多瓦悠人,各种糟心事儿让他几乎寸步难行。我在阅读的过程中数度感受到作者的崩溃,但是渐渐的,我和他一样接受了这些现实,并开始以多瓦悠人的处事方式看待一切。然后你会发现,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无法完成的事,错过的事,被耽搁的事,都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觉得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我已经没有那么害怕浪费时间了。
以前的我很恐惧虚度时光,就好像睡了一个漫长的下午,醒来时发现黄昏的光已经溜进房间,当下会觉得睡觉是一种罪恶。或许下次睡醒已经是自己的暮年,而我的一生也不过如这个短暂的午后一样,一事无成。
时针转动的速度逐渐加快,忘了曾经以为的“有所成”指的是什么。对于现状没有特别喜欢,也没有特别讨厌,未来没有非常想达致的目标,甚至对明天的饭菜也没有特别期待。这就是我当下的状态。
用以自我约束的“延迟满足”已经很久远了。高中的时候,我可以忍受一个星期做学习机器,然后在周考结束时逛书店,时间不多,一个下午加一个晚上,但已经足够了,这段时光因为之前的忍受而格外美好。而现在的我,能忍受的东西越来越少,“及时行乐”的念头越来越顽固,一面成为一个想到什么就去做的行动派,一面陷入懒惰的泥沼无法自拔。

>03 衣、食、住
这几日风大,12楼,关上门窗的时候能听到外面呼啸的风声,以及不能紧闭的门颤动的嗡嗡声。在这样的时刻裹着被子缩在房间里,很有一种安全感。
每天,食堂的工作人员会将饭菜送来,有六个套餐可选,我看了一圈,始终没有找到自己满意的组合搭配,突然理解了那个说什么也要把麦当劳拿上去的同学。人体必须消耗热量,即使是坐在这里什么也不做,到了饭点也还是会饿。
外面响起敲门声,第一天,我还会急忙走过去开门,然后才意识到,这样的敲门声是不求回应的。哐哐哐,三下,紧接着是“开饭啦”的声音,工作人员将饭菜放在外面的桌子上,同样的声音会重复并远去。其实,在你已经感受到饥饿,并且听到外面有动静的时候,就知道,饭来了,生理本能占据了脑子,甚至有一些莫名的期待。我想,猴子听到饲养员敲盆的时候应该也是这种心情,甚至觉得自己像巴甫洛夫的狗。
发饭这件事让人尊严尽失。
“被饲养”的感觉让我浑身难受,于是并不急于去拿饭,在那段间隙里,能听到其它房间开门的声音,短促的,转瞬即逝。这条长长的走廊两侧,住着像我一样的人,每天打开门的唯一目的就是取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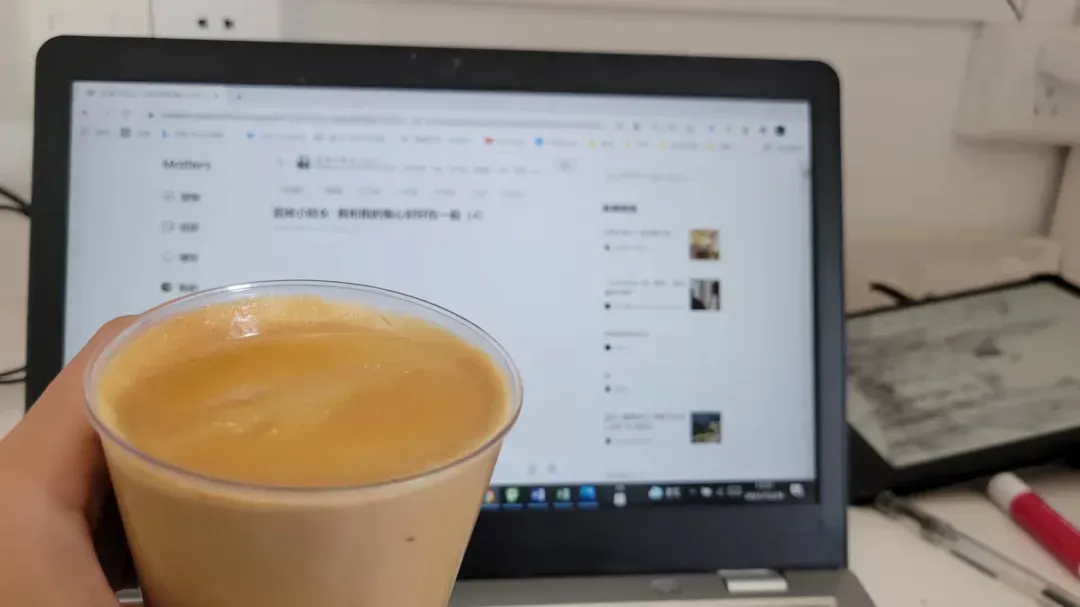
我妈开始每天晚上给我打电话,并且反复嘱咐要多喝热水,多保暖,不能感冒了。我一开始以为她怕我一个人待着太无聊,以及担心感冒会影响体温测量。后来我才意识到,她是担心我真的感染上新冠。在某个晚上,我因为去洗澡没有接到她的电话,出来以后发现她竟然一直在打。我有些困惑,这个点不是应该知道我在洗澡吗?接通之后她说,以为你出了什么事儿。
能有什么事呢?突然晕倒在房间?因为感染了被拉去医院。这可能是她当时的念头。这样,我才明白她为什么反复说不能感冒了,在她那里,感冒=感染,这么说来,逻辑便非常奇怪了,如果真的感染,喝热水就能挽救吗?
我妈眼里的世界非常简单,她是不问前因后果的,并且觉得只要按着她认为对的事情去做,结果总不会太坏。
但是要注意保暖这个事情确实让我头疼,来的时候懒得带太多东西,只穿了一件薄外套,连着几日开始降温,我在房间里被冻得嗷嗷叫,万幸有两床被子,我得以用其中一床把自己裹起来,尽量减少活动。这样一来,连去阳台看风景的心思也无,在外面能待的时间仅仅是一支烟的功夫。
无聊倒是不会无聊,我选择用MC来打发时间,或许是因为自己被困在一个地方,所以史蒂夫代替了我,在另一个世界不停地游荡。我对于打游戏这件事情也上不了多少心,模组下载了不少,每个随便玩一玩就删掉了,技术类的觉得太复杂,打怪类的又觉得太无聊(主要是我太菜了)。绝对不能忘的是打开作弊模式,我的懒惰和急于求成在一场游戏里体现得十分明显:懒得跑了,便直接传输,懒得挖矿,便直接开创造模式,玩了这么久,建造房子仍然停留在造火柴盒的水平。
但是我确实需要这种“自由”的感觉,即便是什么也不做,即使是知道这里的风景一成不变,我也能在游戏里游荡很久。“仗剑走天涯”的史蒂夫足够抚慰人心。
>04 世界被折叠
偶尔也看电影,《不要抬头》让我爆笑了一场。笑有很多种类,大部分情况下我的笑是正常的,但是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的笑里常常伴随着奇怪的声音——面对黑色幽默的时候,人往往是一边笑一边爆个粗口。
电影的讽刺意味很强,在科学家发现一颗即将撞毁地球的彗星,而总统在考虑自己的支持率,电视台在考虑节目效果,科技公司在考虑自己的股票,没有人把这当一回事。他们呐喊过,也沉沦过,配合世界的演出,但最后无济于事,彗星撞地球,big boom!
出现在疫情第二年年末的这部电影,是当下社会的一个注脚。我们人类在面对灾难的时候,可能实在无法解决什么。《三体》里探讨过,如果灾难即将发生,那么地球的组织结构会发生什么变化?是团结一致应对外界侵略,还是分化更加严重?我们确实想象不到政客的思维方式,做决策的是他们,但他们很多时候是愚蠢的。极权当然能够最快地完成一些事情,但其问题在于你永远不知道做决定的是什么样的人。
电影本身当然也是精英主义的,在这里,民众是只会在社交媒体上戏谑灾难,只关注八卦娱乐,在得知真相的时候又只会打砸抢烧以及群交的乌合之众。我想,如果精英们能对民众多一些信任,或许事情也会不一样吧——现实的例子也告诉我们,群众一直都是被伤害者和被侮辱者。

就这么几天的时间,我在新闻里看着西安的疫情越来越严重。先是管制车站,想要离城的人需要开具证明,于是人们奔波在街道办、核酸点,车站之间。然后是小区被封,买不到菜,出门买馒头的年轻人遭到防控人员的暴打。官方发布会直播被各种质疑声逼得只能关闭评论。B类密接的患者主动要求隔离未果,最终感染了全家人。
但即便是加严管控,病例数也在不断上升。有人写,这里的政府不擅管事,只擅管人。
这确实是我对西安的一种感受。住青旅的时候,隔壁床是一个学医的女生,她每天也不出门,偶尔在床上打电话。有天晚上,她突然像是控诉一般地说起自己的遭遇。她参加了西安这边一所医院的培训课程,本来想着提升一下自己,却因为一次请假被扣除一个月的工资,她知道这只是机构敛财的手段,想要维权,而后矛盾越来越大,医院直接拒绝她入住宿舍,并且扣下行李。现在她一直在寻求政府系统的帮助,却遭到了踢皮球式的待遇。女生很激动,一直重复着她的经历,并夹杂着无可奈何的谩骂。
这就是城堡式的故事,普通人在巨大的官僚系统面前的渺小和无力。城堡就在那儿,可是你就是接近不了,抵达不了,负责人在电话里推诿,她就得继续待在西安浪费时间。
这一切让人觉得仿佛回到了两年前,新闻里到处是荒诞而忧伤的现实。
一个女性在隔离时来了月经,无奈只能向酒店管理人员控诉,疲惫的身体,年幼的孩子,阴冷的房间,冰冷的饭菜(甚至还未准时送达),以及不断渗出的血。视频里是她颤抖的哭诉声,而对面那个工作人员面无表情(可能是在口罩后面看不出),这样的场景让人无比绝望。
拼命回家的人各显神通,骑车从西安回淳化,步行入秦岭山区,甚至横渡渭河,新闻里称他们为“楞娃”。在全城防控下,他们是三个异类,以不够体面的方式出逃,被抓,被戏谑,还有点滑稽。但是我们不是一直在失去体面吗?
隔离是将人突然扔到了另外一个环境中,它剥夺了正常的社会网络和行为方式。以一张纸条贴在门上,但纸条并无封锁的实际功能,它仅仅是权威和管制的象征。三餐需要被送达,但其它的需求不被承认,人被重构成了一个只有进食需求的动物。如果管理者误读了这种情境并因此认为自己获得了什么权力,裂痕会急剧扩大,任务至上,人位居其后。即便是优越的隔离条件,善解人意的工作人员,损害感也会存在。而你知道,疫情时代,全世界都在共享着这份伤害。
北边疫情正凶猛,南边,立场新闻被封。这两件事像是一个互文,提醒着被夹击在中间的我们,或许所有的事情都有因果,“命运馈赠的礼物,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

>05 跨过旧与新之间
到年末,各大APP的年终总结又开始了,即便是一个不喜欢这种总结的人,也被迫受到各种数据的冲击。这一年,听了多长时间的歌,看了多久的书,甚至是吃了多少钱的外卖,加在一起便是你了,一个由物质欲望和精神欲望交织而成的个体。
除了给个人总结总结,各种媒体也开始总结过去这一年里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情,当然,有太多的事情被404了。一个印象是涌动在互联网上的各种狂热,抵制失德艺人,抵制眯眯眼,抵制抵制新疆棉的商家。在这里,我看不到任何可供判断的边界,一切好像都在靠着一双无形的手被推向前,要你存在你便存在,要你消失你便消失。
《先生制造》给这一年的总结是,沉默,然后第二天它便沉默了。
我觉得我还有哭泣的冲动,但是也仅限于哭泣而已了。

跨年和元旦,一个人待在这里,也听不到外面有什么声音,还是会有点孤单。新的一年和过去的一年没有什么变化,我甚至连flag都不想给自己立了,但毕竟得要面对现实,这一年我大概率要面对一些痛苦的时刻,特别是在过完年以后,我也知道这是每一个毕业生必须面对的。
思来想去,重新打开了招聘软件,刷着刷着便失眠了。
还是那句话,焦虑每个人都有,只不过是时间先后的问题。我确实是很善于逃避和掩饰,甚至是自己骗自己:我面对现实是舒适自洽的。《观看之道》里讲现代广告所打造的“魅力”,它必定是冷漠的,这样才能得到他者的妒羡。对,我就是这样陷入到现代消费主义陷阱之中的人——必须与现实保持距离,由此才能维持自己的自尊。
《荒原狼》里写,“不能爱生活,不能爱人,不能爱我自己,不能严肃认真地对待生活,对待别人和自己,对生活要求很高,对自己的愚蠢和粗野又不甘心。”这样的人,当他安于现状并且待在舒适圈内的时候,大抵是自洽的,因为现实能够给予他足够的肯定。可是当他有所求的时候,当他知道自己的能力匹配不上其所求的时候,痛苦便是席卷而来的海啸,让人没有挣扎的余地。
我打开自己的豆瓣年度报告,“你在娱乐小组里待了多少多少小时”,我是有些震惊的,自己是不是如我以为的那样自律呢,很明显不是的。大部分时间,我连自省的自觉都没有。吃饭的时候,睡前的时候,写了一会儿论文想要休息的时候,我不是都在随意刷着手机吗。其实情绪本身也是要消耗能量的,无能量消耗的心理活动,只有麻木而已。
我很少点开一部电影了,我发现很多时候自己都在找恐怖片看,这意味着我的情绪需要被唤起,而不是自己带着情绪进入到一个世界中去;我的阅读很多时候是基于习惯而非求知和好奇,而阅读完毕,也仅限于“知道了”而已。
——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旁观者,他在世界的外面,焦灼地寻找着能够进入其中的门,一面徘徊,一面假装镇定,然后拿出相机对着世界的外墙一顿拍摄,告诉别人,这是美的。
为什么我热爱隐喻,热爱顾左右而言他呢?因为我根本恐惧真实的表述。看李诞在《脱口秀表演手册》里写,脱口秀演员在舞台上不断暴露自己,如此他必须本身是一个善良的人,他的暴露才能够为人所接受和喜欢。这样一种暴露或表达之于我,便是蒙了一层纱的书写,是一种闪烁其辞。
或许是隔离到了第十天,人已经有点疲倦了,并且对外面有了些许的渴望。这隐射着现实的状态:隔离结束了,你终究还是要面对外面的世界。
>06 尾
隔离第十天,开始睡眠困难,借助播客入眠。
隔离第十三天,鼠标突然没电。感觉自己失去了一只手,并且有了不写论文的借口。
四日,西安宣布社会面清零。隔离结束。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