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 | Corona读书会第32期 | 松茸的时日
这是一个起源于疫情期间的读书会。底色是人类学,但疫情的复杂性很快溢出了既定的学科边界,读书会也逐渐转化为议题导向的半公共讨论平台。疫情和疫情次生社会现象之外,Corona关注的议题包括性别与LGBT、美国黑命攸关运动、基建、诗歌、他者、全球灾难政治等,也力图对紧急议题做出反应,如就洪水策划的鄱阳湖批判历史地理学和大坝与水利政治的讨论。有意加入或主题投稿的朋友请在后台留言。
笔记整理小组将逐渐把此前讨论的笔记上载在结绳志的Corona专栏。本期刊出的是第32期关于边疆采摘的讨论。从Tsing的《末日松茸》出发,讨论西南诸菌与人类的关系。采摘、产业、边疆、自然范畴的演变;多物种民族志导向的是人类世的自觉还是松茸多时间;种植园和产业链的谱系纠葛、采摘直播等新landscape及其fetish内涵各种诗学与政治。
第32期Corona读书会 / 2020年10月31日
主讲 / 晓清、缪芸、一谊
参与 / Corona的朋友们
书记 / Poco
阅读书目 / 见文末
一本完整的书及其复调
晓清:这本民族志,没有参考文献,所有的资料都组织在notes里,与书的主体部分浑然一体。这里,我也想一反seminar阅读中的理论构架的解读方式,用多次阅读中发现的不同风景,也就是作者在书中一直强调的landscape地景,和大家分享。这本书我大概读了五六遍。
第一遍读的时候,是跟随作者。
罗安清Anna Tsing生于1952年,是加州大学san cruz分校的人类学教授,也是人类学界近年来最受关注的学者之一。文化人类学家传统上擅长对人类社会及其文化进行分析,以及通过跨文化比较来分析不同人群、社会和文化间的关系。而以罗安清这一支的人类学家则呼吁应该把“自然”也纳入考量。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要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她本来只想找一个具有跨国色彩的研究标的物,结果变成一个让她上山下海、从森林走进实验室,充满合作和意外的计划。这本书就涵括了美国俄勒冈、日本中部京都里山、中国云南、芬兰(北部)拉普兰四个不同田野点的见闻。从序言部分可以看到,选择松茸,一方面因为松茸能够忍受人类制造的环境失调但又不可被人类规模化种植,这种跟人类的关系很是奇特。另一方面,它作为一种在日本历史上扮演重要角色,承载文化象征意义的在地食材,随着工业化、资本主义的发展对森林环境的破坏,逐渐在本国失去了立足之地。反而,在世界的其他地方生长起来,再通过商品供应链返回来供应日本国内,并且为不同的松茸进行排名估值中又折射出全球贸易评估的多种形式。在这个松茸故事链条上,作者又把重心放在了被忽略的行动者——松茸采摘者身上,由他们串起了一系列事件和网络,包括中间商、买手、保值票市场、购买者等各个主体通过不同的政治经济技术规则联系的松茸市场,他们的案例成为以往全球抽象/地方具体化两分法的替代,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各个具体因素的聚簇。同样,作者也消除了谋生优先和保护环境利用生态资源之类的简单的二元对立,展开了被战争的记忆所纠缠的人生、森林砍伐、气候变化等等复调的故事,这些不可能构成完美结局的小故事组成了这本书出人意料的叙事节奏。从而,整本书给人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它不是以往的认识体系,像树那样讲究线性发展,讲究源起,有高下等级之分的那种传统写法,而是成为水平方向上的链接拓展,像人参、生姜这类块茎rhizome类植物,无根无茎,无枝无叶,无始无终,永远都是正在“生成中”,而不是“本体的存在”。块茎强调连接、异质性、多样性,而且赋予空隙积极的意义,即使砍断也会生成。这个概念来自法国哲学家德勒兹和瓜塔里。后面再读时我们还会和他们隐隐约约的相遇,并且将接触到第二个重要的概念assemblage,书里面是翻译成了集合体,但现在觉得聚簇可能更准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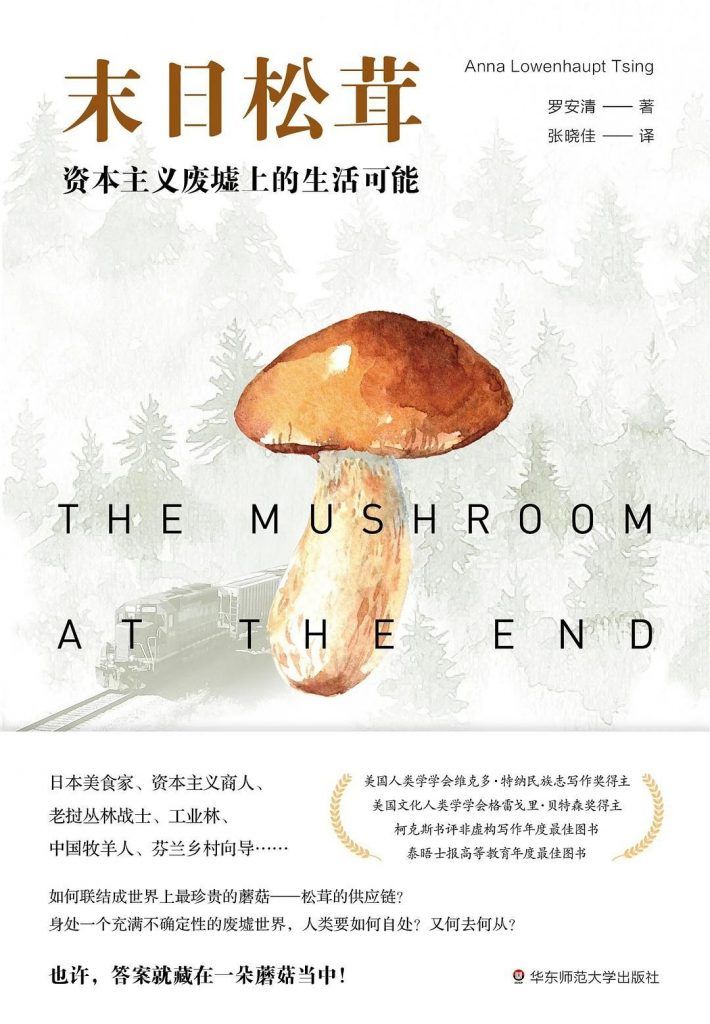
以上是这本书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内容。全书一共四个部分,到后两个部分时,作者继续追踪松茸的踪迹,离开商业,进入相互缠绕的生命形式。这可能也是有些读者读着读着开始困惑的地方。作者也做出了预警,如果大家仔细看的话,在p190.她说这是在概念和故事之间建立起一道失败之墙的结果。理论家们在概括出普世原则之后,期待其他人会填充“细节”,但“填充”从来就不是那么简单。这种知识工具就在概念和故事之间架起高墙,使得研究者们原本有意提炼的敏感意义也逐渐消失。我们习惯了把所有的知识实践(包括我们的内省、神话和传说、谋生实践、档案文献、科学报告和实验)分解成一个个单一的程序,但作者试图帮助我们打开,打开一个分层的、异质的,由不同认知和存在建构的,可能相互交染的景观。接下来概括一下后两个部分的内容。
一部分是由蘑菇展开的种间关系的知识。
一部分是干扰,作为一种工具,作为一种方法论。
蘑菇是真菌的一种,真菌许多人认为是植物,实际上更接近于动物,它不从阳光中摄取养分。这里稍微补充一点生物学知识,真菌是在体外而不是体内消化,就是说,它在摄入食物的时候,会滋养其他物种,比如真菌会消化岩石(和细菌一起)创造让植物生长的土壤,也会消化木材,将它们分解成营养物质,从而被循环利用于创造新的生命。所以,真菌可以说会营造出一个地方的种间关系。世界上很多受欢迎的蘑菇,如牛肝菌、鸡油菌、松露、松茸,都是通过种间关系而存在的,与宿主树共同茁壮生长。而且,它们的菌根互联,可以帮助森林面对威胁时做出反应。作者从中得到的启发是,这种物种和物种间共生的关系,对我们习以为常的进化论中的种间关系——捕食、猎物关系是一个反常理解。它们不是消灭对方。长久以来,我们熟悉的是自私的基因的故事,不需要合作者,可规模化的生命在自我封闭和自我复制的现代性中捕捉到遗传基因,这就是韦伯所说的“铁笼”iron cage。但其实还有另一种,许多有机体只有通过和其他物种的相互关系才能发育,我们命名为“突变”。作者在追踪这个章节里提到,有一种乌贼,必须在海水中遇到一种特定的细菌,才能发育出发光器官,这个发光器官是模拟月光,将自己的影子藏起来躲避捕食者,看起来是个非常重要的器官,但幼年的乌贼不会主动长出来。但它不一定会遇到这个细菌。所以这个事情充满偶然。物种间的相遇是一次次不同的事件,而不是一个内部自我复制的系统。所以没办法标准化,规模化,规模化需要但研究逐渐发现,共生才是规则,不是例外。自然可能是在选择“关系”,而不是选择个体或基因组。这里,作者提到了,真菌,是一种指南,一直反抗着自我复制的铁笼。而共生关系,我们常常用“外包”这个比喻,但其实生物过程和商业规划的比较无法一一对应,始终有一条,不可规模化,不可被简化为互换对象。他们需要遭遇,需要邂逅。进行自然历史的描述,而不是数学建模。迫切的好奇心正在召唤我们,也许一位人类学家,在为数不多、重视观察和描述的科学中接受的训练,可以发挥作用。
不习惯思考“干扰”的人文主义者,常常把这个词和“损害”联系起来,但生态学家使用的干扰并不总是负面的,也并不一定是人为构成的。用作者的话来说,干扰和万物并存,干扰始终追随着其他干扰,干扰是常态。提出干扰的问题不会中断讨论,反而打开了讨论景观动态的大门。
不同于让森林自我恢复的观念,日本人提出要干扰森林,制造一种混乱来帮助松树,从而帮助松茸。这里提到的复育计划,人类活动应该和非人类活动一样,成为森林的一部分。共同参与景观建造,人类、松树、松茸都在无意中相互培育。人类和他者一起创造了无心设计的景观。景观本身是活跃的,是正在形成中的,可以看出人类和其他生物在塑造世界中的携手共进。

把干扰作为一个起点,行动的开端。
我们不习惯一个故事里没有人类英雄。但在这个人类只是参与者之一的冒险故事中,作者把景观做成了主角。干扰作为一种分析工具,需要意识到观察者的视角,这个相当重要。单一的评估干扰的标准是不存在的。干扰从来不是“是”与“非”的问题;干扰指涉一种开放的、不定的现状。过度划分的界线在哪里?干扰总是与视角有关,从而也就是基于生活方式阐发的问题。干扰是一项很好的工具,可借此对全球/地方,专家/民俗的知识展开多种多样的分层。
这里要指出的事,物种也并非总是讲述森林生命的准确单位。“多元物种”这个术语仅仅是超越人类例外论的替代词。但是一个人使用什么单位取决于他想讲述什么样的故事。
第二遍和第三遍都是在校订译稿,编辑读书稿和读者读书的一个区别可能在于,细节,细节的冲击力特别强。
到第四遍读的时候,正是做这本书稿的复审,正是在三月疫情爆发之际。可以这么说,直到2020年3月,这本书的中文书名还叫做“世界尽头的松茸”,因为当时已经看到对台版译文的一些商榷包括书名,at the end of the world在这本书里更指向一种空间上边缘化,而不是时间概念。但二三月份的时候,面对当时疫情的困境和愤怒,一方面时时反思自己作为学术出版人到底能做什么,一方面突然发现编校这本书稿让自己从一种无望甚至可以说比较绝望的状态中获得了力量。这里要补充一句,松茸英文版出版是在2015年9月,当时大家还未曾预见2016之后Trump的上台、阶层种族的撕裂以及新自由主义积习已深的恶果。在Trump上台后,荒废的制造业地带(last belt)事件被报道,我才开始关注那些寻找工作的人们,也就是处于不稳定状态的人们——不稳定者——的呼声,对书中强调的不稳定性、废墟还没有那么强烈的感受,而且无法想象世界要如何从线性进步观中抽离出来,给高歌猛进的世界踩刹车是多么不可能的事,而简体中文版准备出版的2020年春天,我们看到了世界的摇摇欲坠,仿佛末日来临。书中对人类对其他物种的那种经过简化之后的食用-可食用关系,习惯了人类作为所有故事的英雄主角,不断攫取资源,让那空间异化成废墟,然后抛弃,去寻找下一个可以为资产生产、剩余价值牺牲的地方或物种,大规模裁员,正规雇佣(以前的铁饭碗或者说结实的饭碗)稳定工作成为幻想,面对病毒这个物种人们一开始的希望寄托在气候变化上,…仿佛成为一份面前世界的说明书。有一句熟悉的文学对白是“回不去了”,我们真的想要回去吗?实际上,20世纪的资本主义中,给了我们进步许诺和GDP无限增长永远在发展的经济,其实是由低价丰饶的资源做支撑为代价的,在资源枯竭、气候变化加剧的情况下,这所谓的“回去”是不是还要走那条路?如果眼看着是走不通的,那我们是不是要正视,这种“不稳定”“不确定”的状态才是我们的常态?我前不久看到一个澳大利亚学者做的采矿业的多物种民族志研究,他研究气候变化带来的温度上升、地质融化对采矿者的影响,当代采矿活动正在加速分解(有机物、沉积、森林和北极生态系统的生长)和重新形成过程(物质资本、流通、市场价值和资源增长)——遥远吗?但想一想这半年翻番的黄金价格以及动荡世界的对金矿业的索求吧,猛犸象的化石都可以让我们心中一震。

如何应对不稳定不确定的状态呢?松茸和它的伙伴们给了启发:合作共生。不要仅仅追求自己的内生发展之路,而是依赖多种生计和环境可持续性的其他行动者。大家还记得前面提到的松茸、松树和其他生物的故事吗?所以,那个时候起,我开始深刻觉得松茸这本书不仅仅为学者,学术圈所有,它应该面向更多的受众。它所激发出来的那种温暖的力量,可以传递更远。这里还要岔开一句,我们的图书出版除了大家熟悉的书号,就是就算isbn之外,还有一个数据是CIP,cataloging in publication number图书在版编目码,这是一个按照中图法分类的编码。之所以突然科普这个知识,是因为,如果买了这本书的同学们可以看到,它现在已经被分到了F类食用菌供应链管理,而不是通常社科图书所在的C类或大文学类I类,用世界尽头的松茸做书名,真的很担心它被视为是一种讲边疆蘑菇的生物书。我们希望“末日”两字带有的某种情绪可以让它见到更多的陌生的人文社科的读者。好,再回到合作共生带来的力量感。合作共生不是简单地描述一个“在一起”的状态,而是包括人在内的不同物种聚集后之间如何互相影响,相互生成。这里还要提到一个donna haraway提到的圈层性,spheric,通常认为这个观点来自于日本,森罗万象shinra bansho指的是“宇宙中的一切”或者是“天地间的一切创造”,我们人类在其中只占很小的一部分。这像一个把所有东西装起来的袋子,是生命存在的世界,是所有的物种和物质,以及在天地间所有物质的相互联系。这种无差别的群体的概念特别重要,这是根茎与块茎之间充足的混杂(the rich mix of roots and rhizomes),并且拥有巨大的生物数量。这个观点挑战了一直以来西方科学中我们熟悉的区隔,迫使我们去思考一种整体上纠葛。这种打破区隔的尝试可以说是一种同盟alliance,像学科之间并不需要接管对方才能一起工作。合作并不意味着你要融合所有的学科来制造某种新的混杂物。你们是盟友allies。事实上你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坚持自己的学科,因为只有当你们有分歧并开始相互交流时,你们才能在新事物上面进行创造。
松茸产业和采摘实践:在地的观察
缪芸:松茸产业在中国也有一些特点,一,松茸时效性很强,快递业的发展促进了松茸的产业链。顺丰连续7年在香格里拉市开发布会,要全力支持松茸产业。后来更多快递进来了。二,还有电子商务,不仅仅靠大的出口,也更多依靠朋友圈的微商、淘宝等让人们认识松茸。三,吉迪村的个例来说,因为《舌尖上的中国》得到报道,销量很好。
具体到迪庆藏族自治州。书中说,森林里采摘者是自由状态,离开森林则变成了资本化的运作。让我想到微商对松茸的表达,会有一些颠倒。藏族朋友他们会说松茸如何养生,非藏族的朋友反而更多讲自然的馈赠。香格里拉本身带有异域想象,对藏族文化、藏族生态的想象,这是松茸在自然和文化方面的附加值。其实,采摘松茸不是那么浪漫。菌子在雨后才有,人们要把土刨开。人可能会有关节炎,不是那么浪漫,但是卖松茸的时候会浪漫化。
松茸也是一个交易链。村民其实是在交易链的底端,松茸有地域鄙视链。据说,香格里拉的松茸比较多比较好,比较紧实没有虫眼,旅游发达,交通方便,形成了一个交易点。附近四川藏区的也会来卖,本地人觉得是冒充了本地的松茸。我对规则如何建立很感兴趣。吉迪村形成了规则——下午四点的时候会形成本地的交易市场,有些人为了获得更新鲜的菌子就到村子里蹲点。这些具体内容有待进一步了解。

中间商到村子里收,到市场里卖。云南是多民族聚居的地方,回族有做生意的传统,以前虫草生意回族做中间商的比较多,现在微商的兴起,各种各样的人都会去守点。大多数的藏族村民不是直接在线上卖的,也没有在城里卖,因为这样时间花费多,他们又缺少关系,不一定卖出去,所以宁可卖给中间商。一到松茸季节,整个云南都开始卖松茸了。销售需要关系网,当地村民没有这种关系。还有人开直播,但有影响力也是少数。
松茸作为一种副业。书里说到,移民到美国的瑶族等人群采摘松茸为生是理性选择的结果,他们认为金钱不如自由重要,松茸也联系起了他们的旧有习惯和乡愁。也有不是移民的人,比如逃离战争阴影的白人。迪庆的藏族村民不一样,对他们来说,采松茸是一种副业的补充,不是完全依靠松茸作为来源,而是季节性的、不稳定的、依靠外来人的生计来源。我去的村子,每年每户依靠松茸可以赚5000-20000,比小麦收入更多,但是他们在重要性上把小麦排在第一,蔓茎第二,松茸第三。他们特别提到了今年的疫情,觉得能自给自足的话,在村里呆几个月都不用担心 。这也可以看到,他们对稳定生活的需要,也是基于对外部环境的认知。
人们是会有务实的心理。但是,也不是完全功利的。比如说村民就会说,种地的好处是,不像上班要去打卡,种地有一定灵活性,累了、下雨了就可以不去种地。采摘松茸也是。我们有在村子里做培训,村民没有接触过制作酵素的事,但是他们愿意来学习,他们不是为了得到一个目的性很强的成果,而是愿意尝试新东西。他们在松茸季节不挖松茸,而是来学新东西。这说明他们一方面是务实的,但也不是功利的。
关于资源的争夺。随着虫草和松茸生意的兴起,村与村行政划分的边界就变得很重要,极端情况下会有打架。甚至出现了地理位置上有优势村制造麻烦让另一个村断水断电的情况。但是村子而言,文化上有解决方法。比如,一篇文章说,虫草资源在村子间分有争议,但两个村子同属于一个寺院,有同一个幼儿园,双方达成和解了。还有一篇文章讲的进村采虫草有进山费,但会对非本乡的人会收得更多。藏族文化中人们会讲因果。我认识的村子,僧人会告诉村民,你的福报不会因为和其他人分享了而减少,村民会允许附近村的人来捡松茸。但还有一个客观原因是松茸刚出来的时候,村民正在收小麦,没有时间,他们就允许其他村的人来捡松茸。
很多人看到松茸或者虫草会联想到自然破坏。云南虫草比较少,四川、西藏多一些。挖松茸之后要把土盖回去,让它以后能再长出来,也不能挖特别小的松茸。大部分人会注意这一点。也有人在改变。就像种茶叶一样,有的人会用农药,会砍掉其他树来种茶树。但他们意识到了这样做对生态不好,或者也因为商业环境对茶叶品质和自然保护的要求,也会有一些回归。
人类学、人类世与生态女性主义
一谊的分享分为几个部分:1.arts of noticing;2.人类学对人类世概念的批判性介入;3.自然与资本;4.生态女性主义的进路。
一个部分就是arts of noticing。在这一片资本主义的荒芜当中,你还剩下些什么?在这本书的第一部分,它是从美国的奥勒冈州的山区开始的,为什么说奥勒冈州的山区会是一个资本主义的荒芜,20世纪初,伐木业开始出现。1930年的时候,奥勒冈州已经成为美国整个木材输出最大的一州。我们喜欢把它说成好像是一个进步的故事,一个目的性很清晰的故事。但是罗安清说的不是这个故事,她要说的是一个在1989年之后,伐木被视为是一个对于自然生态的有序发展不利的行业,因此被禁止了。一片发展的泡泡被击破之后,到底这片山区资本主义的废墟当中还剩下些什么?what’s left,留下什么,如果是我翻的话,我可能会说还剩下些什么,但是留下什么的确是比较希望的,也是一个有历史性的译法。书的开头就带领我们进入一个罗安清对于什么是美国的完全不一样的articulation,不一样的描绘的路径,这个路径牵涉到对于人类世整个概念的批判性的介入。
2019年,Jason Moore摩尔教授来到台北,做了《人类世或资本世?气候、权力、资本造成的地球危机》的演讲,在里面他比较清晰的爬梳了人类世到底都在说些什么,比较流行性的说法,它是一个强调全新世的结束之后的新的地质时代。大概在2000年间,有一些地质学家和科学家认为从工业革命开始,人类对于整个全球地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最重要的是碳的生产数量之大影响了整个地质的组成。但全新式的终结,它不仅仅是地质物理上的转变,也代表了资本主义本身的 state shift,我们不再能够把人类放在全球环境变迁之外,我们不能够再简化的把自然生态和人类分开来,成为一个二元对立的认识论的范畴,它也加深了一个叫做“没有生态的人类” Human without ecology的情况。这里也是一种所谓的人类特殊论,当代的人类学中,社会学家或者是地理学家的批判性的介入,都会试图去谈说我们要怎么样把人类对于整个环境生态、对于地球的基本状态的影响看成是一个权力、政治、资本交织于其中的一个历史性的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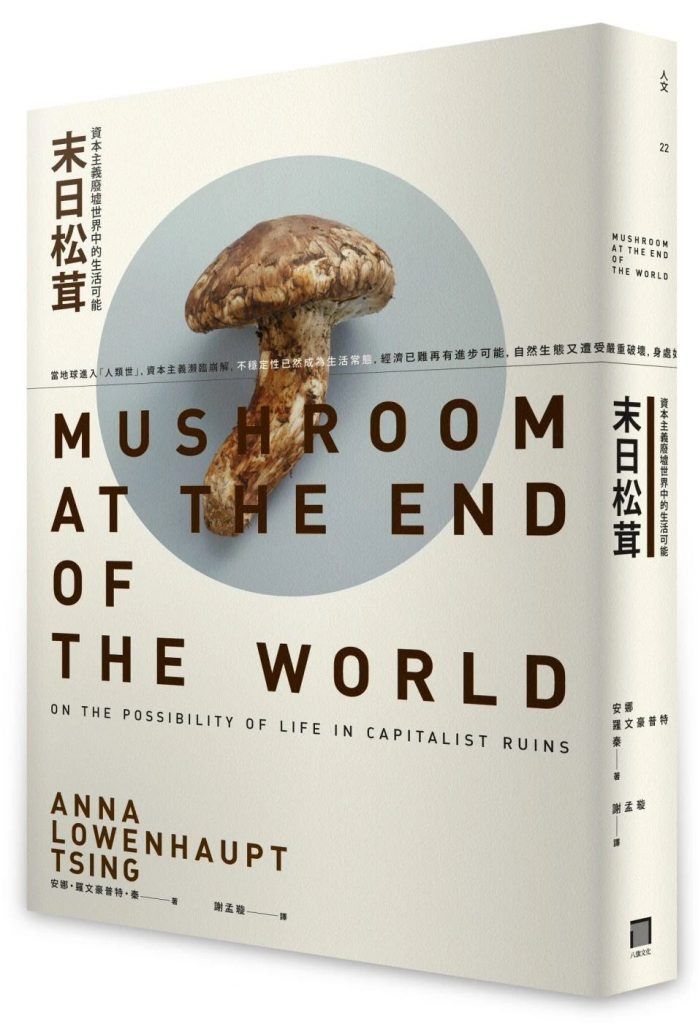
2010年Cultural Anthropology 这本重要的期刊上,刊登了一个特刊 《多物种民族志的出现(Kirksey, Eben, and Stefan Helmreich 2010 “The Emergence of Multispecies Ethnography.” Cultural Anthropology 25, no. 4: 545–76),宣告一个新形态的民族志写作,它事实上不再是以人类特殊论去讨论当代全球生态变迁的状态。2020年, Andrew Matthews在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里面写了Anthropology and Anthropocene,说罗安清这本书不仅在理论上重要,在方法论上更重要,打开了多种民族志怎么写,写的时候有什么基调,用科学的、客观的、学科在上的、理论先行的写法,还是用和读者对话的、亲密的语调,诚恳告诉读者自己是怎么进入这样的议题。思考的过程中有哪些人加进来了。这本书给我们的启发是,理论的内容跟民族志的内容,还有民族志怎么呈现,怎么样不用一个对立性的方式去说故事,而是用一个合作性的方式去说故事,在形式上有相当大的突破性。
这本书不只是好读而已。我第一次读到书里面的几个章节是2007年,在纽约的人类学导论的课上,一直到15年出书,有超过10年或者说将近15年的时间了,她一直很坚持某一些思考的路径,一直持续问一些很困难的问题,坚持问这些很困难的问题。这些很困难的问题牵涉到自然与资本的交互形成的问题。回到刚刚讲的书的第一个部分,奥勒冈州为什么会成为一个资本主义的废墟?在89年伐木业消退之后,失业的白人、二战之后到了美国的南亚难民、一些新移民或者是墨西哥移民各方非美国主流中产阶级群体的人就去聚集在资本主义的荒芜当中,在这个荒芜里面又生出了一些新的生命形态,透过松茸连接出来一个新的社会性,一个很有趣的网络,除了从生物学的角度去看,菌菇做体外繁殖,改变了或者说触发了环境的种种的新的生命形态的发展,同时它又影响到新的人和人之间的形态的连接。这个部分非常不同于我们熟悉的古典的政治经济学或者说当代的政治经济学。它们思考资本问题的时候,用一种比较普世论的角度去看资本的问题。资本生成的世界,每一个世界都牵涉到在地的人跟物的状态,因此中国的脉络也是非常重要的。人类学谈自然与资本,不要去重复了自由主义经济学或者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对于所谓的什么是经济,什么是生产的种种的这些既有的概念,我们不是在做物化,就是说把资本的逻辑再度套用在自然或者看世界的方式上。事实上对罗安清还有同行者来说,是希望能够有一个新的arts of noticing,一个新的看待世界的方式,这个方式它必须要很具体从每一个人或者说研究者自己的研究脉络里面,去看到这一些无视既有的资本理论里已经告诉你的事情,而是要跟民族志的材料有很深的关系,长时间一起工作,长时间一起合作,找出一个可以看到一些不容易被看到的面相。
再稍微补充一下,俄勒冈州成为美国当代资本主义的废墟荒芜的过程,不是一个理所当然的历史进程了,美国的整个资本主义的荒芜化,也就是学界说的后工业化的状态,其实始于1970年代美国的资本家银行家想要去对抗68年之后美国让社会更平等的发展方向,所以银行家、石油企业家才有一个新的集结,他们希望能够松绑各种环境的法规,还有金融环境的法规,可以做更高风险性的金融行为,所以奥勒冈怎么会变成资本主义的废墟荒芜,牵涉到整个全球的新自由主义。70年代后期,全球新自由主义对于我们整个社会到底应该怎么样被想象,社会公益是什么?公共是什么样的东西?有一个被洗牌的过程。这个部分不管是政治经济学家或者是人类学家都在某个程度上是同意的。

我们要怎么样面对这样子的一个世界?生态女性主义者有不一样的想法,透过这本书,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不一样的进路。二战之后法兰克福学派,欧洲犹太分知识分子流亡到美国的这群批判政治经济学的阿多诺、霍克海默以批判作为一个进路。生态女性主义稍稍不一样。生态女性主义怎么去面对资本废墟?对于这样的不稳定的生命状态,有什么样子的建议?不是说这个是一个末世论,研究资本主义的学者或资本的学者并不是这样子的态度。面对不稳定的生命的状态和经济状况,我们怎么样去回应呢?就要回到罗安清怎么结束这本书。结尾里,她告诉你作为一个当代学者在当代的新自由主义的世界里面的局限,告诉你,还有一些同行者,还是有一些共同一起工作的朋友,除了arts of noticing,除了我们每个人必须要去面对自己周遭的各种生命形式,各种生命政治之外,我们还要去交朋友,有更多的勇气进行一些比较困难的合作,因为合作事实上是很困难的,我们每个人可能都希望今天能够照着自己的形式去工作。有一句话不是说如果要走得快就自己走,如果要走得远,就要有同行者。生态女性主义的进路,事实上是非常在意同行者。
Donna Haraway 有一本书是staying with the trouble。不要害怕这些困难的议题,在不放弃、不把问题视为理所当然的过程里面,怎么样坚持去问这些很困难的问题。这个trouble实际上是一个动词,就是不要害怕去trouble,不要害怕去制造这些麻烦,不要害怕去问这些很困难的问题,stay with it。它不是抽离式的,或者想要超越。我们必须要打开的是什么东西是可以被看见的,什么东西它是往往被隐藏的。就像罗安清在废墟里面迷路,刚开始她觉得地上什么都没有,一片荒芜,都是沙子,遇到了两位采集者,透过这些采集者,进入去看到一些很难被看到的多物种的交织的状态。在看见看不见的光谱当中,有很多是每一个研究者对于什么是可能什么是不可能的想象的尺度,这样的尺度的打开,不是一个个人的尺度,而是一个合作的尺度,一个对话的尺度,是一个不断的在困难的对话当中,不去害怕这些困难,不去把这些困难美化浪漫化。特朗普上来之后制造了更多的不稳定,更多的麻烦,在令人感到不舒服的世界的状态之下,我们其实就更需要生态女性主义。它一直是提醒我们说不要那么快地想要去跳过这些不舒服的不愉快的问题,而是stay with the trouble,然后找到同伴,在过程里面一起往前进。
讨论
Salvage/攫取式的打捞积累:翻译与辨析
一谊:对自然的攫取,实际上是 primitive accumulation,或者是最近大家要翻了另外一个方法叫做original accumulation,是原始积累的概念,是一个攫取的概念。appropriation 如果劳动力有进行加工,那么就有劳动的时间性和生命进去,但是矿业林业的话,比较多的是叫做original accumulation,自然被当做是一个廉价的取之不尽的东西,这个是工业化之后,我们把自然当作是廉价自然,自然被廉价化,被化为廉价自然里面的还有奴隶、被殖民者、女人、边疆,当这些都被化作是廉价自然的时候,就可以被无偿的取用了。无偿的取用就变成所谓的original accumulation的逻辑。罗安清的进路是用salvage攫取式的积累,松茸的民族志看,不是打卡进去,早八晚八的这种工厂模式,是一个采集者的模式,但是这采集者也不是自然的分工,是一个二战后的脉络,是美国工业主义,美国资本主义冷战的脉络。所以攫取积累是可行的翻译。我自己的翻译是拾荒积累。这些概念要被谈得更多。
晓清:打捞、捞捕不像一个新词,所以采取了攫取资本主义。新的名词欢迎继续讨论。
本书对行动的启示
一谊:我没有办法替她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怎样去理解资本世界,是第一件事。articulation往往会决定行动能不能打开。这涉及用一个什么样子的本体的角度或者什么认识论的角度,用一个实证的角度,用一个历史的角度,不同的角度有它角度的政治就在里面了。我觉得她的态度来说,学者的工作可能更多的是在这个角度的琢磨上,怎么说事情,怎么样去做一个问题的描绘,也关联到当代人类学有关本体论的世界成型的讨论,比如说法国人类学界在谈当代政治的时候,谈的不是要很快能够找到共通性,而是说在我们分享同一个世界,我们怎样去面对20世纪的问题,殖民主义所带来的有关自然的概念,这样子的一个历程。如果你从这样的历程去看,不同的人在不同位置上面所形造出来的不同的世界,可能 articulation都还没有做到。不同的声音都还没有被听见,看不见的力量都还没有被清晰地描绘的时候,有关集体行动的宣言manifesto到底是不是包容性的?必须要有一个更细致的继续trouble它的过程。罗安清比较早在Fiction里面就去质疑说,全球这个想象是从哪里出来的,这个想象本身要被质疑。Jason Moore就有一个比较历史学的取向,他说这是在68年之后,美国激烈的反越战的批判声浪之后,尼克森总统想要去收服这些社会批判的声音,才转向了一个要去提出自然保护的概念,想要消弭政治性,所以全球或者说集体行动这些概念,要怎么样去放置到每一个行动者,或者社群的脉络里面,你的集体性是在什么样基础上面,想要导向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未来的想象。在行动跟概念之间,要有一个比较细致的处理,还是在staying with the trouble。生态女性主义里面好像有一些评论人说不支持比较具体的社会改变,实际上不是的。在知识性跟概念上面的重新的反思,怎么样回头去看你自身的周遭的脉络,再来往下去想往再去做对话,这个是我自己读的一个体会。
松茸采集对外部全球市场的依赖性
缪芸:松茸不是当地人主要的收入来源,他们要做一个选择,究竟花多长时间做。松茸和虫草不一样。虫草价值高,可能成为一年全部收入。但是松茸的价值没有那么高,可消费人群更多,是比较分散的形式,买卖双方都比较分散。全球化的联结来说是低端、分散的全球化表现。可能和我们以前看到的是不一样的。
生态女性主义的议程
一谊:Donna Haraway也有一些口号,staying with the trouble。make kin, not babies等都是在政治上比较前进的想法,但是她们不要复制政治经济学对于资本逻辑的强化。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读这本书可以读出另一个系统,松茸的价值很大程度是象征性的,珍馐是文化价值的问题,价值是有波动的。要从资本内部外部去考虑它,要从人类学价值理论去切入。具体的政治行动是不是民族志的工作?在民族志之内之外做了什么?格雷伯在知识上很细腻深入,但在政治上有另一个层次。他们有一个网站,东西非常多,很多的合作。
晓清:刚刚在问说外部性它到底有多少?我在看书的时候,一个比较深刻感受就是一直在强调各种异质性和分层性,不是像我们想象中的一个固有的逻辑,要一直追问下去,一直要你打开自我。我编辑的另一本书,提到病原体和环境的关系。一些笼统的解释比如城市化说全球变暖或者森林开发工业养殖等,笼统的解释会掩盖它可以从多角度多层面的思考的这种路径。所以我的补充就是说我们可以有一种叙述的实践,也可以去发现其他的参与创造历史的这种方式。可以更具体一点,可以更突破一点原有的边界。
【阅读材料】 Tsing, Anna 2015 The Mushroom at the End of the World. 梁雅茜 虫草、藏药与西藏的全球化 调查|被夺去生命的拉姆 【辅助】 松茸价值链的文化嵌入 In 《生态人类学》 Donna Haraway and Anna Tsing Reflect on the Plantationocene Andrew S. Mathews. 2020 Anthropology and the Anthropocene: Criticisms, Experiments, and Collaborations.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Writing and rhythm: call and response with Anna Tsing and Paulla Ebron Intro In 《帝国之裘 清朝的山珍、禁地以及自然边疆》 Intro In Schmalzer, Sigrid. 2016 Red Revolution, Green Revolution: Scientific Farming in Socialist China. UChicago Press.
欢迎通过多种方式与我们保持联系。
独立网站:tyingknots.net
微信公众号ID:tying_knots
【倾情推荐】订阅 Newsletter
成为小结的微信好友:tyingknots2020
我们来信、投稿与合作的联系地址是:tyingknots2020@gmail.com

目次(持续更新)
- About us | 一起来结绳吧!
- 进口、洄游与误归:三文鱼的驯养经济与后新冠时代的多物种认识论
- 口罩为何引起热议
- 结绳系疫 | 错过新冠革命:后见之明与民族志知识
- 结绳系疫 | 后疫情时代的后见之明与具体研究
- Corona读书会第23期 | 医疗基建 Medical Infrastructure
- 新冠疫情会长久地改变洗手习惯吗?
- Corona读书会第6期 | 动物、病毒与人类世
- 非男即女?:生物学家有话说
- Graeber | 中文里的格雷伯
- David Graeber | 萨林斯悼念格雷伯
- David Graeber | 论飞行汽车和利润下降
- Graeber+Piketty | 劫富:关于资本,债务和未来的交流
- David Graeber | 傻屌:解开“领带悖论”
- David Graeber | 过于关怀是工人阶级的诅咒
- Graeber | 互助也是一种激进:恢复“冲突与和平之真正比例”
- 国际聋人周的礼物:一份人类学书单
- 「修车大水,就是我想要的生活」——自我去稳定化(self-precaritizing)的「三和大神」
- 算法文化与劳动分工:启蒙运动中的计算
- Graeber | (反)全球化运动与新新左派
- 书讯 | 英文人类学新著 | 2020年9-10月
- 欧洲以东,亚洲以西:后冷战世界下的中亚(上)
- 欧洲以东,亚洲以西:后冷战世界下的中亚(下)
- Corona读书会第30期 | 把XX作为XX:方法、地方与有机知识分子
- Graeber | 如何改变人类历史的进程(至少是已经发生的那部分)
- Graeber | 大学死了吗?人类学与职业管理阶层的兴起
- 马克思、韦伯、格雷伯:学术与政治的三种面向
- Corona读书会第7期 | 全球公卫中的跨国人道主义 Transnational Humanitarianism
- 书讯 | 英文人类学新著 | 2020年夏季
- Corona读书会第28期 | 大坝与水利政治
- 特朗普人类学(一):手、谎言、#魔法抵抗
- Graeber丨格雷伯与科层中国:从《规则的乌托邦》说起
- 黑色海娜:对苯二胺、孔雀与不存在的身体
- Corona读书会第32期 | 松茸的时日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