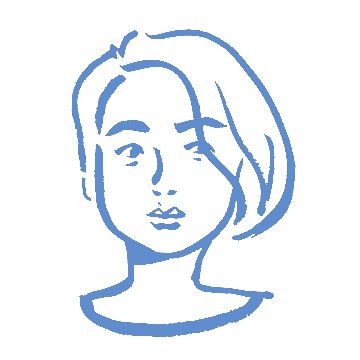来美国九年后,我看了第一场NBA现场比赛
20岁的篮网新秀托马斯,用几个干脆利落的假动作闪开防守。他后跳一步,跳跃,腾空,出手,三分,球进了!整套动作一气呵成,行云流水如同舞蹈。我惊呼,“真漂亮!”。全场起立喝彩,观众沸腾了。连一直默默看球的男友也鼓掌叫好。
虽然不懂篮球,比赛刚开始连主客队的篮筐都没分清,这并不妨碍我看的起劲,乐在其中。直到坐在狭窄的座位上,还是如临梦境,不敢相信自己真的在看NBA。
想起出国前要好的同学写信给我说,
“…去纽约的话,一定要去看布鲁克林篮网队的比赛。”
当时我对纽约的印象完全来自好莱坞电影里纸醉金迷的画面,对布鲁克林的印象也只有《布鲁克林有棵树》里励志的小女孩。谁知道纽约也有数不清的流浪汉。谁知道后来我会住在布鲁克林,离篮网队主场只有几站地铁的地方。
中学那会儿,班里的男生不是迷足球就是篮球,迷篮球的不是迷科比就是詹姆斯。我也对科比有好感,可能还因为喜欢他的长相,黑人球员里少见的清秀。
还记得刚听到科比飞机失事的消息时,我感到头晕目眩,难以置信。不是总有人编造名人去世的事吗?何况他才41岁。我甚至以为伟大如科比,如霍金,因为成就斐然,被神赐予了免死金牌。却忘了科比也是肉体凡身。那是我第一次被生死宿命的无力感笼罩。如果科比都会死,谁不会呢?当和我们同时代的传奇逐渐湮灭,我们的死亡也不再遥远。
来美国后,有太多事要学习和适应,篮球是最微不足道的。忙碌中一晃眼,已在纽约待了第九年。美国的主流运动中,我依然不知道棒球的规则,也看不懂橄榄球员的横冲直撞。但有天我在电视上,看到哈登和布兰特的镜头时,脑子里突然冒出来同学的那句话。我决定,要去现场看一次篮网队的比赛。
到了比赛那天,晚上七点,我和男友看中了中间位置的座椅,原价要(税前)300刀一张票。等到比赛开始前最后半个小时买票,能便宜至少一半。最后我们以(税前)125刀买到票后,我激动地朝球场快步走去。本以为疫情期间,又是寒冷冬夜,看球的人会少点。结果到跟前才看到乌压压排队的人群。入座后环顾四周,发现差不多90%的座位都满了。
比赛开始前,照常由歌手演唱国歌。意外的是,全场起立为本周牺牲的两名纽约警察默哀。
除了比赛本身的精彩,我的眼睛总是被各种各样的细节吸引。比如空中的电子屏幕打出了中文的拜年字样;进球时金币碰撞的清脆音效让人极度舒适;球员一跑开,就一手一只白色抹布跪在地上光速擦地的工作人员;身着黑白条纹短袖,单手扶着一箱啤酒高举过头,逐层叫卖的男人。他的手臂显得那么粗壮,腰身又那么灵活;普通观众被镜头捕捉到后,开心的手舞足蹈;我知道和不知道的名人被拍到,又一次引得全场尖叫。
当比赛暂停和中场休息的时候,主持人为活跃气氛,还设计了许多节目和游戏尽兴。原来卖力歌舞的拉拉队员中也有男性,原来扔衬衫的时候会用到一种像“高射炮”的工具,后排的观众也能有机会拿到。这些都是我从没想过的。我最喜欢的是响彻全场的喇叭里解说的声音。在主场队员进球后他会变着花样的念出球员的名字,在客队进球后语气就像周一上班那么低落。虽然看不到脸,他雄厚的声音充满了夸张的表情。可直到比赛结束,我和男友也没有在一万人里找到解说究竟在哪。三个小时里,整个球场开了一场盛大的派对。不同种族性别年龄的人齐聚一堂分享篮球的欢乐,此时此刻,人们暂时放下了差异和偏见。
现场的热烈气氛确实是电视转播比不了的。虽然一切都很商业,但快乐是真实的。哈登并没上场,远远看见他穿着鲜亮的黄色连帽衫和牛仔裤,两臂交叉坐着观战,嘴唇从一把大胡子里露出来。尽管连杜兰特的影子都没见着,我已心满意足。
看球的时候,我突然有点想告诉那个同学,“我终于去看了篮网队的比赛,真的很好看。”不过我们已经很久不联系了。
有次和仅存的国内朋友聊天,我们说到特权这个话题。我的观点是男性生来比女性拥有更多特权,这让我忿忿不平。聊天框里冷不防跳出一句话:“那你也有特权啊。不是所有人都能像你高中就去美国念书。”表面上我云淡风轻地回应他,“是啊,我承认。”但我的心揪了起来,下意识有一丝想要反驳的不甘。
的确,我动动手指买票就能看NBA,而我甚至都不喜欢篮球。我的球迷同学,有多少非美国的篮球迷可能一辈子也不会来现场看一场比赛。但我又无法不想到那些才几岁就被父母带来看球,穿着球衣吃着冰淇淋,笑容天真的美国小孩。他们第一次看NBA是六个月,一岁,还是三岁?我已经25岁了。
就像美国同事聊天时说到,“我基本每个夏天都去佛罗里达度假,去了太多次都烦了。”美国朋友从小去过很多次迪士尼。我还是没去过佛罗里达,加州,拉斯维加斯和迪士尼,还是插不进她们的谈话。
从16岁到25岁,来美国后的九年里我一直在打怪,过关斩将:语言障碍,文化差异,家庭变故,经济拮据。我求学,搬家,打工,毕业,求职,搬家,离职,升职…在去年终于找到了收入还算不错的一份工作。这些年来我觉得自己都在跑步机上,边跑边走,不敢停下脚步,怕被生活甩落。终于得来一份暂时的安稳,可以喘口气了。因为经历了过山车般的起起落落,这喘息的片刻对我来说弥足珍贵,又怎么是一句“特权”可以概括的。
之前看到一张“特权计分表格”:根据人的出生地、种族、性别、性取向等等指标对其打分。特权越多,累计的分数越高,反之分会越低,甚至成为负数。最后总分只要大于0都是有特权的。我很兴奋的做了这个测试,也叫身边的朋友去做。但细想来,这张表格多大程度可以当真。我们要如何评比自己身上重叠的种种因素?比如一个家境殷实的异性恋黑人男性和一个贫困的同性恋白人女性相比谁更有特权;或者一个白手起家开了餐馆的华裔移民,和一个生于美国却领福利度日的贫困黑人相比;一个在中国被遗弃后被美国父母领养的亚裔女性,和一个富裕中国家庭送出国留学的亚裔女性相比呢?特权可以被量化吗?如果可以,怎样算公平?
我的中国同学看我,和我看那些白人同事,是否是一样的感受。
我们这么容易羡妒高位者,同情低位者,可我们如何看待自己?
当西安的父亲居家隔离几周不能出门的时候,我在纽约排着长队检查疫苗卡去看一场球赛。场内观众不时摘下口罩欢呼,聊天,吃薯条和汉堡,喝冰啤和鸡尾酒。我在兴高采烈的人群中,神情自若,又看到自己的特权。
2022年1月26日,星期三。这天我第一次看了NBA现场比赛,篮网队六分输给了掘金队。这天也碰巧是科比去世两周年的纪念日,他还是41岁。如果有下次,我想看一场篮网队获胜的比赛,那会是另一种感觉吧。
(完)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