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博读到一半,我的导师搬去别的国家了
上两期里所写的 H 的故事收获了比较多的留言和关注,感谢大家的喜爱。管理好自己的 ego 和期待,以及遇事采取主动出击的姿态,算是我从 H 那里学到的人生课了。 采访最后 H 提到自己理想中的实验室是一个成员之间能自由沟通合作而不是只有彼此竞争的环境。我当时插了一句嘴:“哎,那你说的正是 dry labs 了。” 今天就讲一点 dry labs 的故事吧。
§ 巧了,我的项目也横跨两个实验室
K 所在的项目是另一个欧洲的计算神经科学领域的跨国博士项目,共有将近十个学校和国家参与,他本人是纯理科出身。
我认识 K 是在研究所的厨房里。我们研究所有一个大厨房,由于研究所位置离学校食堂较远,我们平时都自己带饭,在厨房里热一热,和同事们边吃边聊。

在一众穿着套头衫吃着黑不溜秋的土豆茄子或者意大利面的同事里,只有 K 不仅每天穿着笔挺的衬衫领带,还带着很丰盛的午餐,有菜有肉有饭,有时候竟然还有烤羊排。K 是伊朗人,他来读博时带着自己的妻子,妻子平时就在大学里别的实验室做做助理工作。有人互相照料的 K 生活得很得体,生活态度也很积极。
K 所处的项目横跨德国和瑞典的两个大学,项目本身也非常鼓励国际化教育。经过几番筛选和面试后,远在伊朗的 K 获得了这个来欧洲求学的机会。K 的项目设计比起之前的 wet labs 的合作更灵活一些,学生可以自由选择学校和导师,再根据项目进程分配在两个学校的时间。
据 K 说,在搬家、找房、签证、语言课这些令留学生头痛的 top4 事宜上,项目和学校也都提供了很多帮助,他们的生活相对容易。
§ 友好的同事环境帮助我快速融入
语言障碍一直是我比较关心的。看过第一篇文章的小可爱可还能 recall 那种在休息室里当植物的 social pain?
但是 K 说:“刚来德国时的确有一点语言问题,但是慢慢发现,研究所里的外国同事居多,平时几乎是英语交流,同事们也都很友好,所以慢慢地就从 uncomfortable 变成 comfortable 了。”
更幸运的是,德国和瑞典的同事都很友好。
“我在德国度过了三年,在瑞典度过了六个月。我觉得很开心也很顺利。” K 说,“德国对我来说是家的感觉。我在这里学习和使用一种 simulation 技术完成了研究的主要部分。随后我们发现可以再使用另一种模型来完善这个项目,所以我才去了瑞典。

“我去瑞典只学习了六个月。我想要学习的技术是已经毕业并且在本地工作的同事建立起来的。因此这位同事每天下午下班以后就来研究所对我进行义务教学。他对此也很开心,就是自己虽然毕业后没有再做科研,而自己一手建立起来的模型还能继续创造价值。
“这些经历对我的帮助很大,最后我的论文完成度很好。我觉得从科学上来说,我也在两个 scope 不同的实验室里获得了互相加成的训练。我很感激这个项目。”
的确,答辩结束后, K 的导师说会推荐他的论文去学校评奖。
§ 读博到一半的时候,我的导师却搬去英国了

但是 K 并不是一直这么一帆风顺。
在我加入研究所不久以后,就发现 K 的导师怎么不在这里。原来在 K 读到博士第二年的时候,导师就获得了英国的永久职位,把整个实验室搬走了。
由于非欧盟学生在英国要缴纳很贵的学费,导师的研究经费无法负担,最后导师只带走了来自欧盟的两个学生。剩下 K 被留在这里远程培养。
这个故事的走向对于很多人来说,就有可能 BE 了。在博士生涯初期就要跟导师分开,我身边遭遇过的朋友们都表示非常艰难。
但是 K 说,导师虽然搬走了,但好在人还是很负责。
“我们经常开视频组会,而且我的论文有95% 的讨论都是跟这个导师完成的。他的贡献真的很大,一直在尽力为我提供帮助。”
K 并没有多说这个过程是否不易。我猜想要么是 K 很坚强也跟导师保持了良好的沟通,要么是做理论计算工作的独立性比做实验研究稍强一些。虽然跟导师不在同一处,K 的项目一直按照比较正常进度在进行,加上德国的研究所里还有很多友好的同事,热烈的学术讨论和欢乐的社交生活从未停止,K 才顺利度过难关。
等到 K 毕业的时候,他已经搬去英国的同事们还专门回来参加他的答辩,为他制作博士帽(德国的毕业习俗)。
§ 如果非要说遗憾的话
在我采访 K 时,他已经答辩结束了,妻子随后也顺利生下了可爱的女儿,他们打算搬去另一个地方开始博后生涯了。
我问:“那你觉得这几年有什么困难和遗憾吗?”
K说:“非要说困难的话,其实最后的答辩过程需要合并两个国家的程序,答了四个多小时,真的挺费劲的。还有就是论文格式也比较麻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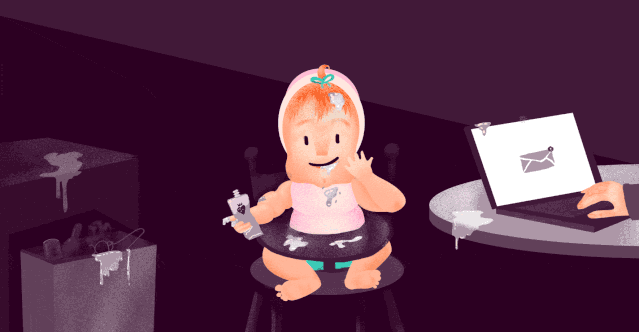
“导师的话,我挺感激他们的。但我的主导师未婚,我觉得他有时候可能不理解有家庭有孩子的学生会面临的特殊的困难。
“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我论文写作最后半年需要延期六个月,当时我的主导师有一些资金困难,而瑞典的导师一开始表示她会支持,却在最后含含糊糊不表态。而与此同时,她却给自己瑞典实验室的学生续上了延期。可能,我们这种 joint student 跟 major student 在这些方面会遇到一些待遇上的差别吧。”
§ 后记
关于 K 的访谈故事比较短也比较积极,毕竟我写作的初衷不是为了卖惨而吸引眼球。在采访了越来越多的人以后,我发现求学生涯中有很多普遍的问题,每个人随机分配到其中几个。事实上,也并不是所有困难都只会劝退。希望大家能看清困难的实质,想到办法度过自己当前的难关。
家庭、朋友、健康都是关键时刻的救命绳索,祝愿各位不必身陷绝境。另外,友好积极的环境对所有人都有益,如果可以的话,在保护自身利益不被侵害的前提下,尽量与人为善吧。
这是我写的博士生访谈系列的第五篇,原文发在公众号 “汉莎路第九号” ,感谢 matters 的读者喜爱,我有空会把后续文章搬上来。:-)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