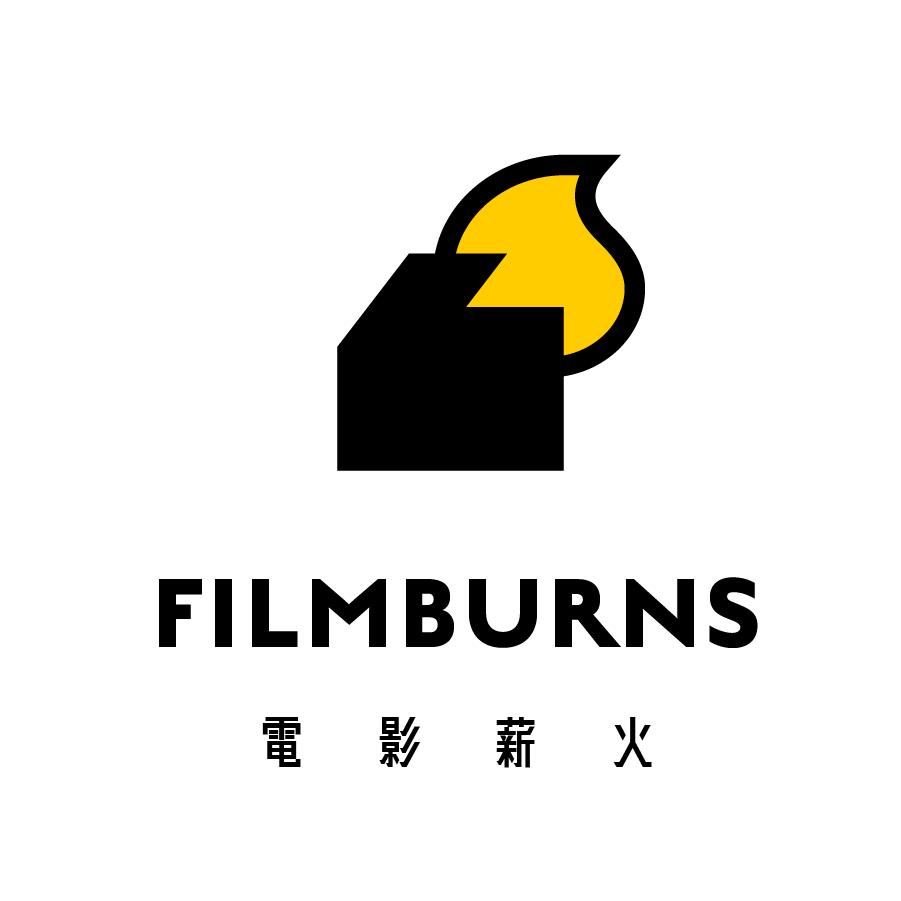《新活日常》:好好生活的修煉

文|劉境南
觀影期間心情一直忐忑,畢竟一個德國知名導演受政府和財團所託,以現代化的東京廁所作為主題,拍攝一個熱愛文藝的日本廁所清潔工的日常,歌頌其敬業精神。這樣的碰撞,怎樣想也有點錯位。即使撇除可能發生的東方主義凝視,精英階層對勞動階級生活的理想化投射,難免亦是一大擔憂。抱持忐忑看了上半場,一方面被主角平山寧靜富足的內心世界所撫慰,另一方面糾結於應否保持行車距離——那個優雅和善、一塵不染,每天哼唱英倫音樂、用富士相機拍攝樹影、睡前看文庫本的獨身男人,果真如實地反映一個廁所清潔工的形象嗎?

如果電影所說的,僅僅是任何人都可以擁抱當下每個美好時刻,那很可能我會抱持以上疑惑直至完場。幸而劇情發展至中段,由主角平山的侄女突然造訪開始,這種擔憂得以慢慢緩解下來。
雖然電影沒有明說,但從他分別與侄女和妹妹的對話,大概可推想出他曾經有過的不如意過往。平山的情緒一直醞釀至妹妹接走侄女之後,一直冷靜自如的他終於淚腺崩堤,身影在昏暗燈光下顫抖,這是電影首次表達他的孤單。夜裡,他夢見侄女、單車和燈,還有一連串朦朧的影像,然後沉沉睡去。翌晨,他被屋外的打掃聲吵醒,然後起床刷牙換衣,喝一罐咖啡,一邊聽著卡式錄音帶,一邊駕車上班。表面一切如常,但他並非忘了昨夜憂傷,也不是故作堅強,只是生活依然要過。
更重要的是,在無所欲求的外衣底下,平山擁有對未來的盼望——與侄女共度的最後黃昏之下,女孩要求看海,卻被平山拒絕:「下次吧。」女孩問:「下次即是何時呢?」平山:「下次是下次,現在是現在。」對啊,還有「下次」的日落可以期待,而眼下的現在,亦有書本、音樂和植物作伴,還能奢求甚麼呢?

這情節將平山在鏡頭下理想化的生活,一下稍稍拉回現實,倏然與熒幕外的觀眾接軌。無論 Wim Wenders 在電影中夾帶多少私貨,他又帶著怎樣的眼光看待日本及其勞動階級,想表達的內核卻是人類共通:不論表面多麼地了無拘束,每個人都背負著自己的巨大人生,小心翼翼地踽踽獨行。但日子始終要過,既然過去無法改變,何以要勉強自己?不如專注當下與將來,在舒適區中尋找生活的避風港。這種選擇當然不是毫無代價,與家人近乎斷絕聯絡便是其一,做著旁人眼中不亮眼的工作是其二。因此平山最教人敬佩的,是他始終以豐富的內心世界面對孤獨,對抗不友善的外來目光。
平山的經歷總算合理化了他對現狀的選擇,但假如將他放諸一個藍領去看待,看似悠然的「文青」生活習慣能否繼續成立呢?然而愈是思考這個問題,便愈覺得這個問題很有問題。癥結在於:若果我們說這是精英階層想像的童話,認為清潔工哪有閒情逸致看書聽歌,那何以就不是一種歧視?早前《窄路微塵》上映時,也有人質疑拮据的單親媽媽外型時髦,恐不符現實。但又是誰說「基層」必定打扮隨意,沒有對潮流與美好生活的追求?
同樣道理放在平山身上,他的生活其實並不奢侈,只是上班途中聽聽喜歡的音樂,然後勤懇地工作,午間看見美麗的樹木,就拍一拍照;看到樹根旁掙扎的孤單小草,就帶回家好好裁種;下班後泡個舒服的澡、吃餐飽飯,睡前看看書作為固定的娛樂而已。這些習慣花不了甚麼錢,他單身、沒有兒女,又不用供養雙親,絕對負擔得起。因此真正需要思考的可能是,當我們在為「被理想化」的基層生活抱不平時,值得同情的,會否反而是鏡子映照出的自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