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虛詞・過敏鳥】「用神用竅,令你會更多感覺」的填詞人周耀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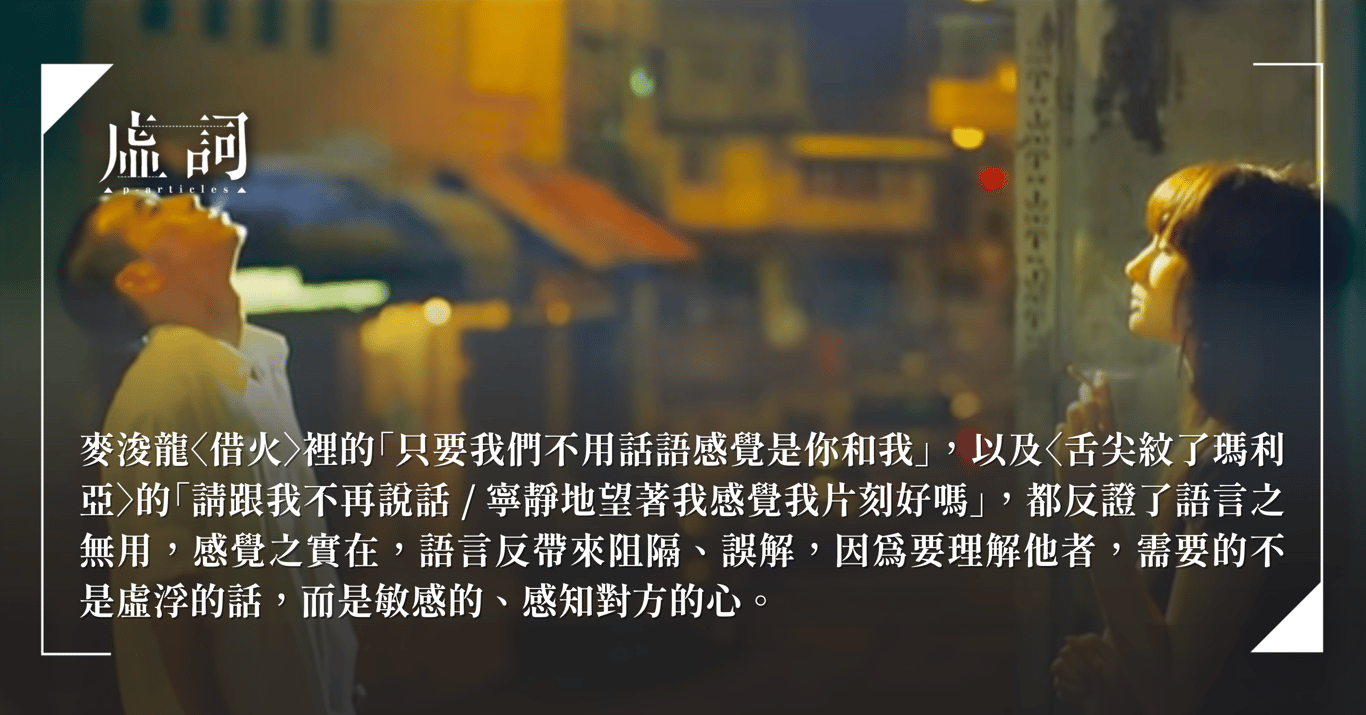
文|陳芷盈
「我們必須敏銳,因為世界太想我們麻木。」周耀輝曾在訪問裡如是說。
一分鐘也要捉緊,但求剎那的烏托邦
周耀輝的敏銳,始終如一,說的這個一,是一日、一分鐘、一剎那。〈從此世界多了一分鐘〉、〈今天只做一件事〉、〈剎那的烏托邦〉,都將一刻化作無限大,一切情感都在那壓縮的一點中爆發。
去渴望、相愛、感覺,是對抗麻木的武器。生於我城,忙碌的生活與狹小空間,幾乎不容許情感的宣洩,麥浚龍的〈從此世界多了一分鐘〉道出這個困境,主角但願擁有「24:01分」,在短暫的一分鐘內盡情與愛人相愛,抵達副歌部分,感情壓抑的歌者如解開枷鎖,聲嘶力竭地教人抓住此刻的感覺,「當能渴望就渴望 / 無論以後歲月有幾多」,希望「就此可以多一分鐘跟你去張狂」、「虔誠地快樂」甚至「揮霍」。張狂、虔誠、揮霍,這些詞語的情感力度非常強烈,因為愛的真貌,正是一種傾瀉情感甚至自我的迷狂狀態。麥浚龍另一首歌曲〈我們的末日〉,歌詞也寫到時間有限,愛有盡頭,那麼在末日降臨、情感耗盡前,就要「盡量將你與我流露」,即使只有「一分鐘亦要捉 / 什麼的記憶 / 和什麼的嘆息」。短促一生,我們必須要去捉住每一刻才不枉過,即便是嘆息也是活過的證明。
〈從此〉和〈我們〉都有一種壓抑與悲傷感,當與陳奕迅的〈今天只做一件事〉對讀便十分有趣,明明主題相近,後者卻能以如此溫柔的方式去表達,歌詞開首明確提到「發覺這世界永遠太少空間」,於是提醒我們主動「花一天感覺一切是愛」,副歌「慢慢地邁向聽朝 / 靜靜地懷念昨日」以疊字叫人放緩腳步,恬靜寫意。這裡的「愛」不限於情愛,而是對世間的感受,頗有「從一粒沙看世界」的奧妙,教人細心感覺萬事萬物。
〈今天〉裡感知美麗的渴望,結合〈從此〉裡所相信的「沒太多 / 都有多一分鐘相信有天堂」,彷彿催生了〈剎那的烏托邦〉。詞人知道「烏托邦」難求,在歌詞裡鋪展了大量看似相反的情境,「雨歸來 / 看天壯 / 雪歸來 / 會知赤地某些玫瑰 / 某天流麗綻放」,說明在絕境裡總有某些事物仍能滋長,教聽者以不同心境觀看世界,這又讓人想到〈我們〉裡開首兩句,「葡萄會趁雨天向上爬 / 薔薇會趁晚霞萬里香」,正說明了美好其實是在暗黑裡併發。在〈剎那〉歌詞後段,「是暗光 / 是暖黑 / 是某些讓我相信萬物亦快樂」更反轉所謂好與壞的概念,黑暗可是溫暖的,陰影也是美麗的,到了歌詞最後那句「但求剎那的烏托邦」,便清楚說明了烏托邦是可以去主動尋求的,亦鼓勵人在崩壞的世界守住一角美好。近年黃妍的〈我心中尚未崩壞的部分〉更加直白地訴說著這個信念,歌詞「我就算全身有傷 / 心至少一寸未變壞」,叫我們即使只剩一寸空間也要去掙扎,但求守住最後的溫柔。
重新感覺一個字,感覺屬於你的「甚麼」
重新感受一刻以外,周耀輝的歌詞也提醒我們要重新感受一個詞語,一個字。〈彳亍〉把行字拆開,左腳右腳,一步一步,去發現甚麼。「甚麼」這個詞語,常在周耀輝的歌詞裡出現,理解為開放、想像、未知。歌詞「可否跟我沿著甚麼邊走邊看藏著甚麼」,充分表達出一種前路未知,必須往前走才能明白到底能找到甚麼的狀態,另一方面,又因每個人的路都不一樣,使用「甚麼」便留有解讀的、曖昧的空間。
曖昧容納的是可能性。「甚麼」是問號,代表不確定,但「知道」也非句號,周耀輝教我們重新理解一個詞語的可能性,知道可以不是終結,可以是繼續探索的開端。麥浚龍的〈True Romance〉裡,說的是即將萌芽的一段戀愛,周耀輝竟選擇用「知道」這個中性的詞語來形容這份美好,歌詞「這感覺多好 / 知道自己不知道 / 便繼續繼續想知道 / 繼續繼續虛得似天空」,便帶有希望一直一直探索下去的渴望。陳建安的〈未知道〉,「未」這個字便象徵著一種可能性,不是「不知道」,而是「未知道」,而歌詞「命運極妙妙在沒有根據 / 世界太怪怪到勇敢走過去」,更教人將對未知的恐懼,轉化為放膽相信「未知」。若〈彳亍〉是一個人的自我探索,在壞時代創作的〈未知道〉則與人同行,勉勵大家一路走在生命之中。
周耀輝對字詞的理解與感受力如此敏銳,常常令人驚艷,一些約定俗成的詞語,他也可以重新組裝,讓人以別樣的角度去理解。彳亍如是,〈我們的末日〉裡一句歌詞「然後分開 / 一樣會白頭 / 亦可偕老」亦如是,「白頭偕老」象徵對永恆的愛之期盼,他卻拆開這組詞語,彷如拆開一對愛侶,原來分開也是另一種一生一世。周耀輝用字極為精準,有時只是一個單字就能鑽入聽者毛孔。〈雌雄同體〉裡的「也許接近到當你快樂我會癲」,當中「癲」字,印象中甚少入詞,如此描繪一段「同體」的關係,帶有醉狂迷離,忘記他是她之感。又例如〈從此世界多了一分鐘〉的「我和你太多未碰過」,「碰」字令人驚奇,「碰」本可用作擬聲字,讀起來清脆俐落,如像碰撞就在你耳邊發生,同時可代表具體上的身體觸碰,或精神的碰撞,也可代表「了解」、「發掘」、「嘗試」、「體驗」等慾望。多元的解讀,大抵是因為周耀輝省略了一個「主體」,沒有具體形容碰到的究竟是甚麼,便解放了想像空間。而〈彳亍〉裡的「神遇到 / 佛碰到 / 但我希望碰到我」,可以想像第一個「碰」與前者的「遇到」近似,只是某種擦肩而過,但第二個「碰」字卻是細細探入內在,一寸寸探索自我。
令自己有更多感覺、更多渴望
或因周耀輝常在歌詞裡擴闊字詞的邊界,又喜歡以坊間不常用的句式組句,乍聽之下總是未能立刻意會。如麥浚龍的〈寫得太多〉,副歌最後一句「所以懇求你 / 可以應承我 / 感覺」就讓人迷糊起來:感覺本應是名詞,是「Feeling」,若用作動詞,也理應是有一對象去「Feel it」,那麼「it」到哪裡去了?到底周耀輝想我們感覺甚麼?是不是漏寫了甚麼?
後來才意會到,感覺就是直接的體會,毋用補充。歌詞說的是,關於愛,我們總是寫得太多,感覺得太少,感覺毋須訴諸語言,像麥浚龍〈借火〉裡的「只要我們不用話語感覺是你和我」,以及〈舌尖紋了瑪利亞〉的「請跟我不再說話 / 寧靜地望著我感覺我片刻好嗎」,都反證了語言之無用,感覺之實在,語言反帶來阻隔、誤解,因為要理解他者,需要的不是虛浮的話,而是敏感的、感知對方的心。在Zarahn的〈如果感覺有顏色〉裡,歌詞更開宗明義說明了「人類太多美麗 / 時代太少字句 / 若你太少表達 / 我卻始終太多感覺 / 有時說話講不到的」,我們需要的是感性,是一種體驗世界的渴望,那是我們抵抗麻木,抵抗冷酷世界的武器,如容祖兒的〈渴望晨曦的女孩〉裡,歌詞寫道「再發現已變做能夠渴望的女孩」,當中「能夠渴望」是一種能力,讓人把感覺激活,讓熱情重燃。在Senza A Capella的〈我一伸手抱住我〉裡,「告訴自己必須渴望⋯⋯為著有我 / 就有新的天國」同樣強調渴望的重要性。「渴望」驟看之下只是一個平平無奇的詞語,但周耀輝就是要喚醒我們對「渴望」的「渴望」、對「感覺」的「感覺」,那就像一個連自我都要懷疑的哲學家,唯有時刻審視自己有否失去那份敏感,才能與這個麻木世界對抗。如〈寫得太多〉所寫,一旦感官開了,在任何地方都可找到美好,世界很壞,尚待人「用神用竅 / 令你會更多感覺」,潛進靈魂深處,鑽進七竅之中去感覺生命的存在,那麼即使世界只剩一分鐘,也不算活得徒勞。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