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女性参政:当女权诉求遭遇选票政治,她们一边利用“父权红利”,一边突破传统性别角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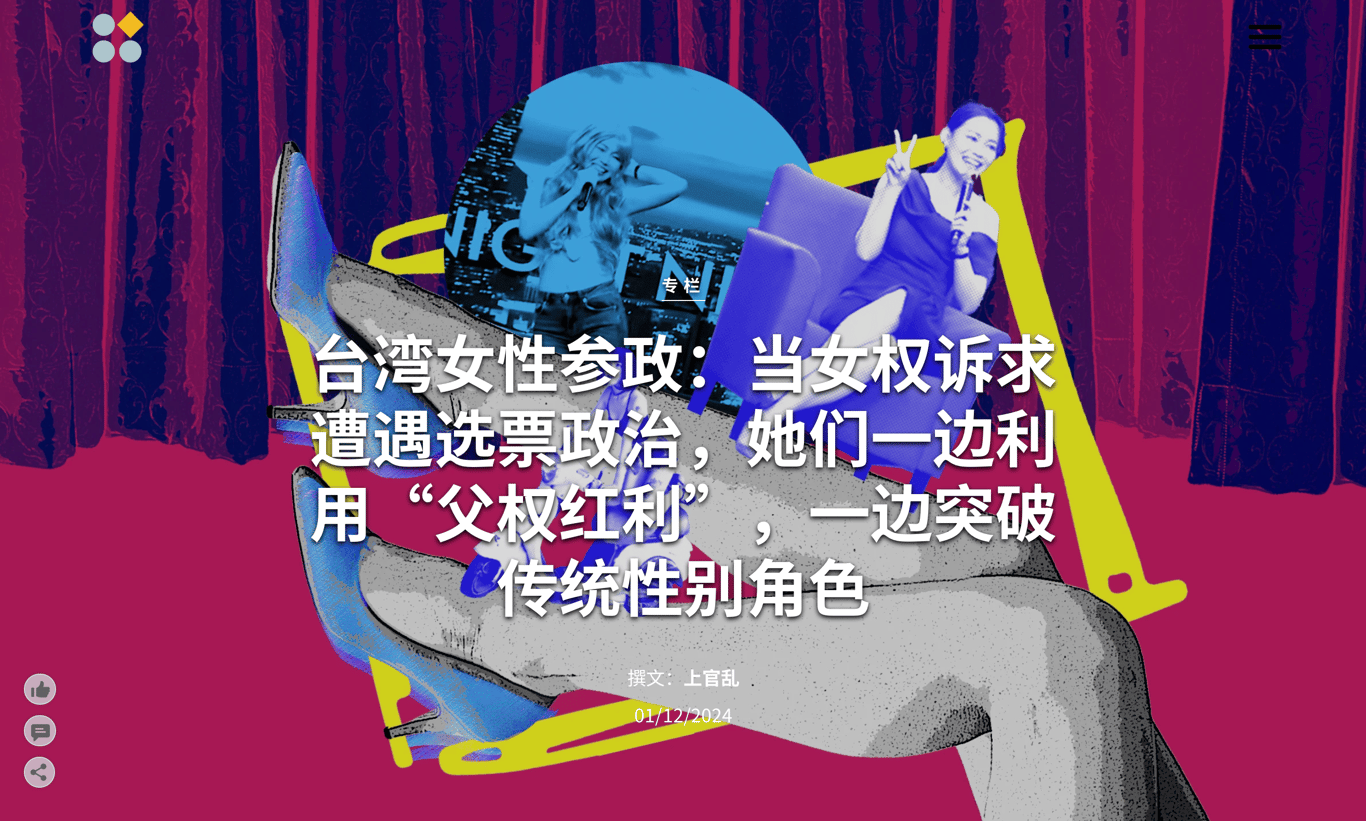
文|上官乱
原文发布时间|01/12/2024
自从2016年蔡英文成为华人社会第一位民选女性总统之后,2020、2022乃至2024年几次选举,台湾女性候选人的比例都逐次上升,关注的议题也更多元。今年,不仅参选立委的女性候选人比例再次破纪录,更是有两位副总统候选人是女性:民进党的萧美琴和民众党的吴欣盈。但是,经过采访和观察后,我们又可以发现,今年的女性参政有很多新特点:经过了MeToo运动之后,候选人的性别议题更多元了;更多的小党大力提名女性候选人,挑起了女性参政的大旗;但面对激烈竞争,在性平主张和选举目标之间,很多女性参政者又不得不做周全和妥协……
这是否意味着台湾的女性参政和民主多元有了的新景象,或者说进入了新的探索阶段呢?
“既然我就是‘父权红利得利者’,那就好好运用它”
在台北最艰困的选区之一南港和内湖选区,有三个女性立委候选人:国民党的李彦秀、民进党的高嘉瑜和基进党的吴欣岱。吴欣岱作为台湾基进党声量最高的分区候选人,因为个人形象突出,理念清晰,和媒体声量大,如今已经成为一个政治明星。接受笔者采访那天,她刚刚录制完政论节目,带着抢眼的妆发,在竞选办公室准备下一个行程。
她在社交媒体上从不吝惜发布“着装清凉”的照片,还经常穿短裙“扫街”(街头拜票),甚至和网红一起唱歌、创作MV。在自己的竞选总部办公室开幕那天,她还率领团队大跳韩国女团舞,唱台语歌。像她这样“张扬”的女性候选人,今年很多,当然也会引发争议。比如民进党候选人黄捷,前不久因为扮演大热的网路动画《山道猴子的一生》里性感的重机骑士女主角,被政治对手大批物化女性。但是很多外型条件突出的女性候选人,并不因为争议而放弃通过形象被看到的机会。吴欣岱说,去年她看见一位女性议员候选人,竟然穿女仆装扫街,“但是我看出她一脸的不情愿,哈哈,肯定是幕僚告诉她,这样会有票。”
“(对于合理地运用外貌优势)我不会有愧疚感”,她同时也坚定说。她很清楚,外型抢眼,加上充满理性光环的医师身分,自己就是“父权红利得利者”,在选战中好好运用红利,也没什么不妥,反正每个人都在这样做。只有当选了,才有权力提出自己的理念,改变社会。如果自己的外型可以赢得声量,转化为选票,何乐而不为。毕竟台湾基进党目前政党票还没过5%,所以她必须为自己和政党赢得声量。
在决定参选立委之前,她曾是理念尖锐的女权主义者,一直担任基进党的性别部主任,关注的性别议题很广泛,甚至不乏“免术换证”这样的小众议题。但是自从参选立委之后,她不得不因为选民的期待而做妥协。小党的资源少,委托民调公司做一次民调要20万台币左右,为了每次民调都能看到些许乐观的变化,她不得不在运用外型优势,和保持克制、避免攻击性之间,小心地取舍,因为如果太冒进,又可能丢失女性的选票。“女性太了解女性了,”她说。她不得不在“父权红利”和选民印象之间小心周旋,避免过线。
但是她发现,女性除了外型,还有一些特质也是争取“父权红利”的利器,比如向男性“示弱”。她知道一位女性参选人,外型不是很出挑,但是很善于把握分寸,精道地“撒娇”,或者委屈流泪。“这真会换来党内前辈和选民的心疼”,她甚至开玩笑,“如果有一天竞争对手在媒体面前哭,我也只能跟着哭了。”
“流量时代,大家就喜欢看女人吵架。”她表示,并不喜欢迎合这种“女人互相扯头花”的刻板印象,因为选举应该通过扎实的政见来对垒,但是每次她的竞争对手说了什么,媒体马上就会给她打电话请她回应,尤其期望看到她激烈的批判对方。如今,她不得不在这样的环境中小心地求存,慢慢地从不适应,到学会运用规则。
那么传统大党的女性参政者是怎么想的呢?
于2020年九合一大选当选的民进党桃园市议员黄琼慧,今年没有参选立委,但是她成天奔波于每个党内立委候选人的造势活动现场,利用自己的人气,为同仁助选。同时,她还是赖清德女性后援会“信赖姐妹会”的桃园地区负责人之一。
她认为,MeToo运动之后,民进党内部的性别环境改观很明显,女性更敢于捍卫自己的身体自主权,拒绝性暴力了。在她看来,黄捷cosplay被指责的事件很无聊,那是一场很特别的活动,该漫画原作者也在现场,再说那个女性角色原型充满自主和独立的意识,没什么不好。“我觉得选民现在越来越聪明,不会被对手带风向”,她说。因为民进党内部,性平议题早已不需要刻意强调。党内提名的不分区立委名单有很多女性,占比远超过保障名额。而分区立委名额,按规定需要经过党内初选,这时候主要就是看民调,拼能力,并没有太受性别因素的影响。“在党内,女性只要够强,不用考虑性别问题,”她认为。
真正多元时代来临?女性候选人在小党中百花齐放
正如黄琼慧所说,民进党作为一直高举平权价值的大党,在今年上半年遭遇MeToo事件之后,已经迅速做调整,女性提名人也比2020年明显增多,单是不分区立委就有17名女性。在区域及原民立委候选人中,民进党71位中女性占了31位(43.7%);而国民党作为一个百年老牌大党,以男性文化占主导,没有过度强调平权,但68位中女性也占21位(30.9%),也比2020年增长了不少。柯文哲的言论一直被认为有“厌女”倾向,但令人意外的是,民众党的区域立委中女性比例反而是三大党中最高的,民众党11位中女性占7位(63.6%),当然可能因为他们的总提名人数很少。而成立于2019年的政党“小民参政欧巴桑联盟”,今年首次提名立委参选人,10位皆为女性——因为党员都是已婚女性和母亲,包括已婚女同志。她们集中于关注性平、儿童权益、弱势群体、新住民、文史议题,提名的参选人中还有已婚同志女性。
这正是今年大选的一个巨大特点——小党百花齐放,而且重用女性候选人。
在各党的性别平等意识上,也可以看到不少进步。就在2020年12月,国民党台南市党部主委谢龙介出席助选活动时,还说“女人拉票,可以拉到客厅,可以拉到房间”;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也曾讲“男人以天下为家,女人以家为天下”。民进党元老辜宽敏也说过:穿裙子不适合做三军统帅。
但是在最近的政见陈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警界出身的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说,自己几近大半辈子住在女生宿舍,自己是从骨子里面、打从心里清楚明白一件事,身处女性团体当中,“对于女性只有尊重,你才有生存之道。”
柯文哲虽然总是失言,但是,他也提出希望改善职场的“性别歧视”、男女同工不同酬,以及改变女性因为生育而失去职业发展机会的问题。似乎为了挽救他的厌女言论形象,在柯文哲和吴欣盈的网路营销文案里,还会强调两者性别互补。
赖清德在MeToo运动中的行动果决让人印象深刻。在关于女性权利方面,他强调,将启动“性别平等教育2.0”,推动多元全龄性别平等教育;缩短不同性别的薪资差距,并建立友善育儿社会环境,支持“双就业、双照顾”,让女性职涯发展不再受限于家庭照顾责任。 而且他的搭档萧美琴,不仅有外交背景和民意代表经验,也有相当的平权经验。
对于老牌大党的父权文化痼疾,年轻小党似乎比较容易避免。吴欣岱就讲到,因为基进党创党人都是男性,所以起初基进党内还是会存在无意识的父权思维,但是随着她和更多女性党员加入后的努力改造,现在党内整体性别平等意识比较浓厚。
女性参政人在平权诉求与选票政治之间的妥协和拉扯
台湾的女性主义学者认为:在政治领域中,当女性获得权力,必然会遭遇反挫。蔡英文当选时,曾有声音说女性不适合领导台湾,其中一个原因是女性无法平衡事业与家庭,但是蔡英文是单身女性,于是质疑的声音又变成没有结婚生育就无法共情大众。这种莫名的矛盾,体现了女性参政的常见困境。在现在的女性候选人身上,我们还能看到更多的矛盾。
首先是身体自主权。民进党立法委员赖品妤喜爱cosplay,但是在2020年接受民进党征召参选新北市第十二选区立法委员不久,就遭到了攻击。她早前拍摄的性感泳装照被挖出来,还被指控疑似性交易。经过这几年女性参政者们不断强化身体自主权的宣导后,这种偏见已经明显变少,但是比较隐性。比如,有些人不会直接针对女性参选人的穿着,却会暗示其目的是吸引“猪哥票”(猪哥:好色的男子)。
这一点或许不准确。就在笔者采访吴欣岱期间,正好有一个男性支持者来到竞选办公室,进行小额捐款。我问这位支持者,吴欣岱的外貌形象到底有没有吸引他的支持,他说,其实并没有,他支持的是吴欣岱的理念。
还有一些单身女性参政者觉得自己没家庭,可以全力投入工作,是参政的优势。但事实上拥有孩子的候选人有时候反而更具有优势:她们会打出妈妈牌,谈教育、谈社福,透过男性无法经历的经验优势,争取选民共鸣。
这一点,吴欣岱也很有感触。
一直倡导女性能力,喜欢单打独斗的她,有一次无意中发现了,母亲身分成了她的优势。她有一对儿女,自从参选以来,就很少陪伴他们。有一次突发奇想,干脆带着孩子一起去菜市场扫街,这样不仅可以陪伴孩子,还可以让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事。没想到取得意外的效果,大家觉得母亲的角色很给她加分。
当然,这些身为母亲的候选人,也会面临一些选民的疑惑:你能否平衡工作与家庭,同时成为一个合格的母亲和优秀的民意代表。但是对于男性候选人却不会有这样的要求。结果就是:虽然大家声称不看性别,只看能力和政策,但实际上对女性的要求更高。选民期许的女性候选人,似乎需要随意转换的身体和心理界线。
更重要的是,就算成功当选,依然会面临党团内部无处不在的、隐形的父权规则。据BBC的报导,目前的主要政党内部环境还是男性为主的,偏阳刚的,男性之间的社交日常,这里都有,比如,喜欢把对性别的冒犯被当成是幽默和权力。还有人一到选举,就会把女性候选人或者女性助理,默认为老板或者男性候选人争取选票的物件。有的候选人女助理就表示,自己跑行程时,会被少数男性趁机吃豆腐。就连现任议员、立委也难逃此劫,在新闻报导出来的案例中,议员游淑慧、钟沛君,立委范云都遭遇过性骚扰。而在2023年上半年发生的MeToo运动,也揭示出,在政党内部,由于选举或者团结需要,女性其实很难讲述自己遭遇的性暴力,“大局为重”是她们的头号紧箍咒。但是这些积习在me too运动之后,有了一些观念的改变。
女权运动与政党政治共舞,以及选举制度改革后的女权新探索
其实今天台湾女性参政者面临的种种问题和矛盾,在过去几十年并不陌生。
根据《当代台湾女性参政研究》的论述,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以吕秀莲为首的体制内精英和主流知识分子,开始引入西方女权主义理论。在实践上,他们偏好提倡文化、温和理性、党派中立的运动策略,成立基金会,通过体制内运作,让很多改善女性处境的法案生效。
到了90年代,因为台湾社会民主转型,以顾雁翎为首的新一代女权主义者,提出了基金会式的半体制内女权运动的局限性,开始和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伴生成长。这时候的女性诉求更多,她们拒绝传统女性形象,寻求新的价值。女权主义阵营也开始分化,同性恋女性主义和异性恋女性主义的差别开始显现。更显著的是,性骚扰、性侵犯等过去被认为私域的问题,被大家提到公共领域,进行反思和讨伐。这当然会遭到社会反扑,甚至有不少知识分子觉得女性主义是在骚扰校园,破坏公共秩序。这促成了女权主义者们在1994年5月22日举行“522女性连线反性骚扰大游行”,在这场游行中,来自中央大学的教授何春蕤喊出“我要性高潮,不要性骚扰”,体现了妇女运动因为世代差异而呈现多元和异质,也拉开了妇权派和性权派的分野。
以何春蕤为首的运动者鼓励女生穿漂亮来游行,并要求社会保障妇女人身安全的夜间大游行,“夜行无罪,妖娆有理”,而此时因为陈水扁要求提前取缔公娼制度,促使性权游行开始和公娼运动合流。可是这无法得到主流女权派的认可,他们认为性权派的诉求不食人间烟火,脱离群众,最终可能会导致整个女权运动不断小众化,无法再和社会展开对话和沟通。逐渐地,阵营之间对待政治的不同态度也导致内部龃龉不断,甚至分裂。
随后,因为台湾开始政党轮替,妇运开始和政党政治关系密切。大家意识到,女权运动可以借由民主投票,从根本上改变妇女地位。而民进党的草根性和进步价值天然容易获得妇运的信任,所以早期,6成以上的妇女运动认同民进党和本土政权,直到现在,这种局面依然很牢固。
但是在选举文化中,女权运动者们需要面对新的趋势。陈水扁当选前,几位主打妇女权益诉求的台北市议员女性参选人纷纷落选。让女权运动者们开始思考,到底应该如何让妇女政策吸引选民;又该如何用共识替代冲突。那些尖锐的或者小众的诉求,慢慢地被策略性地收敛起来。这些女性进入政坛后,大多不会刻意彰显自己的性别因素,她们往往把自己的女性政策诉求以温和方式提出来,并会广泛注重女性权益、民生议题和弱势群体的议题。比如今年民进党的副总统后选人萧美琴,在做立法委员的时候,就率先提出过同婚合法化的提案。
但自2008年起,立法委员人数从225席减至113席,同时采用“单一选区两票制”——全国73个地方选区一区一名,加上平地及山地原住民选区各选出3席、共6席立委,剩下34席不分区立委则根据政党票得票比例(得票率须达5%门槛)做分配。这意味着,过去的妇女保障名额在地方立委选举上自动失效,只有在不分区立委中,才有保障名额。此时,妇运和多元化力量更边缘化,女权运动者过去依靠自身影响力获得提名的优势不再广泛有效,因此不得不依赖政党提名。而妇运与政党紧密捆绑之后,首先遇到的就是男性为主的党团文化,于是前述的所有问题和矛盾,似乎都有迹可循。
另外,随着台湾政党政治的两极分化,女权运动者在依靠政党提名之后,也往往会因为考虑政党利益,有时候不得不让有利于政党的主张优先于女性平权的主张。于是我们就可以看到,性平方面比较前卫的主张,慢慢地在小党候选人中得到更多突显。
那么,愈来愈多的女性参政,到底对推动台湾社会进步有多大的作用呢?学者曾以“描述性”或“实质性”的概念来看待这个问题:女性政治人物如果能真的替女性或弱势者发声,那她可说是一个实质性的代表,否则只是一个描述性的代表,一个选举政治下的“花瓶”。所以,这些女性民意代表参政后,到底会为台湾政治多元和性别平等带来多大效应,还要看她们之后的实际行动,而这正取决于现在这个探索阶段的成果。
(歪脑的专栏、评论和分析文章均属文章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