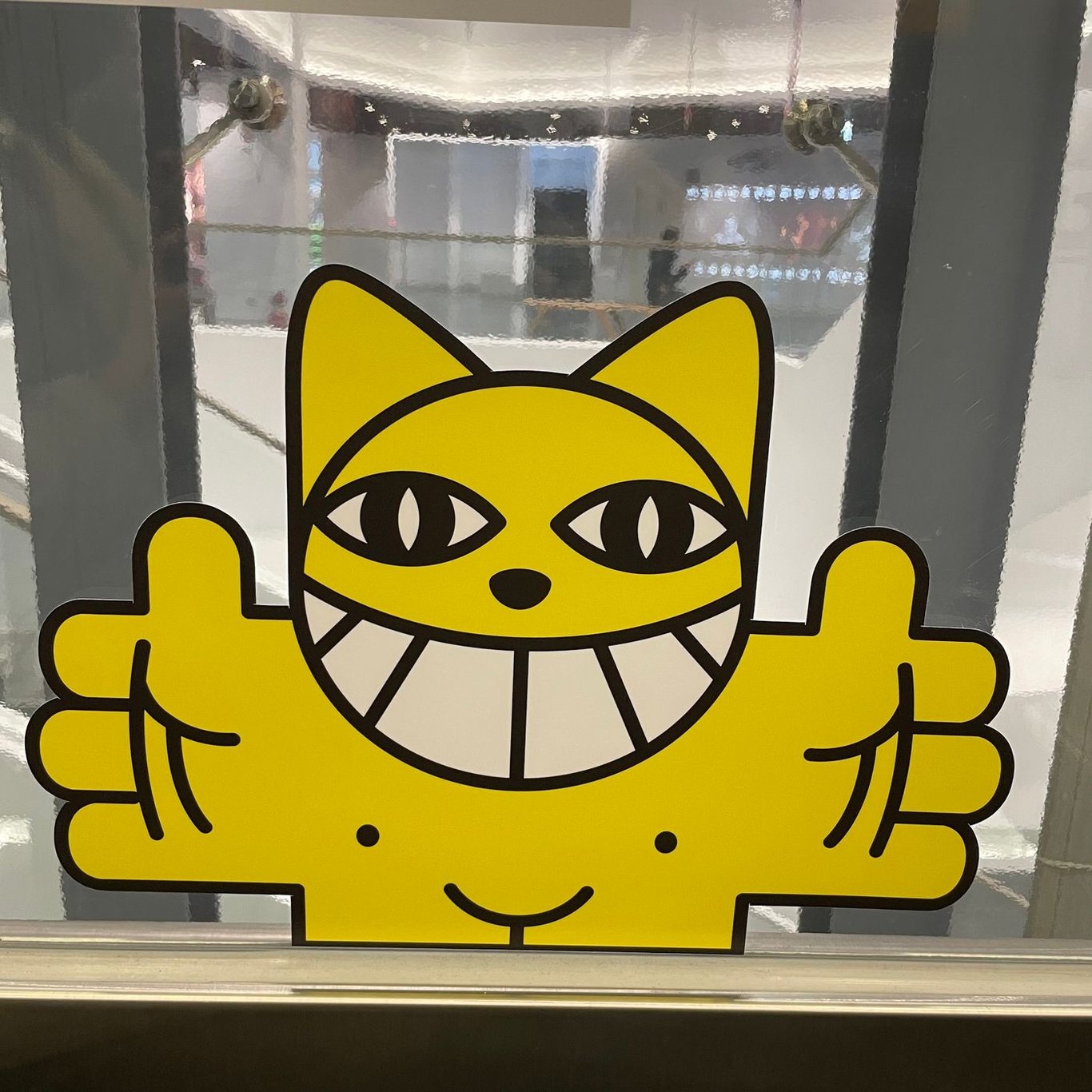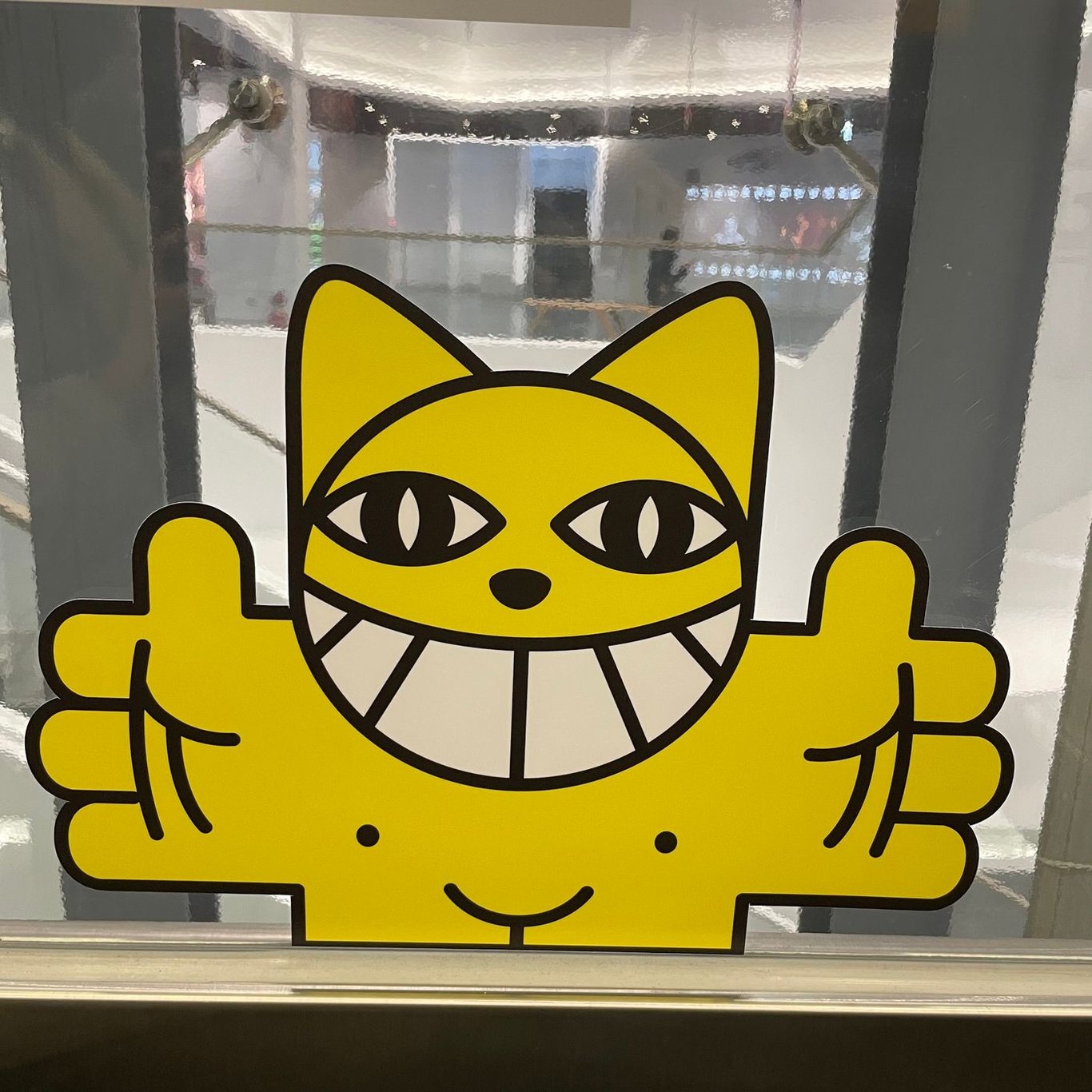徒步旅行
「今天我們的目標是Timeline PLaza公園。」
「那還有多遠?」
「google map上面是顯示26公里。」
「我們目前大概走了8公里,走了兩個半小時,平均算大概是每小時3點多公里,正常來說平路每公里應該要走4-5公里。」
在台南永康區的711創意門市喝著礦泉水,思考著目前已經耽誤到的時間,計算著今天還得再走多長的路。如果想在三天內從台南車站走到嘉義車站,再從嘉義車站走回來,每天的基本步行量就是40公里。剩下的32公里,在不同的交通方式底下,看見的是不一樣的風景,思考的是不同的事情。很久沒背著行李走這麼久的路,又是頂在32度高溫下的柏油路上,上次在這種狀況下走路已經是6年前還在軍中的時候了,相隔6年感覺這件事好像變難了。
「走路」算是一個什麼樣的活動?移動的方式?一種運動?幫助思考的過程?飯後幫助消化?陪伴的形式?沒錢的象徵?腦袋在一步又一步踩在北上的中正北路,思考著稱不上問題的問題,稱得上「問題」的問題又是什麼,要具體的解釋產生問題的動機?還是講清楚問題之後想得到的答案?為什麼問題的問題這麼複雜,有純粹的問題嗎?
時不時地回頭看著跟在後面的子媛,想給予眼神的關注,兩個人一起走,走在後面的最怕的是被丟下,害怕看見的背影變小,害怕自己專注許久的前方消失在眼前,害怕自己只能無能為力地看著不想消失的一切就這麼消失?不曉得子媛是不是真的有這些害怕,我也很少真的有在走在最後一個時候感到恐懼,但也正因為如此,才假設了許多的可能的心理狀態,即便一切也都可能只是假設。
假設了太多的可能,就會帶來許多的焦慮,想要關心、想要給予支持,帶有焦慮成分的關心及支持是純粹的嗎?還是只是想藉此紓緩焦慮帶來的不適?純粹的關心及支持又是什麼?帶有焦慮味道的關心與支持不好嗎?
太多是不好的,味道不對的關心與支持也不算好,但即便是帶有過多或不適合的焦慮味,但本質還是關心,還是在意著對方,還是建立在一種想連結的基礎上,特別是人這種沒辦法獨自存活的物種,如果是這樣,「關心」本身應該還是可以稱得上良善,甚至是幫助物種延續的一種行為,一種人類存在的必要成份吧?是嗎?
可以吃但不好吃的東西在餓得要死的時候吃還是好吃的,還是能夠保住性命的,會不想吃的原因無非就是現在很飽、又或者有更好的選項。剛剛走過幾間檳榔攤,明明很渴了,就是不願意停下來買點喝的,非得等走到新市車站對面的711新雙新門市才願意走進去,在飲料櫃前來來回回地,最後心滿意足地挑了瓶老虎牙子。
當時已經是六點了,是可以吃晚餐的時間,在台南這個路邊攤就算google評分只有一顆星還是好吃的城市,如果正餐選擇便利商店的微波食品,是某種程度上的無知,但如果在台北,小吃攤的評論即便是五顆星,仍然選擇便利商店,則可能象徵這個人懂台北。
選擇多走了300公尺去台南蔡虱目魚專賣店,隨便點個肉燥飯跟魚皮湯都是便宜大碗好吃,對於收入不到國人年平均所得的人來說,能吃到這樣的外食,是一天的小確幸,但這樣的快樂可能對於收入早就達六位數的人來說,根本不值得一提。
快樂應該要是簡單的嗎?還是其實應該追求高層次的?什麼是簡單的快樂?憑什麼快樂有分等級?能夠吃到好吃的東西是簡單的快樂,但仍不滿足缺少的可能是更高層次的。可能在意一起用餐的人是誰,在意眼前看到風景、聞到的氣味、聽到的聲音,在意食物或餐廳本身的社會價值,在意的事情很多,然後追逐,進而獲得,這樣稱得上追求高層次的快樂嗎?這是量變帶來的質變嗎?
吃飽飯,定了今天至少再走2小時的目標,少走的明天再補走回來就是了,決定好目標,讓餐廳的冷氣不再使人眷戀,即便大腿燒襠還是決定繼續走,這個再走2小時是我說的,我得說話算話。
「你腳張的太開了,要不要我們乾脆搭火車回去了,趁我們還在可以搭火車的地方。」
「我們這樣是不是半途而廢情侶檔,上次走白沙屯媽祖遶境也是走一天就不走了,這次也是,每次戴這頂帽子都走不完全程。」
「但是你的腳感覺也走不完,我也好像有點中暑。」
「那我們走到前面那個紅綠燈再折返,這是我們最後的尊嚴。」
也不過只是往前多走了50公尺,不曉得是得到什麼尊嚴,但兩個人都笑得很開心。
原本只是前幾週一句「好想上山。」,才決定安排這幾天去山裡走路順便野營,但因為天氣不穩定決定該在平面道路上流浪,最後變成早已回到台東,坐在電腦前記錄這一切。不曉得為什麼,明明什麼都沒完成,此刻想起來卻還是很快樂。
「如果只有你一個人,你應該走得完。」
「如果只有我一個人,我根本不會走。」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