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沈冲:中德之间的科幻漫游|围炉·FDU

几位研究方向各异、来自德国或中国的青年学者,尽管都不研究科幻文学,却共同创办了一本致力于翻译、推广和传播中国科幻文学的独立杂志《Kapsel》。他们为何做这样的尝试?我们今天如何理解科幻?科幻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无国别性吗?我们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杂志的创办者之一、复旦大学德语系的沈冲老师。以下是对话记录。

围炉=围炉
沈=沈冲
1
科幻杂志《Kapsel》与翻译策略
创办杂志的契机
围炉:可以简单介绍一下您参与科幻杂志《Kapsel》的契机吗?
沈:我本身是做德语文学研究的,在柏林留学时有个好朋友Lukas,他是学应用文学的。我们每周都会在大学食堂约饭,然后坐在院子里边喝咖啡边聊天,有一次说到要做一本关于中国文学的杂志。2017年正值《三体》德语版面世,于是自然就想到了科幻。我一开始对科幻没有很深的研究,只是比较好奇,有时候会读一读。我们计划把中篇长度的故事翻译成德语,给一些德国的读者和身边的朋友看,请他们以读者来信的形式谈谈想法。我们的主业都不是科幻研究,办杂志的初衷,一半是出于兴趣,一半也是希望能通过这个认识一些有趣的人。
最初的想法是找一些当代的、和我们年纪相仿的、比较年轻的作家。第一次我们找到的作家是迟卉,过程非常机缘巧合。当时我不认识任何科幻作家,后来在豆瓣上认识了钟螺,巧合的是她是复旦科幻苹果核的成员,通过她我们认识了迟卉。我们由此得到了作者本人和《科幻世界》的授权,一起翻译了《虫巢》。在中德双语的故事之外,我们还收入了和作者的线上对谈、针对情节的插图、读者来信和简略的介绍文章,另外还有这个故事的德语朗读版,前前后后大概花了一年的时间。这些都是我们联系一些朋友一起设计完成的。
Ruben Pfizenmaier负责项目的策划和推广,杂志的设计和排版则出自Marius Wenker之手,第二期开始Felix Meyer zu Venne加入了我们,中文名叫麦子丰,我们都管他叫Mayo,他是个中国通,也不是科幻研究出身,研究的是中国戏剧。我们联系了一个比较小的出版社Fruehwerk,前三期定价是十欧元一本,我们也不指望拿这个挣钱,顶多就是希望收支平衡,可以覆盖印刷费用,一开始的翻译、排版、插图和文章都是义务劳动和友情参与。第一期做出来之后反响还可以,就决定做第二本。

围炉:感觉读者来信的部分很有意思,在德国对中国科幻感兴趣的是哪一部分人呢?
沈:还是年轻人比较多。我觉得他们也不一定特定是对中国科幻感兴趣。有一部分人可能是对中国感兴趣,有一部分人可能对于科幻感兴趣。就像我作为一个中国读者,就不会特别计较是美国科幻还是日本科幻。当然也有一部分人,对中国特别感兴趣,所以不管是中国的科幻还是中国的纯文学都想读一读,可能对他们来说这也是认识中国的一个窗口。
也有一些比较热心的人,例如德国挺有名的科幻作家兼学者 Dietmar Dath,他在第三期给我们杂志写了读者来信。包括我们后来和作家刘宇昆和学者宋明炜也有联系,至少他也知道这个杂志。我们还翻译了陈楸帆的作品,不过是在另外一个即将出版的合集里面,再后来有了Anja Kümmel,Ann Cotton等青年作家的参与。能引起一些比较有名的科幻工作者的注意,完全始料未及。最开始的时候,我们根本不会想到这些人会关注到我们。
围炉:之后杂志是怎么发展起来的?
沈:第一期之后,我们通过迟卉认识了更多年轻的科幻作家。接下来几期中,我们翻译了夏茄、江波、宝树和吴霜等人的作品,根本不愁没有稿源和灵感。
第四期Kapsel得到了柏林市政府的资助,把这个活动做到了线下,邀请一些中国作家到德国去。线下的交流还是以年轻人为主,也会参与当地的书展,在文化中心Acud举办活动,这个中心也都是年轻人在经营,有点亚文化或青年文化的感觉。2020年本来应该有不少活动的,但因为疫情很多活动都在线上举行,有些也不得不取消了,绝大部分受邀去柏林的中国科幻作家都未能成行,非常遗憾。
杂志大概保持一年一期的更新频率。前面三期的文章都是《科幻世界》已经发表过的,我们问他们要了版权,很多作品都是第一次翻译成德语,作者也很乐意授权给我们。
最新的第四期比较特殊,这些作者是我们邀请的,我们事先给了一个话题:梦,或者说乌托邦,而且必须是积极意义上的乌托邦。我们请了两位年轻的德国作家Anja Kümmel和Tim Holland,还有两位中国作家吴霜和宝树。故事都是我们约稿,他们特地为杂志写的,不同国家不同性别,他们的文本之间形成了很有趣的对话,仿佛一组四重奏。德国作家Anja Kümmel的《梦》的中文翻译后来授权在《科幻世界》发表。《科幻世界》这么大的杂志能关注到Kapsel,我们非常开心。

选题思考
围炉:最新一期的杂志的话题,您是给了一个乌托邦的话题邀请大家来写,这个话题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沈:很多时候对于科幻,我们有一个误解,觉得通过科幻一定要去进行一些批判。科幻写作者似乎更倾向于写一个“恶托邦”的故事而非“乌托邦”,更多以一种批判的、只破不立的视角去写一个故事。比如Anja Kümmel,写《梦》的作家,她说在开始写之前,她不知道应该怎么下手。因为她的约定俗成,或者说教育她的文化,让她习惯于书写末日景象。而且她也比较喜欢这种阴暗结尾的故事。我们的文化氛围也是如此,我们觉得皆大欢喜的故事肯定就是好莱坞式的,带有些贬义和俗套:主角肯定是有光环的、打不死的,坏人的话是一枪一个,最后主角怎么样都能活下来。但恶托邦的故事走了另外一个极端,很多时候我们会认为,恶托邦也许更加引人思考。
我们选“美梦”或者说“积极的乌托邦”这个话题,某种程度上也是对于这种观念的一种回应,一个皆大欢喜的故事,难道就没有说服力吗?难道就没有引发人思考的能力吗?其实并不是。写作比较可怕的是走向程式化,觉得一个皆大欢喜的故事肯定是给小朋友看的,肯定是童话故事。我们希望挖掘皆大欢喜故事的深刻性。
此外,乌托邦也有一种复古怀旧的情结在里面,因为科幻刚刚出现的时候,更多描绘的是一种乐观进取以及对科技进步的信仰,很多时候就是乌托邦的一个图景。比如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就是对中国未来的美好愿景。“乌托邦”有比较原始、单纯的感觉,所以选这个题目也是对于科幻最初的形态一种回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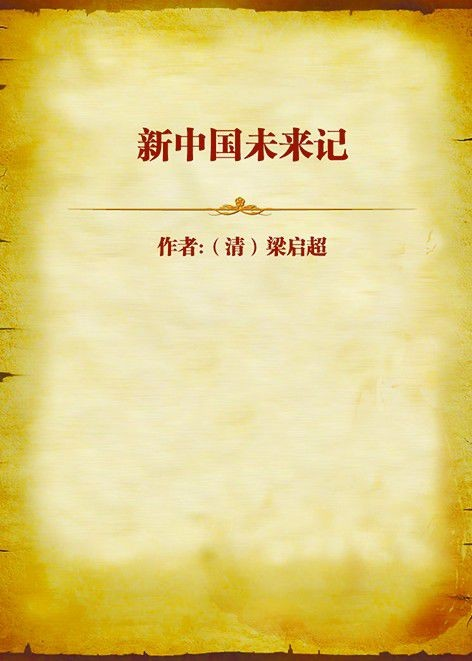
另一方面,我觉得这个题目对这几位中德作者来说,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挑战。通常一个好的作者可能更加喜欢写一些恶托邦,因为这样可以更多展露出他批判的锋芒,但是我们在想是不是这些东西多了之后也会变得疲倦?变得千篇一律,就跟很多好莱坞电影千篇一律的结尾一样?我们是不是可以从一个我们觉得已经穷尽的角度、觉得比较俗套的角度,来重新写出一些不那么俗套的故事?
当时收到稿件后,让我们比较惊讶的是,其中的三个故事都是以电脑游戏为背景的。梦让这些作家不约而同想到了游戏。也许是人生如梦、人生如戏的之间的隐秘关联?无论如何,游戏确实是一种适合天马星空故事的载体。
宝树在《真爱乌托邦》中写的是网络婚姻配对的故事,男女双方必须共同参加一个虚拟游戏以检验彼此的默契程度,中间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反转,最后主角还是在一起了,不过以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呼应了这就是一个梦。
Anja Kümmel讲述了电脑游戏“海洋世界”中一个末世后的世界,里面存在两种生命形态:一方是技术优化的赛博格,他们之间通过数字化相互联结但又彼此独立行动;另一方是水生生命体,有着水母和章鱼的特征,共同构成一个整体的有机体,他们分别代表的“我”和“我们”两种视角,在故事中不停切换。
吴霜的《功夫牡丹》是通过电脑游戏来采集人类基因,这就涉及到伦理和科技的冲突,有了人类的基因库,遇到绝症的时候可以很快匹配到某种血型,也很容易匹配罪犯的DNA。但这又涉及到隐私,或者说被黑客滥用的问题。最后主人公尽管明知是犯法的,还是通过这个游戏实现了这样一个乌托邦,每个人都可以下载这个基因库里面的东西。
最后一个作品是Tim Holland的《堆土》,写的是全球变暖之后,海平面上涨,柏林变成了一个岛,面对新的环境,人类也发生了异化。它的体裁比较特殊,是一个作者这几年正在创作的一首长篇科幻史诗的片段。
翻译策略
围炉:您与两位德国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是怎么合作的?
沈:基本上是我和Lukas、Mayo三个人合作翻译。Mayo中文非常好,如果涉及到中翻德的话,Mayo会先翻译一下。对一些模棱两可的地方主要由我来解释,Lukas的德语文笔比较好,给不少报刊做过自由撰稿人,主要负责后期润色。我们三个人讨论之后,会最终形成一个比较满意的版本。如果是德翻中的话,则是反过来,由我做第一版翻译,遇到理解上不确定的则大家一起讨论,最后形成一个比较好的译文。
我们还参与了刘宇昆(《三体》的英译者)编译的一部科幻短篇集的翻译工作。刘宇昆本身也是科幻作家,我们翻了这部科幻短篇集《碎星星》中的四篇,因为量比较大,我们先是分工翻译,然后汇总问题讨论。
围炉:翻译把中国小说翻译成德文的时候采取的翻译策略是什么样的?
沈:主要是贴合译入语,因为更多是起到介绍的效果。不光是科幻,中国文学翻译到德国其实并不是很多,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个陌生的东西。我觉得还是更加偏向于德国读者的一些习惯。
第一期里面有一个问题,我们讨论了很久,“男孩树”到底是翻译成德语的“男孩”+“树”,还是把中文男孩的拼音放进去,产生间离化的效果。最后我们还是采用了中文的拼音,再加注释。另一个比较有趣的地方是,这篇故事里面有一个人物叫詹姆斯,我们争论了很久要翻译成James,还是詹姆斯(拼音)。
我觉得遇到的最大的挑战是张冉的《晋阳三尺雪》,讲了五代十国的一个故事,晋阳城被攻陷,时间穿梭而来的主人公试图抵抗契丹人的进攻守住晋阳。它的语言类似《水浒传》的风格,古典和科幻的融合给读者很大的阅读快感,但也给翻译带来了很大难度。比方说,里面有很多戏谑的文字游戏,他造了一辆车,管这个东西叫“保时捷”。叫“保时捷”是因为它能让你准时到达。这个东西要传达给德国读者就很难,因为保时捷是他们非常熟悉的东西,但是我们又要把这个“保时捷”作为字面拆开。还有种酒叫“威士忌”,就是猛士喝了之后也会感到忌惮,管手电筒叫“电友”,管墨镜叫“雷朋”(Ray-Ban)。这种时候我们不得不会加很多东西进去解释,尽量在行文中把意思表达出来,减少脚注,因为脚注多了影响阅读的连续性。这是一种非常有趣的现象,有时候我们为一个词,一条脚注会争论很久。
比方说“中原”这种词,是把这个概念用拼音加一个脚注呢,还是字面翻译?它当然是一个地理概念,但更多是一个文化概念。包括里面有很多的文字游戏,中国人会觉得非常俏皮,但是一旦进入另一种语言,可能这种幽默就没了,需要德国读者通过我们的解释去还愿中文的文字游戏。不光是科幻翻译,其他翻译其实也会遇到这个问题,译者都要做出取舍。我们的出发点是让普通读者也可以接受,让对中国有没有任何了解的读者也可以接受,所以我们会倾向于照顾德国读者。

2
科幻文学
面面观
围炉:您如何看待作为类型文学的中国科幻小说?
沈:我认为(当代)中国科幻是从刘慈欣,尤其是从他获雨果奖之后才开始进入大众视野的。从这以后,大家才慢慢觉得科幻小说也可以是中国当代文学甚至中国文化的一个标签。但是科幻小说这种类型文学在中国的产生其实非常早,拿《科幻世界》这本杂志举例,它其实已经有40多年历史了。再往前数,清末的梁启超就写过《新中国未来记》,蔡元培也写过《新年梦》,这些20世纪初的中国科幻,就是当时人对乌托邦的幻想。
当然,科幻小说作为类型文学首先要和神话故事分开来。其实这两种文学会有交叉的地方,科幻会有一些科技的背景,而神话就没有必要和你解释里面的奇幻现象。比如说为什么这个人会飞、那个人会变形,神话里不会去解释,但是科幻是要有科学依据的,至少是看起来有科学依据,不能让读者觉得这是无中生有的变戏法。这可能是因为科幻是文理科交叉的文学,需要有理有据地叙述一种现象,即便这种现象是出现在文学里的,也要给这种现象创造一个道理、一个解释。
科幻和神话会有这样的区分,我认为是从工业革命开始的。《聊斋志异》和《山海经》就很明显是神话甚至奇幻,但不是科幻。凡尔纳的《地心游记》、《八十天环游地球》和《西游记》有很大的区别。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对科技原理的认识有了很大的发展,科学在生活中的运用也大大增加,所以在小说中就出现了解释现象、解释技术的特点,这样就把科幻小说从奇幻小说里面剥离开来了。这并不是说科幻里面的科学就是真实的,更多的是营造一种“真实的感觉”。文学所追求的真,不就是这种真实的感觉吗?

结合科幻小说的历史,我觉得科幻文学刚出现的时候,他的主题更多的是对新发明的预见,或者说是乌托邦(对未来社会的设想)。比方说科幻里面预测未来会有一个类似于自行车的东西,以后就真的有自行车了。所以说读者对于科幻文学就会有这样的期待,预言未来会出现的事物;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乌托邦,就像是梁启超、蔡元培写的科幻小说,他们看到中国社会被侵略、落后的现实,又受到西方科技进步事实的刺激,就会幻想中国在100年200年后在科技上能够有高度的发展,成为一个强国。陆士谔的《新中国》。与之相反的是恶托邦,即科技发展带来的人类社会的异化甚至末日。
科幻本身是由科学和幻想组成的,我觉得这个文体的发展也离不开这两个源头。在科幻以舶来品进入中国的晚清,更多是和天马行空的幻想联系在一起,凡尔纳的作品打开了我们对未来科技的憧憬,于是有了很多基于畅想未来的乌托邦,算是中国科幻的一个小高潮。五四时期推崇赛先生,咋一看与科幻契合,但是事实上恰恰相反,科幻被认为是伪科学,是幻想甚至是迷信,与科学的求真背道而驰,于是这种文体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的发展都不那么顺利。而七八十年代,科幻文学的在科学方面的潜力又被挖掘出来,出现了很多科普读物。科学技术通过幻想的方式,融入到小说中,其读者群体主要是青少年。其实这个趋势现在还有,很多时候我们发现科幻还是放在青少年儿童文学类中。
所以说,刘慈欣的《三体》系列,还有更早的韩松的《医院》三部曲对于我国的科幻文学发展非常重要,正是这样的作品才让科幻又回到了严肃文学的范围里,在思想深度方面不输纯文学。你可以从《三体》里面解读出很多东西,比如说关于危机和和平时期的体制、个人与集体的伦理问题。当然刘慈欣不会主动评判这些问题,而是留给读者去想,这个时候他就是借助科幻提供给了你一个思维的框架。他创造了一种虚拟的语境,在这种语境中就可以去思考另外一种可能性,甚至是对现实的考量,对自我,乃至对人类的思考。而这种思考在科幻的框架里才显得合理且直观。这是科幻优势,也是它的独特魅力。
围炉:您觉得科幻小说对作者的科学技术背景会不会有很大的要求?
沈:我觉得看写什么方面的吧。科幻是一个介于文理科之间的文学。偏理科一点是硬科幻,偏文科一点就是软科幻。作者的背景当然会反映在他的作品里面。就比如说陈楸帆是中文系的,但他好像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领域工作过,这一点我觉得就有体现在他的作品里。再比如说刘慈欣就是一个工程师,所以他的作品里面硬科幻的、物理的成分就比较多。迟卉大学是学生物的,那么《虫巢》这样的故事设定也就顺理成章了。个人的阅历会融入到写作之中,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我不认为科幻作家就一定非得是某些领域的。
围炉:您认为科技的发展会不会剥夺人类的幻想?
沈:这是个很有趣的问题,比如说对新大陆的追求现在已经不可能了,因为我们对地球上各大陆的认知已经基本完整了,所以可能在这方面大家的期待就降低了,也不会再去写《八十天环游地球》这样的小说。
但事实上,科幻小说的题材可以说是无穷的。因为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幻想取向,以前往地球里幻想,写地心里的国家、周游地球、未来世界,现在可以往宇宙幻想,甚至是不同维度的世界,甚至看不见的微世界,或者时空旅行小说,重写过去。这一意义上,科幻只会促进我们对未知世界的想象和对已知世界对重新审视。
对于未来的幻想也是和当下密不可分的。在这里我想举一个例子,就是陈楸帆小说里出现的脑机连接和“赛博格”,把生物和机器联系起来,会涉及各种各样的技术、伦理问题,这也是现在大家都关注的事情,这里就有很多写作的空间。所以说并不是科技发展限制我们的想象,而是科技发展遇到瓶颈时,反而给了我们去往这方面探索的可能性。科幻很多时候会在现有科技的基础上展开一种伦理讨论,本身包含着一种人文关怀。
同时还有一种不会受科学限制的写法,就是偏哲学思考的科幻小说。比如我非常喜欢的华裔作家特德·姜(《你一生的故事》作者),他就喜欢写哲思类的科幻小说。在《巴比伦塔》中他就把《圣经》里的巴别塔故事翻新了,讲人们造巴别塔一直往上,直到最后到顶的时候才发现又回到了刚开始的地方。我觉得这个就和写神话故事的同人小说有点像,更强调的可能就不是科技,而是世界观。这种写法就不要求一定要站在科技的最前沿,和刘慈欣、陈楸帆这类作家相反,他反而在一些你意想不到的地方构建出发人深省的世界观。

3
科幻无国别吗?
围炉:如您所提到的,科幻是一种基于未来科技的伦理讨论,比方说在软科幻里似乎就包含了一种超越国别性的人文关怀,那么我们可以称科幻小说在某种程度上是无国别性的吗?
沈:软硬科幻相对来说是一种成熟的划分,如果说硬科幻是一个强调科技的作品,那么科技对于软科幻而言只是一种背景,作家更多是要讲述一个故事。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个划分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我们会发现刘慈欣在创作的时候其实也是构造世界观,一个基于三体和地球人文明的一个宏大的叙事圈,这与美国特色的太空史诗一类的作品其实有着相似的设置。但郝景芳的一些小说,比方《北京折叠》,其实可能是一个与我们的生活非常接近的故事。
然后谈到国别的问题,我觉得科幻也是一个话语体系,比方说我们提到美国科幻会特别想到美国梦,比方说复仇者联盟、超人等。这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文化输出,或者说一种话语体系的建立。就像是古希腊罗马有希罗神话、北欧人有北欧神话,这种话语也是一个标签化的东西。而中国的科幻如今其实也可能是在寻找这种话语体系的过程当中,科幻就是当代的神话。比方说刘慈欣的作品中就有很多中国元素。就包括史强这个角色,其实就非常的中国江湖气。从文体上来说,比方阿加莎是西方的推理,但是在日本被发扬光大。一提到本格推理我们会想到日本,也许科幻也会成为这样的东西。
科幻一方面肯定是有全球化色彩的,但另一方面也有国别的特殊性。如我刚才所说,科技是在技术更向前推一步的背景下的讨论,另一方面却也是对于自身环境的关照。比方说《北京折叠》就是基于人口众多、贫富差距、边缘人等等的现实考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科幻文学不是文学中的另类,它也一样关照着作者所处的时代。包括凡尔纳,他当时关注的是探索未知处,因而交通工具就是描写的重点。
我觉得任何好的文学,包括科幻文学,肯定是从作者的感悟出发,可能是亲身经历也可能是道听途说或者想象的东西,因此必然带着所处时代的烙印,哪怕是历史小说,也是带着当下视角的,这一意义上,文学不可避免地带有作者的地域性或者说国别性,但是好的文学肯定也包含着一些共同的普世的思考,所谓人同此心,因此肯定会超出滋养它的土壤,走向世界。
围炉:就您所说,科幻都基于一个对于时代的考量,那么在当今世界科技起步发展的时代背景中,科幻是不是就更容易作为文化输出的一个载体呢?因为它相较于传统中国作品,比方《红楼梦》这种蕴含复杂文化的作品,似乎更易被外国读者所接受?
沈:可以这么说。因为每一个类型文学或者说每一个文学题材的一个确立,它都是有一个话语体系,读者在读侦探小说、读科幻小说、读纯文学、冒险小说的时候都有不同的期待。相比《红楼梦》,科幻首先就是产生于西方的,在某种程度上与侦探小说很相似,是一个比较程式化的东西,而这个框架是所有人都认同的。在这个共同的框架之下,其实中国的科幻作品仍然保有一部分是反映中国的,哪怕是把传统文化包装进去,这其实也是一种促进国外读者理解中国的方式。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是以学习者的姿态去认识西方,现在当我们慢慢发展起来后,我们也希望能通过对话,让对方来认识我们,而科幻就是一个渠道,仿佛一种不同文化间的通用语,我们可以在这一个平台上进行交流。
围炉:还有一个与国别相关的问题,我们之前做调研的时候发现,中国科幻小说选被译到国外时,会被国外网站比方亚马逊宣传为某种批判中国、批判现实的作品,是在中国境内无法出版的作品,以此以吸引眼球,您对这个怎么看呢?
沈:这种语调可能有两个不同的情况,一种情况是作者带着恶意去写作;另一种是读者带着恶意去阅读,我们也可以把“恶意”替换成“意识形态”。刘慈欣的《三体》,如果要做意识形态的解读太方便了,包括《北京折叠》也是,但是我相信作为郝景芳和刘慈欣本身在写故事的时候首先是为了呈现自己的思考,而不是含沙射影的意识形态批判或者输出。
1000个读者眼中有1000个哈姆雷特,我们不可能关闭评论口,阅读时读者必然带着他的世界观和立场,甚至偏见。作者是无法干预的。但是作者也不可能为了迎合而去做出改变,或者不以自己的方式去思考,人总是只能迎合一部分人。在交流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发现,一部分人可能根本就没有了解中国,只是带着那种从媒体上或者其他途径的恶意去先入为主地看待一个东西。但是大多数人还是带着中立的态度,抱着好奇心去阅读中国科幻的。当然可以从《北京折叠》中看到我们中国的问题,但是一个普通的德国人也会从中看到德国的问题,他所处环境的问题,甚至是人的问题。这就又回到了科幻是国别还是世界文学的话题了。

科幻在很多时候是一个通过他者反观自身的视角。现在比较流行的还有一个后人类视角。什么是后人类?我们整个文明史都是以人为中心的,甚至不是以所有人,而是以“我”的视角。比方说欧洲中心主义,但不排除将来某一天会出现一个东方中心主义,中国中心主义或者说上海中心主义都是有可能,因为每个人都会倾向于从自己的立场去看待一个东西。但是借助科幻我们甚至可以从一个虫子的视角去看待这个世界。通过想象,其实是站在他者的立场上去思考,去反观自身,从另一个角度去看世界,这可能是其他的文学类型比较难做到的。
围炉:中国的科幻作家是否有成为严肃文学的潜力?
沈:我觉得任何好的作品都有潜力成为严肃文学。科幻本质上是一种雅俗共赏的文学类型,不像某些纯文学一样难以进入甚至拒普通人于千里之外。科幻大有潜力,就像《三体》对于一个小朋友而言就是一个非常魔幻的,天马行空的,一个地球和外星文明之间打仗的故事,我们不需要小朋友去说里面反映了对人类历史文化的深刻反思。另一方面,这个恢弘的故事肯定会引发一些成年读者的思考,去反思文明到底是什么,人到底是什么,这就突破了类型文学的标签,完全可以比肩纯文学。三体文明其实就是地球文明的另外一种可能性,一面镜子,或者甚至是一个自画像。通过他者,我们更好的看清了自己,通过对未来的描写,我们更认清了所生活的当下。自我和当下,是好的文学的出发点,也必然是终极归宿。
关于中国的异域想象
围炉:现在翻译过去那些中文作家的作品在德国那边的影响怎样?
沈:这个很难说,因为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小的杂志,大家不要想象人手皆有的盛况,所以我上面说中国和他们的交流其实是极端不对等的。我们会发现德语文学史里讲到的东西我们几乎都有译本了,但是我们的《西游记》《射雕英雄传》才刚刚翻译过去。绝大部分人对于中国的印象可能就是,中文就是苍蝇脚胡乱叠在一起、中国人长得差不多。很多时候中国在当地的一些机构可能也加深了这种成见,比方说中餐馆:那边所有中餐馆都是几个龙柱子,一些红灯笼,然后梅兰竹菊之类,外国人觉得中国就是这个样子的。99%的德国人没有来过中国,但是大部分人都知道中餐馆,对于他们来说中国可能就是一个非常符号化、非常平面化的国家,而我们很多时候做的事情,很不幸是在迎合和加深这种刻板印象。
科幻是一种相对来说比较对等的交流方式,唯一的壁垒只是语言,其他只需要交给作品本身去说话就可以了。德语世界很多时候是跟着英语世界的,他们之间的壁垒其实是要小很多。所以我说为什么刘宇昆这样的译者非常重要,他贡献非常大,他把一些国内的科幻文学翻译成了英语之后,再有人通过英语把它翻译成德语,或者很多读者直接阅读英语翻译,或者也有直接从中文翻译的德国翻译家,我们Kapsel也是其中之一。沟通的桥梁搭建完之后,德国的读者会认识到,原来中国人是可以写出像《三体》这样宏大叙事的作品的,他们肯定会对所描绘的那个世界产生思考和共鸣,我们甚至不用给《三体》打上中国的标签,因为这不仅是中国的故事,也是人类的故事,甚至是人类之后的故事。

我们以沈冲老师和朋友共同创办的杂志《Kapsel》为开始,讨论了有关这本杂志,以及科幻文学的许多问题。这本杂志是一场中德之间的科幻漫游,我们的谈话则是一场有关科幻的漫谈。我们看到,科幻文学作为一种类型文学,有着许多可以挖掘的内涵,同时在不同国家间了解仍很不充分的情况下,科幻作为一种承载着国别文化信息的跨国别的文体,某种程度上也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一座桥梁。

采访|崔舒婷 曾颖苗 韩天雪 闫力元
整理|崔舒婷 曾颖苗 韩天雪
统稿 | 闫力元
审稿|黄斯怡
图 | 来自网络
微信编辑 | 李卓颖
Matters编辑 | Marks
围炉 (ID:weilu_flame)

围炉近期在举办读书会,欢迎感兴趣的朋友们扫码报名!
优秀的读者读后感将会合集成围炉文章,并收到围炉周边与赠书。
(添加时记得备注想参与共读的书目)
以下为各个读书会群的开始与结束时间:
《理解人性》(6.18-7.10)
《艺术的故事》(6.18-7.16)
《荆棘鸟》(6.26-8.7)
《局外人》(7.2-8.7)
《妮萨》(7.2- 7.31)
《阁楼上的疯女人》(7.6-8.20)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