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我安慰你度过,这时代的晚上
波士顿评论丨拿什么拯救民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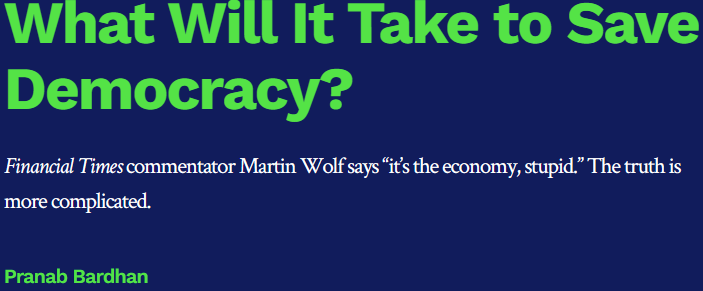
译按
本文是一篇书评。
作者普拉纳布·巴德汉,在印度加尔各答接受本科教育,1977至2011年任教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系,目前是该校杰出荣休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发展经济学、政治经济学。近著为A World of Insecurity: Democratic Disenchantment in Rich and Poor Countries(哈佛大学出版社,2022)。
本文评论的著作The Crisis of Democratic Capitalism,由企鹅兰登书屋2023年2月推出。其作者马丁·沃尔夫,生于1946年,是英国《金融时报》首席评论员。
本文认为,马丁·沃尔夫对“民主资本主义之危机”由来的诊断和应对处方都存在严重缺失,并低估了刺激右翼民粹主义兴起的文化因素。作者指出,不能简单认为,只要资本主义繁荣,经济收益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更公平的分配,民主就能得救。
本文原题“What Will It Take to Save Democracy?”,由《波士顿评论》(Boston Review)发布于2023年3月14日。波士顿评论创办于1975年,初为季刊,后改为双月刊,目前注册为独立、非盈利的政治和文化论坛。
译者听桥,对原文有多分段,并加上小标题。
拿什么拯救民主?
普拉纳布·巴德汉(Pranab Bardhan)

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是当今世界最具声望的经济记者之一,用他在其新著《民主资本主义之危机》(The Crisis of Democratic Capitalism)中经常使用的比喻来说,他感到不悦的一点是,富裕国家中资本主义与民主之间的传统联姻已濒临破裂。
沃尔夫认为,“民主资本主义”是增进普遍福利的最佳制度。但他认为,这个制度已开始出现一些状况,因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已不足以实现高速增长,且不平等的加剧已在自由民主的基本机制中造成广泛的痛苦和不信任。一方面,富豪囤积财富,废除了一些旨在增进包容性繁荣的政策,另一方面,一部分中产阶层和工人阶层的反抗手段是拥抱族裔民族主义的煽动家,这些人给出了诱人但终究空洞的承诺,进而正在毁掉正当程序和政治权利。沃尔夫认为,用共同利益和对共同利益的忠诚恢复普遍的公民意识,是唯一的出路,但他对美国在这个十年结束前依旧维持民主不抱太大希望。
沃尔夫的分析恢弘丰厚又细致入微,我们从中可以收获一些宝贵的教益。但整体而言,本书在诊断和处方方面都存在一些严重缺失。他倾向于低估刺激右翼民粹主义兴起的文化因素,他的改革建言在构想方面过于谨慎且缺乏厚度。除了经济方面的不安,文化地位上的焦虑和怨恨或许可以最充分解释高收入国家缘何接纳了反民主人士。
这不是宽容经济不平等的理由,相反,我们的行动理当远多于沃尔夫的建言,以抗击经济不平等。但这是一个质疑如下主张的理由:只要资本主义繁荣,只要经济收益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更公平的分配,民主就能得救。
民主妥协是如何被败坏的
沃尔夫以民主的简短历史开篇,这段历史可以恰当追溯到两千五百年前的雅典。(似乎并不广为人知,沃尔夫也没有提到的一点是,一些形式的民主涌现在古代世界形形色色的地方,包括美洲原住民和印度-佛教社区。)述及过去几个世纪时,沃尔夫没有提到海量涌现的有关民主起源的文献,那些文献对理解今天民主资本主义的危机有一定启示意义。
本书的一部分将民主(主要是欧洲的民主)视作两大群体之间的妥协: 一大群体是经济精英,他们对确保财产权利饶有兴致,同时畏惧大规模动荡;另一大群体是工人阶层和农民,他们吵嚷着争取政治权利。他们之间的议价拓展了选举权和政治代表权,确保了言论、集会和结社的权利,这些权利最终形成了不同强度的福利制度,缓和了工人的诉求。在这一安排中,经济精英有财富的力量,工人有人数的力量,但群体利益显然一直以来都比沃尔夫强调的更重要:对共同利益怀抱共同信念的公民权利理念。尽管这种基于利益的民主起源理论与自由主义理念的作用无关,无法形成一种完备的解释,但也不会被完全无视。
理解当前危机的一个进路是,寻找解释这一历史性妥协败坏的因素。在游说商业友好型的法律和规章,和通过企业捐赠选举同谋政客方面,政治活动中金钱的影响力都已大出很多,选举开销越来越庞大,乃至于经济精英不再需要在工人的政治权利和福利制度支出方面做出同样多的妥协。美国是政治生活中金钱最为肆虐猖獗的国家,也是坚壁清野的反工会政策比其他富裕国家更恶劣实施,且福利国家提供的工人安全网相当零乱碎裂的国家。
此外,这些民主国家自夸的法治往往是空洞乏力的,许多法律就本质而言是待价而沽的。由托尼·布莱尔、比尔·克林顿,甚至是贝拉克·奥巴马领导的中左翼政党在选举中总是苦苦挣扎(并失去了许多独立人士的道义支持) ,因为他们依旧忠于大财团,那些财团为竞选提供了大量资金,由此严重制约了政策。
在本书中的不同部分,沃尔夫有相当多理由对金钱的这种恶行影响愤愤不平,但除了敦促理当减少这种影响,他并没有用太多篇章给出可行的制度改革方案。比利时、西班牙、德国、瑞典和加拿大为选举或政党提供公共资金的经验,以及其中一些国家限制政党和候选人支出的经验当中,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有很多。茱莉娅·凯奇(Julia Cagé)在其2020年的《民主的代价》(The Price of Democracy)一书中提出了一系列建言。或许并非所有她的建言都很容易实施,但至少,取消对(大额)私人政治捐献的税收减免应当是可行的。近年来,一些政治候选人在从很多人那里众筹或筹集小额捐款方面一样是成功的。(茱莉亚·凯奇,是巴黎政治学院经济学系副教授。——译注)
其他一些方式(在某些方面更为阴险)也削弱了民主妥协。在最简单明了的妥协故事中,工人阶层被认定是团结一致的,但经济需求(比如,他们通常支持的最低工资或公共卫生福利)和文化需求(比如,反对同性恋权利或堕胎,或者,在美国的特殊情况下,反对枪支管制)之间的楔形物往往会分化他们。在这方面,受教育程度更高、专业程度更高的知识经济工人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蓝领工人之间在职业、地域、生活方式和态度方面日益扩大的鸿沟,对精英阶层有所帮助。托马斯·皮凯迪(Thomas Piketty)嘲讽前者为“婆罗门左派”(Brahmin Left) ,但与富有的“商人右派”(Merchant Right)和工人阶层中的右翼相比,人口的这一部分也碰巧更同情社会的边缘群体,即移民和少数民族。(托马斯·皮凯迪,生于1971年,法国经济学家,任教于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和巴黎经济学院。——译注)
除了腐蚀工人阶层提出要求的共同基础之外,工人阶层内部分化影响民主运转的方式还包括彻底的排斥或压迫。如沙伦·穆坎德(Sharun Mukand)和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指出的那样,在民主妥协中,一些既没有财富也没有数量优势的群体——社会中形形色色的少数群体(比如由种族、宗教、语言、性别认同或性取向来定义)——往往被遗漏了。假如他们与多数群体的关系出现紧张,他们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就受到威胁; 保护这些少数群体的权利有赖于特别的宪法规则和落实那些规则的独立司法机构。正如民粹主义的煽动家最近所展示的那样,假如那些规则和机构不存在,民主就可能堕落为多数主义,或詹姆斯·麦迪逊所称的“多数的暴政”。(沙伦·穆坎德,英国华威大学经济学系教授。丹尼·罗德里克,生于1957年,土耳其裔美国经济学家,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詹姆斯·麦迪逊,生于1751年,卒于1836年,1809至1817年担任美国总统。——译注)
这两类分化都涉及文化议题,在沃尔夫的书中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尽管他提到了一些文化因素,但他将经济因素放在首位: 生产率增长放缓,贸易动荡或自动化造成的失业,2008年的金融危机,精英阶层不劳而获的租金和超额利润,以及因而发生的被当成了工人阶层焦虑和愤怒源头的不平等上升或高度不平等。与其说是沃尔夫强调的当前经济状况,不如是说代际流动性放缓,尤其令那些工人对长大后的子女感到焦虑,哪怕他们自己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如经济学家柴提(Raj Chetty)和他的合著者指出的那样,到35岁左右,1940年出生在美国的孩子有90% 的机会获得比他们父母更高的收入(经通货膨胀调整后) ; 而对1980年出生的孩子来讲,这个机会减少到了50%左右。(柴提,是哈佛大学经济学系教授。——译注)
被淡化了的文化议题
在我看来,这些显而易见的重大经济议题与同样重要的文化议题交织在一起,但是在诸如“笨蛋,重要的是经济”这样的章标题中,沃尔夫淡化了文化议题的作用。
沃尔夫需要解释的谜题是,经济不平等是一个标准的左翼议题,但在许多国家,中下阶层和工人阶层现在正转向右翼。沃尔夫确实简短提出了这一疑问,但在一段话中打发掉了; 即使在那段话中,他也几乎没有谈到工人当中的文化分化,只是提到了杰里米·科尔宾的“老派社会主义”在英国的无效。(他忽略了美国的伯尼·桑德斯和法国的让-吕克·梅朗雄等左翼人士一定程度上更成功的经历。)沃尔夫使用的一个数字显示,在瑞典,实际收入持平或下降的家庭比例在2005年至2014年间只有20% (当时25个发达国家的平均比例为65%),然而反移民情绪急剧高涨,并最终助力源自新纳粹的极右翼政党瑞典民主党在选举中大有斩获。看上去,是文化,而非经济,在这里发挥了重大作用。(杰里米·科尔宾,生于1949年,2015至2020年任英国工党党首。伯尼·桑德斯,生于1941年,是美国佛蒙特州联邦参议员,独立派人士;让-吕克·梅郎雄,生于1951年,2017至2022年担任法国国民议会议员,三度参选总统。——译注)
假如沃尔夫乐意深究这一疑问,他必须直面文化议题的突出性。
首先,沃尔夫反复声称,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失败,加上要对2008年毁灭性的金融危机承担责任的精英操盘手逍遥法外的事实,使工人们失去了对精英阶层的信任。但哪一些精英呢?右翼煽动家更反对自由派的文化精英,而不是金融精英; 他们上台后通常做的第一批事情之一,是减少向富人征税,削弱商业监管,同时严厉斥责自由派对少数族裔、移民和性“异端分子”的让步。当然,肯定不是所有社会意义上的保守派工人都受经济愤怒的驱使;对沃尔夫所谴责的滥用市场力量和资本主义的金融操纵行为,许多人没有直言不讳。基于田野调查,社会学家阿莉·霍赫希尔德(Arlie Hochschild)在其著作《故土的陌生人》(Stranger In Their Own Land,2016年)中报告说,路易斯安那州贫穷的白人工人对少数族裔和移民的不满,超过了对大型石化公司,数十年来,那些公司毒化了他们的土地,造成社区中癌症病例多发。
其次,假如不平等和对不公平的食利经济的愤怒是工人阶层愤怒的主要来源,那么为什么部分工人会集结在唐纳德·特朗普、奈杰尔·法拉奇(Nigel Farage)、马琳·勒庞(Marine Le Pen)和欧尔班·维克多(Viktor Orbán)之类财阀麾下?人们必须关注他们的民族主义和反移民口号,以及他们直接攻击自由派的粗俗方式的文化吸引力。如沃尔夫本人指出的那样,在英国,那些保守党紧缩政策的受害者受到英国脱欧口号文化吸引力的诱惑,反而是支持保守党的。我在自己的新书《不安全的世界: 富国和穷国的民主觉醒》(A World of Insecurity: Democratic Disenchantment In Rich and Poor Nations)中明确提出,不只是不平等,经济和文化上的不安全感,令包括中产阶层工人在内的工人忧虑和躁动。最富有的1%人群如何积累财富,不会令他们有多么不安。(奈杰尔·法拉奇,生于1964年,曾任极右翼的英国独立党和退欧党党首。马琳·勒庞,生于1968年,曾任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主席,三度竞选总统。欧尔班·维克多,生于1963年,是现任匈牙利总理。——译注)
第三,在许多情况下,右翼采纳(或配合)了支持工人的福利政策或社会保护措施,由此打击了左翼的士气。很多福利政策受到极右翼政党的支持,那样的政党在德国是新选择党(AfD),在法国是勒庞的国民联盟。美国是个例外: 共和党反对波兰的右翼执政党即法律与公正党(PiS)所狂热支持的儿童援助政策。
第四,右翼使用的文化叙事在影响公共舆论方面比左翼自由派使用的阶层政治的经济叙事更有效。调查结果表明,人们往往极大高估移民和少数民族人口的规模,但极大低估财富不平等和种族财富差距的程度。那种某个文化上的多数人群遭遇围困的叙事和“大替代”(Great Replacement)之类白人民族主义阴谋论的魔咒,是难以打破的,助长了一种受害情结和有关地位焦虑的有毒文化形式。社交媒体恶化了整体状况。在社交媒体上,右翼在传播谎言方面似乎占据优势:那些谎言越是无耻,就越有可能像病毒一样传播开来(社交媒体公司也就可以越多获利)。有证据表明,在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前的三个月里,脸书上偏爱特朗普的虚假故事被分享了大约三千万次,而偏爱希拉里·克林顿的虚假故事被分享了大约八百万次。
工会可以如何作为
资本主义与民主的艰难联姻,这一比喻在沃尔夫的思考方式中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乃至于他提出的问题解决方案往往带有婚姻顾问建议的味道。他呼唤“义务、公平、责任和体面的道德价值观”,并敦促“精英阶层成员必须成为榜样……要诚实而非谎言,要克制而非贪婪,诉诸亚伯拉罕·林肯所称的‘我们天性中更美好的天使’而非恐惧和仇恨”。如是道德劝诫的局限性是明显的,尤其是在社会和政体中的冲突集体爆发的背景下,那些冲突会提出议价、反制性力量甚至是阶层斗争之类议题。
强大的工会是集体抵制被操纵的资本主义的一种显而易见的形式。沃尔夫承认,工会的弱化已经产生了“悲剧性的社会和政治后果”,但在如何重振工会和重新定义工会的目标方面,他没有坚持到底。他似乎支持出于宏观经济的理由限制国际资本流动,但他没有强调,当资本可能流向其他地方时,那些限制措施也会削弱资本的不对称杠杆,由此提高劳动者一方的议价能力。(罗德里克在有关全球化的早期文献中注意到了这种不对称性。)也有意见强烈要求改革美国的劳动法,将工会活动扩大到行业层面,而非企业层面。
工会的目标和职能也需要更广泛一些。我们从德国职工委员会的长期经验中得到的有力证据显示,大公司的领导部门有显著多的工人代表有助于提高生产率,并在不损害利润的情况下确立可信赖的产业关系。(在其2020年的总统初选中,伊莉莎白·沃伦参议员是这一主张的主要支持者。)假如工人在公司运营中享有重大发言权,他们就能影响到公司的决策,将研发方面的投入从当前的劳动力替代方向,向劳动力吸收方向外包或重新安置和转移。一个要求在制定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迄今为止,这些规则一直受到企业游说团体的严重影响)过程中拥有发言权的工会联盟,可以降低普通工人的反全球热情。
此外,工会可以与民间社会团体合作,在塑造共同公民身份方面发挥枢纽性的文化作用,由此发挥远在经济领域之外的作用。过去,特别是在欧洲和拉丁美洲,但也是在美国,工会在当地文化社区中发挥重要作用。工会的衰落掏空了工人内部共同的意义和身份感。煽动家带着他们的种族主义、排外的文化战争议程步入了这一文化空白。在一个充斥着恶毒的虚假信息和假新闻的世界里,在社交媒体放大愤怒和怨恨并制造极端主义回音室的同时,工会可以与其他社区组织合作,在提供指向公共信息服务和确实是独立机构提供的新闻的链接方面有积极作为。
工会在培育民主方面发挥的作用,是在政府和市场之外运作的民主机制的更广泛讨论的一部分,而沃尔夫基本上忽视了这一讨论。
已故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埃里克·奥林·赖特(Erik Olin Wright)有一个他称为“真正乌托邦”(Real Utopias)的完整项目:即基于社会变革和探索取代当下资本主义的具体制度选择的真正可能的一些主张。(正如赖特指出的那样,从维基百科、免费且广泛可得的开源技术,到西班牙的蒙德拉贡工人合作社联合会,一些例证已经存在。)在这个项目的第一卷《结社与民主》一书(Associations and Democracy,1995年出版)中,乔舒亚·科恩(Joshua Cohen)和乔尔·罗杰斯(Joel Rogers)提出的办法是加强二级协会,即工会、职工委员会、社区协会、家长教师团体和妇女协会之类组织,在个体公民和国家之间进行调解,从而夯实民主。(乔舒亚·科恩,是斯坦福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乔尔·罗杰斯,是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法学院教授。——译注)
尽管沃尔夫确实设想了一些根本性的国家改革举措,包括抽签决定和旨在进行知情的民主审议的第二立法院,但假如他更严肃地接触有关这一主题的大量文献,他的制度性思考将会得到极大丰富。
民主既非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条件,也非充分条件
本书对创新的也有讨论类似的弱点。沃尔夫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其他资本主义类型的特点,在那些类型的资本主义中,试验的进行并没有放弃民主,或损害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力。相较于美国的资本主义,德国和北欧国家的资本主义对劳动者更加友好,对高收入家庭征税也更加密集,但据一些全球创新指数,它们并没有更缺少创新能力。承认不同类型的创新也很重要。一些创新是破坏性的,挑战了现有公司,与风险资本家合作的美国私人创新者就是这方面的例证。(在这里,沃尔夫援引了约瑟夫·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理论并表达了肯定的意见。)沃尔夫没有讨论其他破坏性较小、更为渐进的创新形式,而累积起来,这样的创新形式会带来重大收益,德国、日本和韩国的一些大型企业组织在这方面已有出色表现。
沃尔夫指出,专利和版权激发了熊彼特式的创新,他也承认,它们可以成为敲诈勒索的工具,甚至成为进一步创新的障碍。但他对其他选项一笔带过。沃尔夫提到了用奖金取代专利的建议,但在疫苗开发的提前市场承诺方面,目前也有一些令人信服的实验。另一模式是国家购买私人专利后置于公共领域[就像法国政府在1839年买下路易·达盖尔(Louis Daguerre)的摄影发明那样,此举推动了摄影技术的迅速发展]。总的来说,沃尔夫似乎支持在发展“动态能力”方面审慎接触产业政策,但对挑选“赢家”持警惕态度。可在初步探索的许多情形下,不会有太多公司出现在一个羽翼未丰的新产业。例如,在东亚的产业政策中,企业是由政府挑选的,但面对国际竞争时,它们较短期内在出口市场的表现往往被用作一种约束手段。(路易·达盖尔,生于1787年,卒于1851年,法国艺术家、摄影师。——译注)
在企业集中问题上,沃尔夫正确强调了积极反垄断政策的必要性,但他的理由是增进竞争、效率和增长,而非壮大劳工力量。他也没有附和人们对大型技术公司不断升级的要求,即偿还这些公司凭借对它们搜集的数十亿用户巨量个人数据的拥有和控制而攫取的利润。相较于孤立的私人用户,国家在与大型技术公司议价方面处于更有利的地位; 例如,国家可能代表自身要求将数字红利的一部分指定用于公共基金。其他建言也在酝酿之中。巴塞罗那市启动了一个市民数据信托基金,这样民众对数据的收集和用途就有了更大的发言权。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安德里亚·纳勒(Andrea Nahler)支持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数据信托,目标是数据资本的民主化。沃尔夫没有触及这些主张。
回到文化领域,在沃尔夫的书中,对民族主义这一首要文化议题的处理太过肤浅。他主要讨论族裔民族主义,但不是那么容易制造分裂、毒性较低的其他形式的民族主义也是存在的,我们不应允许煽动家霸占整个阵地。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美国和印度都有一段市民民族主义的历史,这样的民族主义不是基于族群而是基于自由宪政价值观,这包括尊重少数民族的权利但并不牺牲正当的民族自豪感:很像是为国家足球队感到自豪,同时庆祝其组成的多样性。培育这些价值观的机构对民主至关重要。尤尔根·哈贝马斯同样比较了“宪政爱国主义”与摧毁了纳粹主义统治下的世界的“血与土”爱国主义。据此,同化仅仅要求接受该国宪法的原则。这种有限的多元文化主义或可平息族裔民族主义者对文化上格格不入的移民的一些通常抱怨。
最后,因对高收入民主国家的狭隘关注,沃尔夫的分析在几个方面受到了限制。有人可能会说,民主和资本主义在这些国家所享有的联姻幸福,可以说有赖于一个庞大的全球仆人阶层,而且有时候,这种幸福牺牲掉了民主和其他地方资本主义的繁荣。这一事实理当令沃尔夫的兴高采烈的陈述——比如“全球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时期同时也是民主化的时期”——失去一些光彩。在更宽泛的视角下,民主既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中国的威权资本主义显示,民主不是必要条件;民主在印度的头四十年里并没有特别增进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一事实表明,民主不是充分条件。
发展中国家还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证明反民主的民粹主义的兴起可以与经济失败无关。强劲的经济增长并没有阻止民主在印度、土耳其、波兰和印尼遭到腐蚀。即使在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进行比较,右翼极端主义也并非只在“落后”的地区兴盛繁荣。在印度,右翼极端主义在古吉拉特、卡纳卡特和马哈拉施特拉等增长迅速的一些邦兴盛起来;在巴西,历经工人党十三年以上的施政,经济不平等显著下降,但工人党在2018年仍输给了雅伊尔·博索纳罗(Jair Bolsonaro),直到2022年才勉强胜出。[这种现象在发达国家是显著的。马泰奥·萨尔维尼(Matteo Salvini)领导的北方联盟(Northern League)是意大利经济发达地区的主导政党。此外,正如波士顿评论一篇文章所论,从选举角度看,特朗普的基础选民中,最重要的一部分生活在地位受威胁最严重的一些相对富裕、快速多元化的郊区,而非赤贫的美国农村地区。](博索纳洛,生于1955年,2018年10月至2022年10月担任巴西总统。——译注)
对所有这些事实的解释原本可以更凸显文化因素。对非正规工人主导劳动力队伍的发展中国家给予更多关注,本来可能促使沃尔夫认识到,有必要制定全民医疗保险和全民基本收入之类政策,在正规和非正规工人之间架起桥梁,增强劳动者的议价能力,可在劳工运动分散而薄弱的美国和印度,这些政策是不存在的。沃尔夫过于迅速地否定了全民基本收入,但在我看来,全民基本收入对贫穷国家来说是一项尤其不可抗拒的政策。
结语
因此,总的来说,关于改革,沃尔夫给出了许多有见地的总结,这遵循了他极为站得住脚的座右铭“不能过度”;他还零星提出了一些看似合理甚至激进的建议。但他没有为民主和资本主义提出一种可行的制度形式的替代架构。那些着眼于实现共同公民地位的勉强劝诫,在当前的危机面前是无能为力的。
喜欢我的文章吗?
别忘了给点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