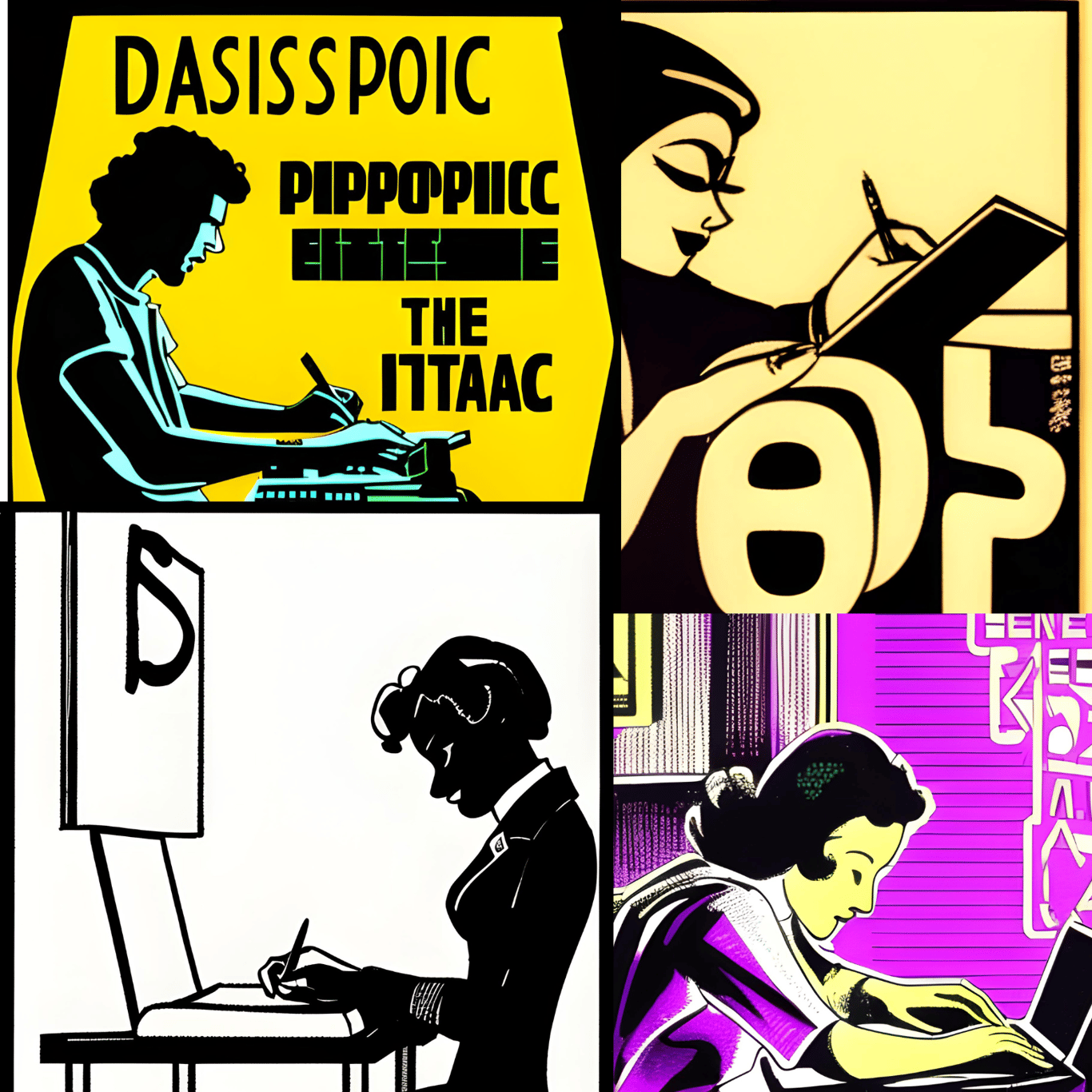
离散纪事Diasporic Letters
离散纪事Diasporic Letters
这个合集是我离开香港、深圳以来,在欧洲不同国家的离散纪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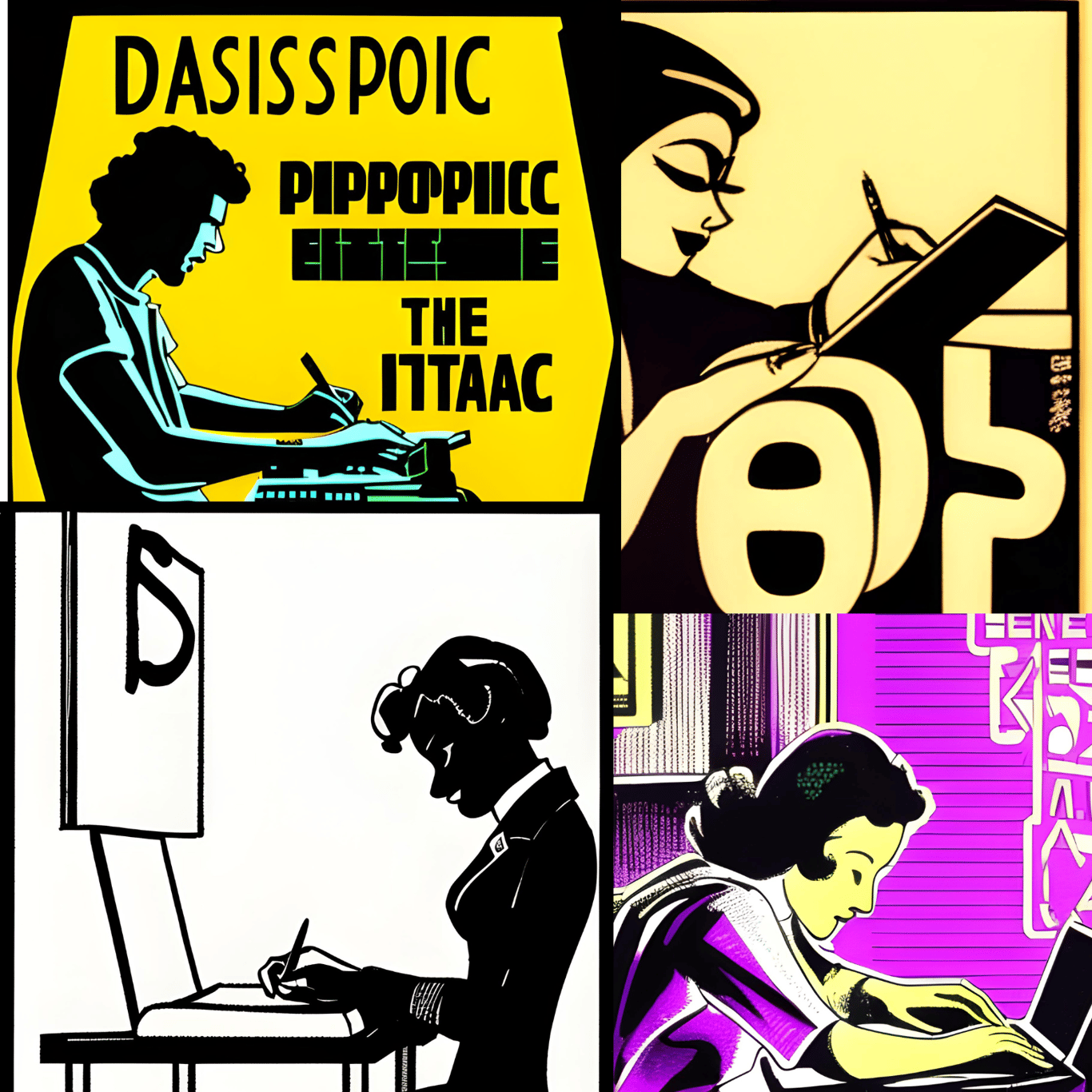
离散纪事Diasporic Letters
离散纪事Diasporic Letters
这个合集是我离开香港、深圳以来,在欧洲不同国家的离散纪事。
一个移民的社交媒体文本细读
本文最初发表在微信公众号「邹思聪的欧洲笔记」,一日内被删除。也因此,我启动了Substack新闻信「Diasporic Letters 离散纪事」,如今再更新在Matters「沈於淵」账户上。欢迎Matters的朋友们订阅新闻信。

客居己乡的小事
我会经常想象她后来的生活。我甚至在想象中,给她安排了一个Marjane Satrapi的人生。她应该要去维也纳,后来可能开始当个画家,给《纽约客》撰写图像小说,画出另外一部《我在伊朗长大》出来。

大流行下,抵达哥廷根
也是那时候,我听到了一首叫做《哥廷根》的法国香颂。那首歌唱:“好吧,我们有我们苍白的早晨,魏尔伦的灰色灵魂;而他们,本身就是忧郁的,在哥廷根,在哥廷根。”

家园的长链:哥廷根的异域来客
我们一边闲聊,一边散步到哥廷根大学的主图书馆门口,今晚是一个月圆之夜。我停下来,望向这个温和的月亮,发着呆,居然不自觉地叹了口气。在明亮的月光下,我能看到自己嘴里冒出清冷的白雾。莫尔也在凝望月亮,接着转头对我说,自己读过不少阿拉伯语翻译的中国古诗,“你们中国古代的诗人,是不是总爱书写月亮?

在波兰,乌克兰人的双重流亡
我很少像这样为他国人高兴。我感到,她们越是在流亡时,从云端去坚守国内的岗位和学业,在异国参与募捐和抗议,又在异国融入当地社群,她们越是践行这双重的流亡,像一个正常而勇敢的公民那样生活,就离重返之日越近。

出走欧洲这一年
“只要我周围的世界每次都是新的,它就没有成为我的世界;我咬紧牙关生存,去抵御每一次陌生事物的袭击……只有在你可以理解的环境中,刺激才会转化为经验,行动才会拥有目的,一张脸庞才会显得亲近,一个人方能被认识。这些模式构成了意义的土壤。但这显然是移民、流亡和’极端流动性’的危险,因为你从那片意义的土壤中,被连根拔起。

“我是波兰人”:保守革命下,波兰女性会经历什么?
性别议题被视为一种“象征性凝胶”(Gender as symbolic glue),在此口号下,执政党凝聚了各类极右翼主张——改变宪法法院构成、变革教育制度和教材、收买选票、限制媒体、清除国际NGO、抵制欧盟、不欢迎移民与难民(这会带来恐怖主义,并伤害我们的女人)、敌视性少数、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