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七日|陸點半
英語的浪漫種在它的文法裡。
昨天正式確診一項譜系障礙。晚上翻看就診記錄,醫生寫了我''appearance: well-groomed」。作者使用了擬物的修辭手法,表達了就診者是一位剛剪完毛洗得香噴噴的昂首挺胸的薩摩耶。

要確診譜系障礙對我這種人來說是難上加難。因為我是成年人,因為我是女性,因為我的母語不是英文。輾轉於四、五位博士和博士後,他們都驚覺我20歲才來的美國,語言表達竟這樣流利有邏輯。我不禁竊喜:看來我現在的英文程度已經翹到可以頂起一瓶汽水了。
至於我的“第一語言”,我是說自我出生以來講的第一種語言,叫做潮汕話。在美國總聽American-born Chinese們說: “My Chinese is pretty rusty.” 第一次聽這樣的表達就是驚艷。
我的潮汕話也是鏽跡斑斑的。
從未在潮汕地區的老家居住過的我,潮汕話從爸爸媽媽口中習得。爸爸是道地的潮汕男人,濃眉大眼,喜歡冷著個臉;媽媽則是方言天賦極強的越南歸僑客家女人——其實她一點天賦都沒有,只是嫁做人婦的她不得不學習他人的方言,好更融入婆家。於是我的第一聲媽媽爸爸,一定是潮汕話。可惜我生在D城這個充滿廣府文化的城市,自然也撿起他們的語言──白話,這個名字聽起來極乾淨,似張白紙,任你如何塗鴉藻飾也無怨言。在香港文化產業大受歡迎後,它的許多別稱開始被人熟知:廣東話,粵語,廣州話,廣府話…
即使如此,我是後悔撿起這門方言的。也許是年幼的我腦容量有限,小小的身體裡只裝得下一門「母語」。我撿起來白話,丟掉了潮汕話。在D城三年幼兒園讓我熟稔了白話,回頭一看,潮汕話已被我扔下在成長的路上。曾經潮汕話流利的我,變得連「你好」 、 「謝謝」 都不會說,全然只記得粗口和生殖器的名稱。
七歲後搬去了H城。那裡是個客家文化濃厚的三線小城。跟著媽媽去買菜,聽她幹著溫軟的客家話買釀豆腐,歆羨慕極了。在H城一直住到來美國,我的客家話聽力水平也堪頂得起一瓶汽水,但口語水平仍是逢年過節時親朋戚友聚會時活躍氣氛的必備保留節目。
未曾想廣東話在美國是居西班牙語後的第三大語言,在美國的華裔遺老遺少沒有幾個不說它。操著未生鏽斑的錚亮的粵語給我許多便利和機會。只是每每被問到「你是哪裡人」的時候,我便要花好長時間解釋我所待過的兩個城市,還有我的家鄉(我什至沒有在我的家鄉居住過)。再到後來,我乾脆只說:「我是潮汕人。」接著便開始解釋為什麼我家裡是說的粵語,而不是潮汕話。最令我惋惜的是:我是根本不會說潮汕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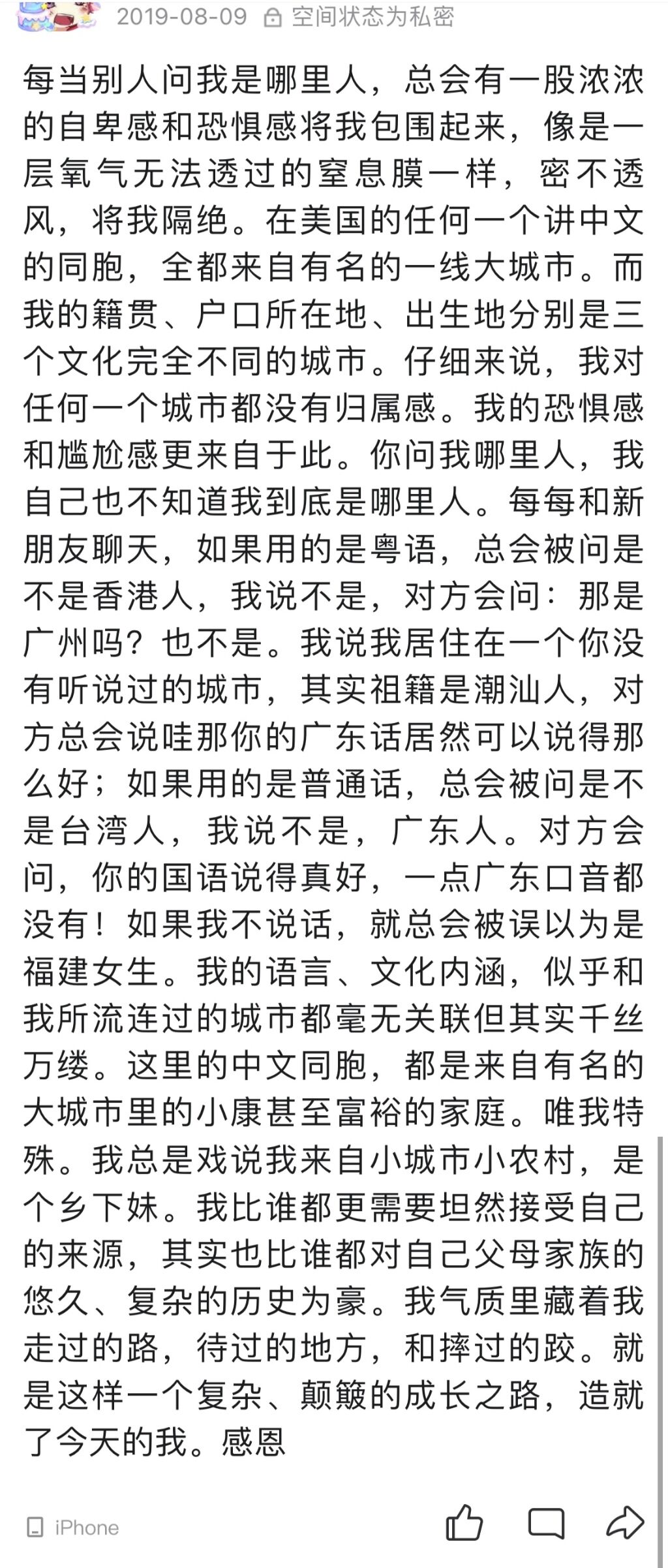
竟把一把通往家鄉的鑰匙給丟了,說來好笑。也曾被自己的表妹質問:「為什麼你爸爸是哪裡人,你就是哪裡人?」這個問題對於父母皆是客家人的她來說,確實很難理解,因為她沒有經歷過這種自我認同的兩難境地。私認為,決定我是「哪裡人」的是我的母語、飲食、習慣。縱使我已不再說潮汕話,但我的口音仍深植於我所說的每一種語言當中;更別提我這「茹毛飲血」的飲食愛好——我實在酷愛生食,而潮汕頂有名的特色美食之一便是生醃。我常打趣說:“大抵是我血液裡的潮汕血脈逼我認祖罷!”
這兩年開始靈性修行後,便覺得我是超越我名字和身體形式的存在,我是哪裡人變得一點也不重要。來找我做塔羅諮詢的個案們叫我“老師”,稱我為“薩滿”;工作上我的職稱叫“會計長;自己勉強叫自己做“靈修者”、“女權主義者” 、「炸雞愛好者」、「執筆人」。那麼多的身份和標籤,那麼多對引號,沒有一個是我真正能從裡面汲取自我感的。我便是我罷——抖掉我身上貼所有著的名詞和形容詞,你還會一如既往地欣賞我和鍾愛我嗎?但當然如果別人再問我是哪裡人時,我還是會回答我是潮汕人。別人好理解嘛。
這篇寫了太多個人隱私啦,算是我的一個樹洞吧。日後會將它刪除歸檔的。謝謝讀到這裡的每一個人。
喜歡我的作品嗎?別忘了給予支持與讚賞,讓我知道在創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續這份熱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