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七日|陸點半
英语的浪漫种在它的文法里。
昨日正式确诊一项谱系障碍。晚上翻看就诊记录,医生写了我‘’appearance: well-groomed”。作者使用了拟物的修辞手法,表达了就诊者是一位刚剪完毛洗得香喷喷的昂首挺胸的萨摩耶。

要确诊谱系障碍对我这种人来说是难上加难。因为我是成年人,因为我是女性,因为我的母语不是英语。辗转于四五位博士和博士后,他们都惊觉我20岁才来的美国,语言表达竟这样流利有逻辑。我不禁窃喜:看来我现在的英语水平已经翘到可以顶起一瓶汽水了。
至于我的“第一语言”,我是说自我出生以来讲的第一种语言,叫潮汕话。在美国总听American-born Chinese们说: “My Chinese is pretty rusty.” 第一次听这样的表达就是惊艳。
我的潮汕话也是锈迹斑斑的。
从未在潮汕地区的老家居住过的我,潮汕话从爸爸妈妈口中习得。爸爸是地道的潮汕男人,浓眉大眼,喜欢冷着个脸;妈妈则是方言天赋极强的越南归侨客家女人——其实她一点天赋都没有,只是嫁做人妇的她不得不学习他人的方言,好更好地融入婆家。于是我的第一声妈妈爸爸,肯定是潮汕话。可惜我生在D城这个充满广府文化的城市,自然也捡起他们的语言——白话,这个名字听起来极干净,似张白纸,任你如何涂鸦藻饰也无怨言。在香港文化产业大受欢迎后,它的许多别称开始被人熟知:广东话,粤语,广州话,广府话……
即使如此,我是后悔捡起这门方言的。也许是年幼的我脑容量有限,小小的身体里只装得下一门“母语”。我捡起来白话,扔掉了潮汕话。在D城三年幼儿园里让我熟稔了白话,回头一看,潮汕话已被我扔下在成长的路上。曾经潮汕话流利的我,变得连 “你好” 、 “谢谢” 都不会说,全然只记得粗口和生殖器的名称。
七岁后搬去了H城。那里是个客家文化浓厚的三线小城。跟着妈妈去买菜,听她操着温软的客家话买酿豆腐,歆羡极了。在H城一直住到来美国,我的客家话听力水平也堪顶得起一瓶汽水,但口语水平仍是逢年过节时亲朋戚友聚会时活跃气氛的必备保留节目。
未曾想广东话在美国是居西班牙语后的第三大语言,在美国的华裔遗老遗少没有几个不说它。操着未生锈斑的铮亮的粤语给我带来许多便利和机会。只是每每被问到“你是哪里人”的时候,我便要花好长时间解释我所待过的两个城市,还有我的家乡(我甚至没有在我的家乡居住过)。再到后来,我干脆只说:“我是潮汕人。”接着便开始解释为什么我家里是说的粤语,而不是潮汕话。最最令我惋惜的是:我是根本不会说潮汕话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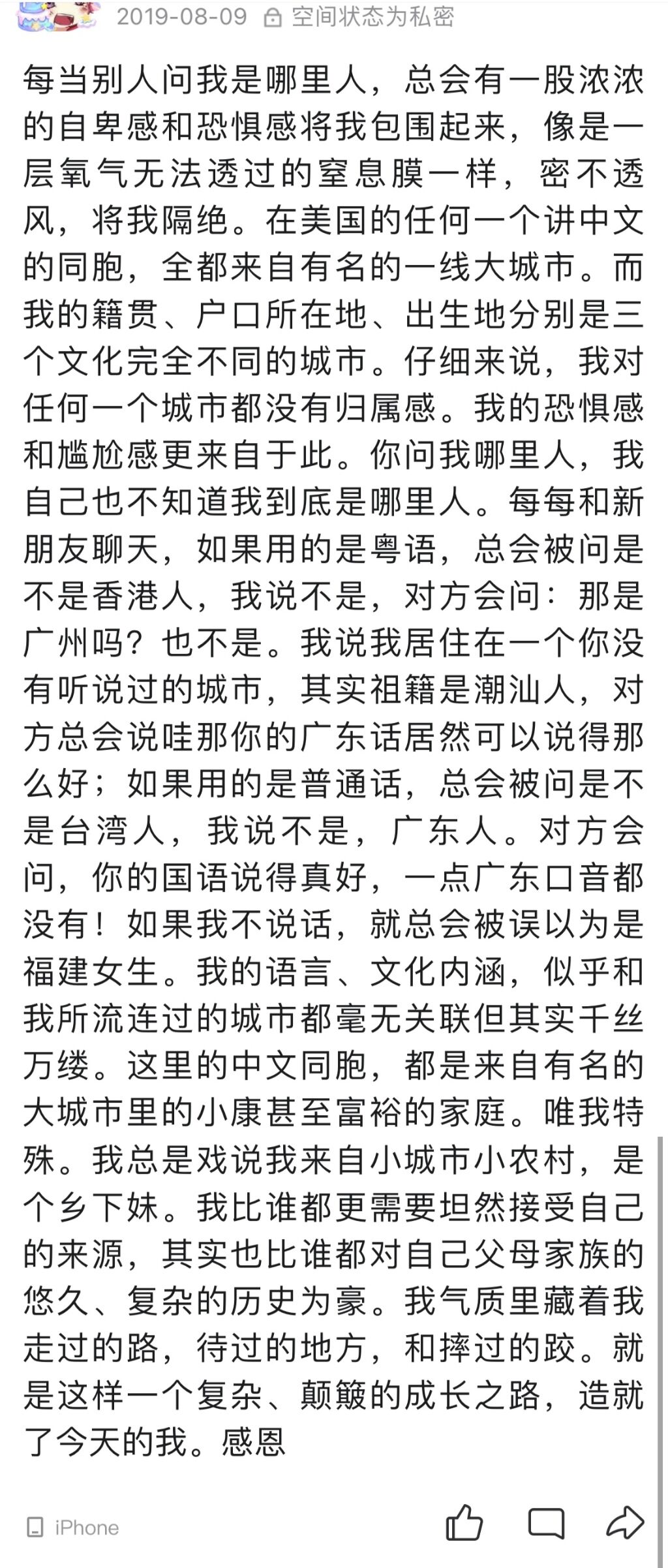
竟把一把通往家乡的钥匙给丢了,说来好笑。也曾被自己的表妹质问:“为什么你爸爸是哪里人,你就是哪里人?”这个问题对于父母皆是客家人的她来说,确实很难理解,因为她没有经历过这种自我认同的两难境地。私认为,决定我是“哪里人”的是我的母语、饮食、习惯。纵使我已不再说潮汕话,但我的口音仍深植于我所说的每一个语言当中;更别提我这“茹毛饮血”的饮食爱好——我实在酷爱生食,而潮汕顶有名的特色美食之一便是生腌。我常打趣说:“大抵是我血液里的潮汕血脉逼我认祖罢!”
这两年开始灵性修行后,便觉得我是超越我名字和身体形式的存在,我是哪里人变得一点也不重要。来找我做塔罗咨询的个案们叫我“老师”,称我为“萨满”;工作上我的职称叫“会计长;自己勉强叫自己做“灵修者”、“女权主义者”、“炸鸡爱好者”、“执笔人”。那么多的身份和标签,那么多对引号,没有一个是我真正能从里面汲取自我感的。我便是我罢——抖掉我身上贴着的所有名词和形容词,你还会一如既往地欣赏我和钟爱我吗?但当然如果别人再问到我是哪里人时,我还是会回答我是潮汕人。别人好理解嘛。
这篇写了太多个人隐私啦,算是我的一个树洞吧。日后会将它删除归档的。谢谢读到这里的每一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