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形.像西西这样的一个女子】与西西从容出入于浮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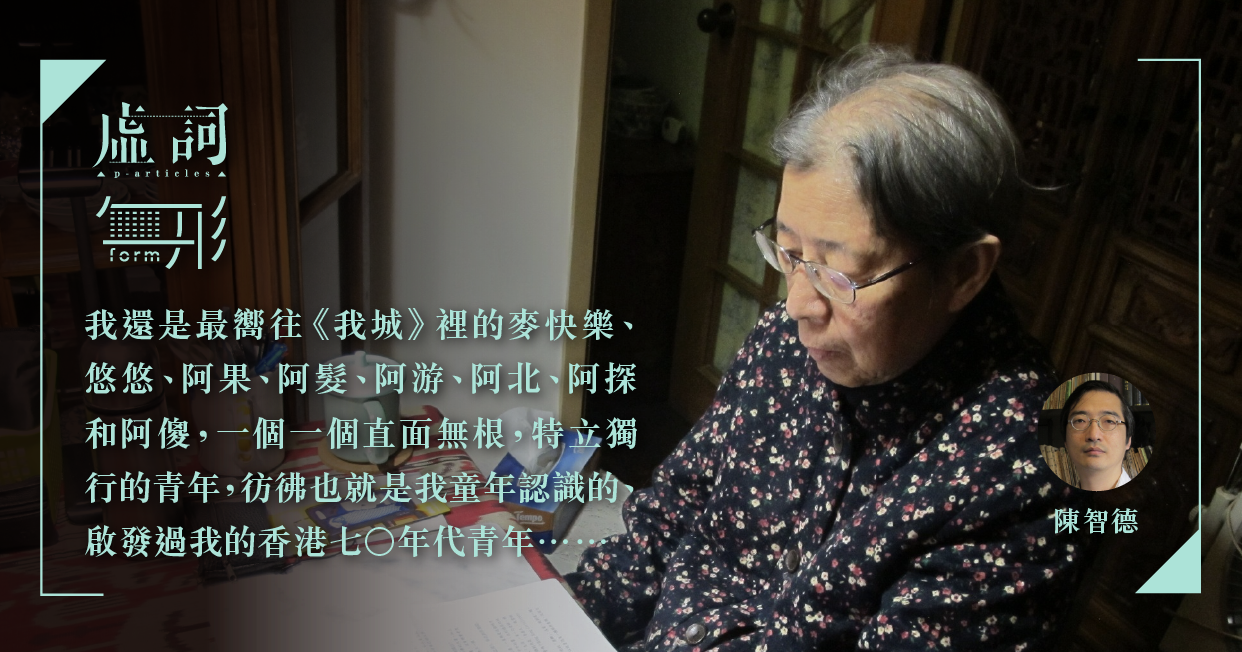
文|陈智德
一九八三年九月,我在报摊买到一份《大拇指半月刊》,之后每期都买来读,读到十一月号许迪锵谈《大拇指》八周年的短文,我才知道这刊物已办了八年,由一九七五年的《大拇指周报》演变为我手上的《大拇指半月刊》,我应该早一点买来读才对啊!当时我刚由小六升上中一,在报摊,在那往返油麻地和旺角的夜路上,很容易就遇到报摊,我买漫画,也买《突破》、《年青人周报》和《大拇指半月刊》,在跌宕的街灯与台灯之间,我逐渐记住了西西、也斯、何福仁、许迪锵、关梦南、叶辉、马若、邓阿蓝、陈锦昌、饮江、洛枫等等作家的名字。
不久,在旺角的二楼书店,田园、学津、贻善堂,我陆续买到素叶版「文学丛书」中的《我城》、《石磬》、《春望》和《哨鹿》,仿佛一一呼应我在《大拇指半月刊》感受到的文字风格,它们鲜活、求新,生活化,像《石磬》中的〈快餐店〉、〈花墟〉、〈美丽大厦〉,也暗藏一些对世俗的抗衡,像〈可不可以说〉这诗,即使我初读时只是个中一学生,却完全理解当中未有说出的反抗性,我最喜欢读到诗的末段有这样的句字:「可不可以说/一头训导主任/一只七省巡按/一匹将军/一尾皇帝?」在那转换量词的轻快节奏中,不明言却引导着对于主流威权形象的颠覆,读来使人痛快,因为在我心目中,学校那位训导主任,实在早已是「一头训导主任」了。我也喜欢〈我听懂了〉这首诗的结束处:「如果千般的爱只有一种/语言/我已经听懂了,并且/跟从你说过一遍」,这样深刻却又制约着情感的语言,真的与我当时在中国语文课本上读到五四初期新诗近乎滥情的诗句很不同。 〈我听懂了〉这诗的副题是「给我的外文老师S姑娘」,我也很希望有机会向《石磬》这书中、另类老师一般的西西说,我在当时已经读懂了,并且,愿意跟从你说过一遍。
在《大拇指半月刊》,有一次我读到西西的〈关于「木兰诗」〉一文,印象深刻因为当时在学校的中国语文课堂上,老师讲到〈木兰辞〉这课文,我正好可以由西西的文章对比学校老师的讲解,所得当然很不一样,特别是西西对〈木兰辞〉的「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这句,从女性角度提出很不一样的解读,我愈发感到,《大拇指半月刊》、素叶版「文学丛书」以及众多我从书店认识的香港作家名字,将为我带来从根本上迵异于教科书以至整个教育建制设定了套路的、完全不一样的文艺生命路径。
西西这一辈战后在香港成长一代作家,包括昆南、蔡炎培、也斯、饮江、钟玲玲、何福仁、关梦南、叶辉、许迪锵等等许多位,承接南来作家于五六十年代的《人人文学》、《中国学生周报》、《文艺新潮》等刊物播迁至香港的文艺,进而吸收西方现代思潮、呼应本地情怀,创建出《新思潮》、《好望角》、《秋萤》、《四季》、《诗风》、《大拇指》、《素叶文学》等等由香港战后一代主导的文艺刊物,以其现代而创发性的文化视野,形成一个生成于民间的公共文化空间。西西这一辈作家的特色,是特别讲究鲜活而独立的角度,不满足于定见,更抗衡建制、潮流和世俗,他们所创造出来的「香港文学」,绝不只是香港一地发表或有关香港一地之文艺,更是一种与香港共同成长的精神、视野和文化态度,他们写出的亦不只是一篇一篇在香港发表或有关香港的文艺创作,而是一种有别于教育建制和世俗潮流的文化、一种独立的知识进程。这群香港作家的传播和影响力,大概无法与教育建制和世俗潮流匹敌,但只要读者真正有心接触、理解,必随着他们进入一道不一样的香港文化门廊、一种新的文化领域。
七〇年代的西西,自六〇年代的〈异症〉、〈东城故事〉所代表的存在主义式虚无风格中挣脱,创出《我城》、〈玩具〉、〈星期日的早晨〉等等展现鲜活语言新风格的小说,尤其《我城》以出殡和迁居而开展的故事,终结束于电话线的安装接通,经过对历史记忆的哀悼和肯定、连串社会现象的呈现和批评,展现出一个一个具鲜活形象的青年,整本《我城》的达观、向上气氛,是由七〇年代青年对文化艺术和社会改革的信念建筑而成,使第一章有关出殡的「那么就再见了呵/我说——就再见了呵」,与第十八章亦是全本小说结束处所说的「那么就再见了呵。再见白日再见,再见草地再见」,两种「再见」展现很不一样的意涵,它们之间也不是二元对立,而是有如硬币之一体两面,寄望于人际的沟通、文化的觉醒和多元开放,缔造出认清了「无」之后始能直面的一座「我城」。
八〇年代,西西在〈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碗〉、〈感冒〉等小说,写出香港职业女性面对社会刻板性别观念上的挣扎,她们自定型的世俗中挣脱出,拒绝接受这世界提供的爱情观、婚姻观,哪怕它是一种众人都认可的潮流:「世界上仍有无数的女子,千方百计地掩饰她们愧失了的贞节和虚长了的年岁,这都是我所鄙视的人物」,西西透过〈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写出她对世俗和潮流的拒绝,某程度上,是与她自《我城》到〈浮城志异〉的文化身份省思密切相关的。 《我城》里的阿果,从一次又一次被质疑国籍与身份的过程中,认清了自己是「一个只有城籍的人」,这种七〇年代的文化省思,连系到八〇年代中期,因中英对方就「香港前途问题」的谈判和《中英联合声明》引致的身份迷惘、移民潮等现象,西西以〈浮城志异〉作回应,小说中的叙事者引用德国作家雷马克著于一九三九年的小说《流亡曲》扉页上的一句:「没有根而生活,是需要勇气的」,寄语总是梦见自己浮在半空的「浮城人」要直面无根、超越无根,再以「明镜」、「窗子」、「乌草」和「慧童」等章节,寄喻浮城人要直面本身的「异」,并由这「异」的重新审视以至肯定,始能现出对香港未来的新视野、新想像,就好像「时间」一章中,壁炉下驶出火车的超现实境象。由这阅读的脉络中,我体会到西西在〈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碗〉、〈感冒〉等小说对女性自主角度的省思,是与她对香港身份的省思相通的, 〈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对刻板性别观念的拒绝,也就是〈浮城志异〉对无根与「异」的直面。
在〈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碗〉、〈感冒〉等小说的女性自主省思以外,西西亦对父性的隐退和消亡具深切描绘,这是西西可能被忽略却是另一使我惊异的所在,她早于一九六八年的散文〈港岛.我爱〉,已从对先父的怀念引申到地方的变迁和认同:「因为有过你的园已经不再有一点痕迹」、「有一间你爱在窗橱外蹓跶的伊利,它们也逐渐隐去,而一切就升起来,城市建在城市上,脸盖着脸」,城市急速发展,最终盖过了西西对父亲回忆的连系,但西西仍肯定对港岛的认同,因为该认同始终与怀念父亲的感受并存:「我开始穿一双红色的鞋,穿过马路,和一个你坐在电影院里。这是一个十分美丽的城,你说。是的,是的,我爱港岛,让我好在明天把你一点一点地忘记。」在〈港岛.我爱〉这散文里,人与地是不能分割的,是共同的情怀,父性的隐退、消亡,同时缔结出新的地方认同。
在众多西西小说的故事角色中,我很欣赏〈玫瑰阿娥的白发时代〉、〈梦见水蛇的白发阿娥〉和〈照相馆〉中的白发阿娥,那穿越事物真幻的淡然,但仍在世界诡变中挥不去瞻前顾后的复杂情怀,也许某程度上,反映西西在时代转折里的思考。着于二〇〇〇年的〈照相馆〉,是从一九八〇年代的〈春望〉伊始的「白发阿娥系列」小说的最后一篇,白发阿娥在那老旧屋村边陲行将结业的照相馆里独对旧照,在香港那年代的「旧区重建」背景中,小说弥漫一片旧人事终止和离散的气氛,在小说的结束处,当阿娥从冲印底片的黑房走出,照相馆的大门出现一位女孩洽拍学生照,女孩的叩门声仿佛一种香港新一代的叩问,然而小说没有顺应一般人的预期,西西可能根本是有意拒绝这预期,阿娥没有和叩门的女孩发生任何连结,她只是很轻淡地,着女孩另找他店光顾:「小朋友,对不起,我们的师傅回乡下去了,你到码头那边的照相馆去拍照吧」,就此结束了全篇小说,阿娥拒绝女孩的理由是「师傅回乡下去了」,实际上是店主要移民、照相馆要结束、阿娥一家都要搬,小说的重点在于阿娥的生命回忆和淡然态度,结束在对于叩门女孩的拒绝,同时也暗示着对于未来的拒绝。
整个「白发阿娥系列」小说,结束在拒绝预期一幕,也等于拒绝温情、继承、感伤或感动等等的读者喜好预期,可说是一个十分孤高、又是个十分「西西」的结束。西西毕生拒绝顺世、拒绝顺应世俗预期的唯一例外,可能是答应陈果纪录片《我城》的拍摄吧,陈果的《我城》并非不好,只是西西置身各种镜头和拍摄程序的安排当中,大概感到愈来愈厌倦吧,西西始终是拒绝顺世的,在她最后留下的《我的乔治亚》、《缝熊志》、《钦天监》几部作品,还以她一种率性自由而难以逾越的文艺高度。
昔日我从报摊每隔两周按期买回家的《大拇指半月刊》,庆幸仍有几份保存至今,可说已是「白发大拇指」了,它们与许多同样已残损、褪色的旧书刊一起,竟随我身飘移,不过仍是那一道拒绝被设定的文艺生命路径。但如果可以的话,我还是最向往《我城》里的麦快乐、悠悠、阿果、阿发、阿游、阿北、阿探和阿傻,一个一个直面无根,特立独行的青年,仿佛也就是我童年认识的、启发过我的香港七〇年代青年,忘不了那飞扬的生命情调,他们一定活在那自由鲜活的、以文艺或信仰或一切的理想作护照、从容出入于无边境、无国籍的浮城。
陳智德詩人,作家,曾任香港教育大學文學及文化學系副教授,著有《根著我城:戰後至2000年代的香港文學》、《地文誌:追憶香港地方與文學》、《這時代的文學》等。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