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该基因化了吧,女性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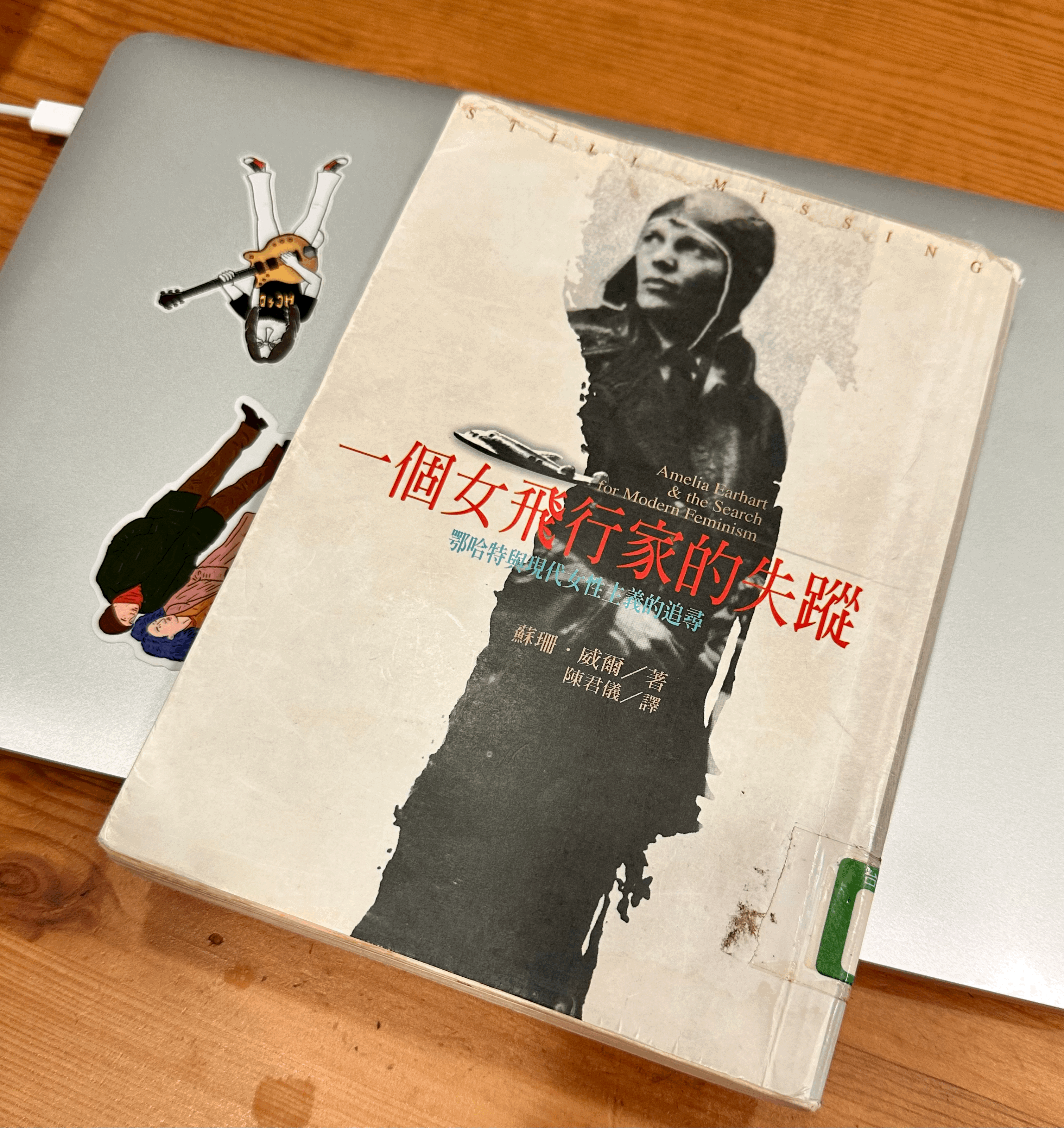
《一个女飞行家的失踪:鄂哈特与现代女性主义的追寻》(Still Missing: Amelia Earhart and the Search for Modern Feminism),是关于Amelia Earhart 的故事。最早知道她是从苹果1997 年那著名的「不同凡想」(Think Different)广告片。因为太喜欢这支广告,曾去研究当中所有人物乃何方神圣。 Earhart 现身于第37 秒,那个高高瘦瘦面带男孩神韵的短发女孩是也。
Amelia Earhart,过去我仅知她是第一位成功独自飞越大西洋的女飞行员,生命消逝于人类首次最长距离飞行——环赤道——的最后一段南太平洋航程中。因为她勇敢无畏的开创性冒险精神被贾伯斯视为范型人物,所以将她纳入不同凡想名人录中。稍微提一下,女性主义者一定很讨厌我在飞行员前面加上「女」字,但以她身处的二三〇年代而言,女性如此从事确实值得大书特书;我不想以今非古,所以还是写女飞行员。
不过在读了这书后,我认识的Amelia Earhart,又多了一个更让人钦佩的女权运动者身份,她无疑是第一波女性主义代表性人物。
举个例,Virginia Woolf 在1928 年说女人要有自己的房间,但Earhart 希望的是一个意义上「允许做自己的空间」,而非实际上的自我独处。碰巧1928 年也是Earhart 首次飞越大西洋而声名鹊起的年头,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位女性解锁此等成就,即使那次她并非驾驶员,仅负责航程记录工作(前面提到的那次越洋成功是之后1932 年的事)。这么说起来Earhart 还比Woolf 更前卫,岂不?
又如Earhart 日后做了自己从前无法想像的事:结婚,可她婚前曾致信予未来丈夫,要求「如果我们发现在一起不快乐,你一年内会放我走。」直至1937 年逝于太平洋前,她都没有让婚姻走到那一步。有办法让家庭和事业并行无碍,以身作则向社会证明女性也可以在保守环境下务实地自主人生,在男性的世界里开辟自己的天空。
事实上她丈夫布南先生不但没有成为拖油瓶,更是她之所以能够做自己的重要后盾。他为妻子宣传、演讲、出书,像个经纪人般精明地打点行程、搞定媒体与塑造形象。夫妻各有生活及工作重心,齐心打造进步又成熟的形象,没有谁属于谁的问题,只有互为助力。女性独立不代表要与男性绝缘,这在当时很能取得社会主流的认同。然而,第一波女性主义也不乏逃逸者,简直过着与Earhart 有天壤之别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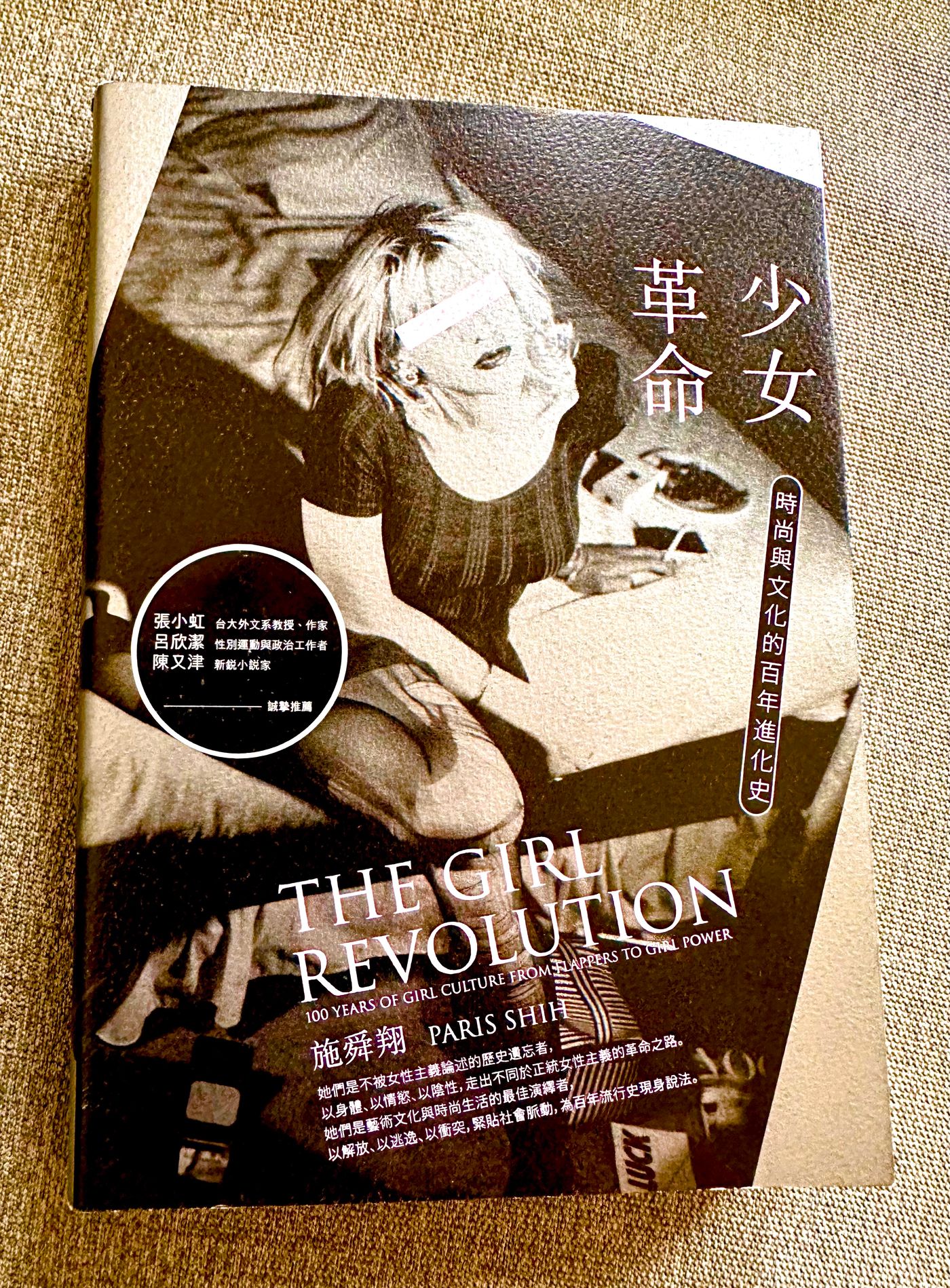
女性主义研究者施舜翔在其著作《少女革命》中说,在前后三波女性主义历史上,其实也各自包含了彼时被排挤于外的非传统女性。
第一波时间跨距较久,按照维基百科所言是从1850 年起至二三〇年代女性获得选举权后结束。 《一个女飞行家的失踪》中亦提到,十九世纪末的职业妇女,经常选择不婚,而和别的女性一起生活,共同经营一个类婚姻家庭。社会倒不甚关心她们的情欲与性关系,直到Earhart 成名的二十世纪二三〇年代才逐渐走回异性爱的潮流。
书中提到这点是因为Earhart 无论内外在,阴性特征从来不明显,自然不见情欲部分。她自幼即热爱冒险,不以相夫教子为人生目标,给人印象永远是短发、衬衫与长裤。这与当时崛起的好莱坞女明星凯萨琳赫本(Katharine Hepburn)形象相似,那也正是Coco Chanel 塑造女裤时尚的年头,可见独立自主的女性正开始走入大众视野中。
若再把时间拉前一点,回到十九世纪末期,由Henry James 的《波士顿人》(The Bostonians)书中来体会两个追求女权事业的女子如何正大光明同居一起相濡以沫。此书写于1886 年,当时社会仍由男性彻底主宰,身为男性的Henry James 为何可以写出一本戮力宣扬女权的小说,而且还隐含女同志倾向,想来真是神奇。后面这点可从上上段论及《一个女飞行家的失踪》中获得佐证,而前者其实有一点讽刺,因为Henry James 安排聪颖可人的女权精灵Verena 最后嫁给思想保守的南方传统大男人Ransom 先生,让她的多年同性导师兼战友兼爱人兼经纪人Olive 小姐败得一蹋糊涂。

Olive 小姐基本上「不把男人放在眼里,对她来说男人生来就亏欠女人,每个女人的讨债额度无上限。」如果这是上世纪末所崛起的最早女性主义者面貌,那简直可称得上百分之百厌男情结。我特别对两段Henry James 用来强化基进女性主义者讨人厌的插曲感兴趣:一段是Olive 的古板姊姊说「宁可被男人践踏,而不是被女人谴责。哪天Olive 和她的伙伴掌权了,肯定会变成史上最糟糕的独裁者。」
第二段是资深女权运动领导人Farrinder 太太觉得自己总是得包容世间顽固的人事,尤其是女权人士的某些习性。所以她说「如果男人的世界尚且如此,心思更细腻的女性就更不用说了」,这无非呈现女性主义初滥觞即萌发嫌隙之芽,遑论150 年后的今天。
当然,Verena 在小说尾声选择弃Olive 而去,我们当然可以批判Henry James 还是无能破格地让女权战胜父权云云;但从另一面而言,才貌双全的Verena 似乎也预告了新世纪女性所需具备的特质。对比三十年前(1856 年)出版的《包法利夫人》,女性从解放欲望到解放思想,《波士顿人》其实已经让女权意识跨出了一大步。倒是,《包法利夫人》是否可因此被尊为第〇波女性主义?唯作者福楼拜是男性,叭!丧失资格!是这样吗?
二〇年代女性主义的一大重点现象是相对于Earhart 等主流势力的都会摩登女子(flappers),正如那些出现在费兹杰罗小说《大亨小传》、《爵士时代》、《尘世乐园》中的女性,尤其是真实世界中一辈子试图摆脱他阴影的爱人洁妲(Zelda)身上。不过批评摩登女子最严苛的原来不是男人而是女人;什么脑袋空空、打扮愚蠢的干话都出自女人嘴里,更为传统女权运动者所不齿。

《一个女飞行家的失踪》中提到,二三〇年代的女性主义者分为两派,一派支持法律上的平权,另一派支持法律上妇女应受到保障,两者皆认为自己做法才能让妇女获得最大福祉,彼此泾渭分明互不往来;连女性主义这个名词本身都变成口诛笔伐的对象,甚至被年轻女性目为耻辱代名词。 Earhart 自己也不想被这个词套牢,她说:「我不能自称为女性主义者,但我却相当喜欢看到女性处理各种新的问题。」不独为妇运或更崇高的理想来奋斗(这却是《波士顿人》中上世纪末的女性愿景),却因个人主义而形成的自由女性主义有所归属。无需响亮表态支持,却为女性主义打下一剂剂强心针,这是Earhart 的智慧。
当时的女性主义其实就很多种,其中又以「自由女性主义」为核心,强调机会、众生平等,重视个人成就,算是古典自由主义的延续。 Earhart 宣扬此道不遗余力,既以身作则更到处推广「接受性别的差异,排拒性别的不平等」观念。但到底是开始挑战情欲压抑的摩登女子能代表那年代的女性主义,还是全身上下欠缺阴性性征的Earhart 这款女子能代表女性主义?同时也别忘了,她虽结婚却没有小孩束缚,而且她也不用操持家务,因为名人身边自有一堆仆役代劳;更甭说她的天生优势:中产阶级白人。
再次地我不想以今非古说从前的女性主义论述都把非白人排除在外,但光连平权派与维权派这两边女性主义支持者自己都吵不完了,百年前即如此何况现在。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却也似是日常。
第二波女性主义在六〇年代崛起,女人争取避孕、堕胎,以及夺回属于自己身体的其他权利。可是婚姻和家庭仍然是女人宿命,自主与独立不代表女人单身是正常。所以强调单身状态——无论是否真正处于婚姻进行式——的主张,包含情欲追求和开放式伴侣关系,都成为挑战第二波女性主义的反动力量。 《少女革命》书中提到「以单身女性的身体作为逃逸路线」对比「家庭主妇以心智作为革命起点」,这样的身心观点差异。其实真正革命性的突破乃在于此时期伴随民权运动而升起的「性革命」,而且这也预告了未来九〇年代第三波女性主义的开端。
第三波女性主义离我们现在最近,从八〇年代末期开始研究,勃发于九〇年代,维基百科说「第三波女性主义者不仅批评男权与父权,也批评第二波女权主义者,这让他们和第二波女性主义者分别开来。」
彼时的关键词如"girl power" 和"riot grrrl" 都有「少女」,而且都和音乐有关。九〇年代是我的成年时期,从听西洋音乐的高中生进化成迷上摇滚乐的大学生,对于「女力」、「暴女」的音乐风格与社会风气至今仍记忆犹新。
暴女大本营在美国西北华盛顿州的Olympia,以Kathleen Hanna 及她的乐团Bikini Kill 为首,联手志同道合战友自创杂志,写下「 暴女宣言」(Riot Grrrl Manifesto),信仰「有什么不可以」的庞克哲学,以「拯救女性的心灵与文化修养」——套句「她们」的话。这个「她们」指的是谁,不言而喻。

这批回过头来大方挪用父权所施加的污名,重夺荡妇权的暴女们,以自己身体为反向征服男性的武器,不接受反色情论述,挑战「被害者女性主义」(victim feminism),彻底从女性主义叛逃,意欲革正统女性主义者的命,却意外催生出新一波女性主义。立刻为您点播Bikini Kill 的代表作〈Rebel Girl〉,曲名即是最有力的宣言。
更有什者,紧接着拒绝妥协的暴女之后的是「娃娃荡妇」(kinderwhore),代表人物便是鼎鼎大名的Kurt Cobain 那鼎鼎大名的老婆Courtney Love:穿着娃娃装大唱"I am not a feminist / It's not yours / Fuck you!!!" 这实在太杀了!把不分男女所有人通通踩在脚底下,谁敢说她们不独立自主,正如所有女性主义者所追求的?
暴女与娃娃荡妇夺回污名并重新定义污名的手段,一直延续至今,当然也影响了我们当今的台湾。当陈升、伍佰、董事长乐团、张震岳、MC HotDog 为「台客」正名时,原本更具贬意的「台女」也逐渐被去污名化或重塑定义,因此《 台女》这本书应运而生,看得我大开眼界!
正如《少女革命》尾声所言,约莫从九〇年代后半期起,越来越多关心女性议题的年轻女性拒绝被贴上女性主义者标签而被基进运动者视为叛徒,施舜翔说他写《少女革命》目的就是打算拼凑起这些百年来「扰乱了女性主义大论述的义正词严、解构了女性主义线性史的理所当然」的边缘史、阴性史、少女史。这书我五年前初读,如今在几个书写网站因三月妇女月而起的连番征文、争议等论述中重读,再加上刚好自己又才连看几本相关书籍,想法特多,不吐不快。
最主要者,《少女革命》书中提到《柯梦波丹》杂志曾被女性主义者贬为自我物化与性化的父权帮凶,让我想到类似父权打手、厌女帮凶等词语最近好像又常常看到。不是要帮男性讲话,但这类词语总让人感觉充满浓厚攻击性和不友善的预设立场,好像讲来就是要吵架似的。
身为男性的我经常说下辈子很想投胎当女人... 尤其要是个正妹... 就算天生不正也要能化一手好妆,更不惜整形变正... 君不见「正妹经济」和「女性红利」杀很大...
我讲干话?是啦,但老师都可以要小朋友写「我的志愿」作文了,为什么我不能下辈子志愿当女生?但就怕会不会有人攻击我是父权思想作祟?可应该不会有人把我抹成厌女吧?我羡女都来不及了还厌女... 难道要像《波士顿人》中的Olive 厌男才好?但那又会被反女性主义(antifeminism)那挂的女性主义者炮轰政治不正确...
你累了吗?
在这遍地同温层的分众时代里,似乎没能迎来第四波女性主义——近代历史上大约每三十年会有一波——的涌现,即使九〇年代第三波过后也已经进入第三个十年,甚至前几年还发生过风起云涌的#MeToo 运动。应该不能武断地说女性主义已死,但如果女性主义的各种精神已经被深植到各个角落,就像近百年前"It Girl" 风尚中的"It" 那般内化于身体,即见不到也能明显感受到,如此「基因化」当不啻人类文明进步的一条轨迹。
基因化并非意谓遇到问题隐忍不发,而是更要求具备正确观念,以及随时警觉的直觉反应。譬如很多公司都会说某某特质是我们的DNA,并不厌其烦进行宣导以形成文化,我想最有名的例子应该就是强调相信、尊重和正直的"HP Way"。行为的底线在哪里是任何员工都必须要明白的「常识」,但知与行是两回事,而且即使常识也可能随时间而钝化,所以持续教育极为必要。不断内化为DNA 的过程就是基因化,#MeToo 便是一个很棒的基因化案例。
话又说回来,记得#MeToo 时期也出现过反对声音吗,而且还来自女性。以知名影星凯撒琳丹妮芙(Catherine Deneuve)为首的多位公众人物,联名反对现代女性主义者试图把女性刻划成男性欲望下毫无反抗之力的受害者(典型被害者女性主义),拒绝让好莱坞沦为一言堂。
无论如何,这是个由「众小众」组成「全大众」的年代,尊重差异、维护异议才应该是所谓的政治正确。也许该增展的是由理解发展成基因化的包容,消弭迭举大纛以致误解丛生所孳衍的对立。都吵了一百多年还在那边我对你错吗?
你不累我都累了,哗啦啦写了五千字也该停笔打住。此刻我正准备展读Amelia Earhart 1932 年独越大西洋后一周内所推出的《飞行的乐趣》(The Fun Of It),去年终于等到台湾出版社翻译上市,等我看完再说。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