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不去了,要去哪里? ——「文学的原乡与异乡:陈慧X沐羽」讲座侧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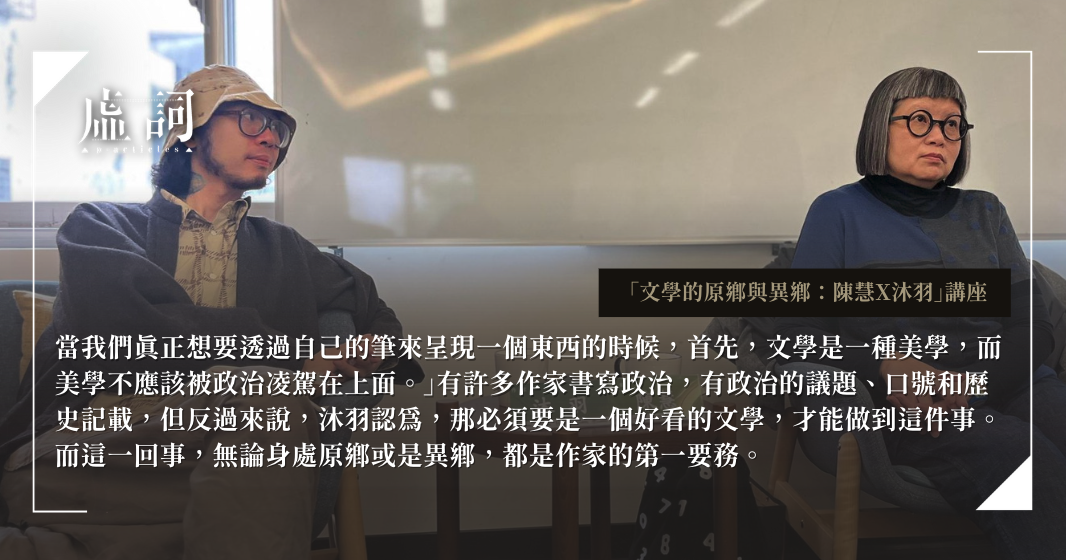
( 原文刊载于虚词・无形)
文|沐羽
作为繁体中文出版重镇的台湾,数十年间持续出版来自世界各地的中文作品,自九○年代始,陆续欢迎了来自香港的董启章、谢晓虹等初登文坛的作家,也出版了也斯、刘以鬯、黄碧云等名家的新旧作品。直到最近,由于2019香港的政治局势变化,新一批作家因各样原因选择台湾作为基地。除了文学出版以外,他们本人亦选择移居台湾。在2024年1月28日,香港文学生活馆在台北纪州庵文学森林举办「文学的原乡与异乡」活动,邀得移居台湾并屡获大奖的作家陈慧与沐羽对谈,讨论在台湾写作的亲身经验。
无独有偶,这天的纪州庵除了这场香港的对谈以外,一层之隔有来自新马的高嘉谦、张贵兴等作家学者对谈「不确定的好人:你不知道的李光耀」。主持人杨宗翰感叹道,台湾在本质上就是一个移民社会,而每个人都在台湾寻找发挥空间。近年来马华文学和香港文学都成了学院里热门的研究题目,而身分认同问题正正就是无论台湾还是香港或马来西亚的核心议题。
没有亲人死去的土地,无法称作家乡
不过,就算是台湾岛内部也有它的移动路径。陈慧说道,她现在在国立台北艺术大学教学时,学生来自岛内各处。无论人去到何处,都无法摆脱「你从哪里来」这个问题。但这个问题饶有深意,她引用在纪州庵馆内看见的朱天心《想我眷村的兄弟们》:「没有亲人死去的土地,是无法叫作家乡的。」如果以这个逻辑看来,台湾是无法成为她的家的。
但哪里才能成为真正的家呢?陈慧的弟弟与外甥在英国,父母葬在香港,而祖父是泰国华侨。香港作为一个移民城市,人们一直移动,难以说清真正的「家」在何方。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陈慧决定换个方法思考:这端看你在什么地方,做了什么事情。如此一来,文学给予了自身一个很特别的身分,唯有在文学里,人可以习惯自己居于异乡之中。

异乡的感觉不只是陈慧,大概能应用到所有移居到台湾的香港人身上。作为九十后作家的沐羽说,自己算是比较晚来的,不只是文坛上的晚辈,也是比较晚出生的。 「我天生就是一个香港人,这好像有点不证自明的。」有血缘,有地理,也有朋友和语言。这一切到了2014年后急剧改变,沐羽指从那时起政府开始与民意背道而驰,但那时他才刚「长大成人」,而且2017年就已经前往台湾读研究所了。
在2014到2019年的多次社会抗争中,沐羽尝试理解这座城市发生了什么事,然而每当理解得这座城市越深,就越不理解自己可以担任什么角色。迷惘是他的关键词。直到后来在2022年出版《烟街》以后,他才找到了不同关于香港的社会学、历史、经济学等等的书籍,研究当时的香港人怎样理解香港。
他举去年年底联合文学出版的五本《刘以鬯作品集》为例,里面写的香港,沐羽只感到「这里是哪里啊」。小说里的香港是罪恶之都,以今日的谐音梗来说就是「国际大刀会」(国际大都会),但这个香港是沐羽完全没经历过的。那是股灾都还没发生(按:1973年香港股灾)的时期,如果说刘以鬯在写作中有一个香港身分,那是跟沐羽的香港身分完全不一样的。
在创作的时候,我们就是异乡人
自刘以鬯的股灾时期,到沐羽出生的年份,大略就是陈慧《拾香纪》里书写的时段。那段被称为香港黄金时期的七○至九○年代,陈慧在后来的续作《焚香纪》写道:那段日子不是流金,其实是锈。在2022年出版《弟弟》后,陈慧得到了台湾文学界的各项肯定,对此,陈慧认为是因为口味相近。
她举在台湾时每年都会看见的现象为例,每逢端午,社群媒体上都会大吵一轮北部粽还是南部粽正宗,除此以外还有肉圆、鲁肉饭等等。陈慧认为,小说也有它的地区性,当她决定在台湾出版一部关于香港的小说时,并不需要台湾读者知道它的宏大背景。以《弟弟》为例,「一个中产家庭,在城市里价值观崩塌时,对下一代的影响」,只要知道这样的概念就足够了。
以诺贝尔文学奖为例,得奖作品都离我们相当遥远,但陈慧认为在文学里面有一些东西是共通的。 《弟弟》的故事,其实是每一个社会都触碰到的代沟问题。 「文学没有疆界」,陈慧说,而这也遥遥呼应了异乡人的说法。没有疆界,因此没有原乡。
说到地区差异,沐羽举出了数年前读过的一部马华小说,邓观杰《废墟的故事》为例。在这部小说出版以后,评论者以「双乡叙事」来形容这部小说,讲述邓观杰有马来西亚和台湾两个乡。沐羽指,第一次看见这个词时相当震惊,原来故乡都可以有两个。如果这个叙事都放在香港作家身上会怎么样?他援引先前陈慧说的「有亲人死去的土地才算家乡」,反过来说,即使有多少亲人死在一片土地上,但如果不想融入,那人永远都是这片土地上的过客。
但就算是香港,放到历史的大框架上说,沐羽认为自己的家族也可能只是香港的过客。在中共建国后他的家人来到香港,如今移居台湾,才不过半个世纪多一些。如果是现在移居外国的作家们,说不定也有「三乡叙事」。如此一来,故乡的议题显得好像是被评论者贴在身上的标签,而人应该找到自己的答案。
陈慧补充道,这大概就是「腔调」所显示出来的差别。就像她如今每次在台湾坐计程车,司机都可以从她的口音听出她是香港人。她的学生也问,为什么来了五年国语还是这样,但她认为腔调跟文学一样,也是属于她的声音。腔调显示了她的来处,「当我们在创作的时候,我们就是异乡人,我们去翻找一些不寻常的东西,翻出一些看似正常但其实并不正常的东西。」
回不去了,要去哪里?
说到「看似正常但并不正常」的事情时,主持杨宗翰将话题带向了未来:陈慧和沐羽的下一部作品。陈慧正在《字花》的线上媒体「别字」上连载一篇小说,在活动时连载到25话,大概会在35话结束。故事名为《小暴力》,讲述在2020年时有一个香港男生来到台湾寻找他的母亲。在写作过程里,她翻查各种相关论文文献,在途中一路对台湾这个地方更加熟悉。 「每个城市都有它的性格,它总有让人意想不到的地方。而我就是一个外来的人,无论怎样也好,我已经在这边了。」

至于沐羽则指,在《烟街》出版后的2022年,他经历了人生中一个非常巨大的挫折,那挫折叫作上班。他停下了几乎所有的写作,到隔年他觉得自己需要复健一下,既然没有办法写小说,那就写散文和评论。由于对办公室这个地方太不满和好奇了,就开始研究办公室的历史和文化,由此重回了写作的道路上。于是在2024年,他出版了散文集《痞狗》,并将与陈慧于台北书展对谈《拾香纪.焚香纪》。
在讨论到从拾香到焚香,又或讲到香港近年的状况时,很多人都会用「回不去了」这个说法。沐羽认为他现在对这个说法越看越奇怪:「有些人想回到英国殖民时期,有些人想回到2014年前,有些人想回去2016或2019年前,甚至有人想回到1980年代柴契尔夫人之前,但反过头来看,难道八○年代至今的东西就没有好的吗?」回到过去,就是把中间建立的好事一笔勾销。沐羽说,还不如分析现在不完美的状况,其后一直走下去。
而陈慧谈到了自己与学生之间的相处,当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聆听。 「原来你是这样想的,这我完全没有想到。」相比起要给一个建议,更多是想听听对方怎么说。她认为,可不可以回去已经没有关系了,更多是要抓住现在的状态。如果抓不住现在的状态的话,去未来也没有用。我们必须整理自己的当下。
「当我们还在写香港,或是书写当下的状况时,首先是要先写好,再来才是写这个议题。」沐羽说:「我们到底在用什么文体?为什么不是散文而是小说?当我们真正想要透过自己的笔来呈现一个东西的时候,首先,文学是一种美学,而美学不应该被政治凌驾在上面。」有许多作家书写政治,有政治的议题、口号和历史记载,但反过来说,沐羽认为,那必须要是一个好看的文学,才能做到这件事。而这一回事,无论身处原乡或是异乡,都是作家的第一要务。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