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网路让我们变笨? 》
利用上班时间重读了《网路让我们变笨?数位科技正在改变我们的大脑、思考与阅读行为》,非常认同书中的观点,同时也得到了很多启发。讽刺的是,我是以电子书的方式重读此书的,在阅读过程中也多次查看邮件与处理其他工作事务,可谓正是本书中批判的分心阅读。
本书主要讨论了网路这种智能科技所带有的智能规范是如何改变人的认知与对知识的看法,从而使我们变成多工处理的杂耍人。
如麦克鲁汉所预期,我们似乎已经来到一个知识和文化史上的关键点,两种非常不同的思考方式要在此交替。我们为了取得网路的宝藏而换掉的(只有小气的守财奴才看不到这些宝藏),正是卡普所称「我们旧的直线思考模式」。冷静、专注、不受干扰的直线思考头脑被一种新的头脑推到一边,这种头脑想要,也需要以简短、不相连、经常重叠在一起的击发方式来吸收和发布资讯,而且愈快愈好。
在书的开头,作者便提出了两种看待世界的方式,以书籍为代表的直线思考和以网路为代表的断裂思考。前者追求专注与深度,后者则是广泛与分心。
这种思考方式的转变是如何发生的,作者以word为例,提到科技对人类书写行为的改变。作者在电脑进化到能进行文字编辑时,使用的修改方式仍维持古老的习惯,即每次写完都列印出来,在纸上修改,最后将修改的版本输入电脑。但不知不觉中,作者发现自己不再需要列印出来了,同时失去了手写与修订的能力。
但不知何时开始,我的编辑程序突然改变了。我发现我没办法在纸上书写或修改任何东西。少了删除按键、卷轴、剪下及贴上功能,和复原的指令,我就觉得失去了方向。我非得在电脑萤幕上做所有的编辑工作。在使用文字处理程式之中,我自己也变成了某种文字处理机器。
科技对我们的改变绝非是单纯的媒介,将旧行为使用新科技进行并不是一种无损置换,这不仅是麦克鲁汉所说的「媒介即讯息」,更显现在科技会改变行为方式,并最终影响我们对此行为的认知。书写变成了一种可随意删减、拖动与复制复原的电子行为,而每一次删改都干干净净,每一个字都可完全抹灭历史般回头重来。书写变得轻盈。
回到网路上又如何呢?作者经历过网路前后的时代,他发现在这个过程中,专注力大不如前,无法进行长时间的单线任务,必须在不同任务间切换。
我头脑运作的根本方式好像也在改变。这时我就开始担心我无法把精神集中在同一件事上超过一两分钟的问题。一开始,我以为这个问题只是中年头脑退化的症状。但是,我发觉我的头脑不只是在慢慢飘走,它还感到饥饿。它要求我用网路喂食它的方式来喂它,而且喂它吃得愈多,它就变得愈饿。就算我不在电脑前,我还是渴望着收信、点连结、用用Google。我想要保持连线。正如微软的Word把我变成人肉文字处理机器,我感觉到网路正把我变成某种高速资料处理机器,一个人肉的HAL。
这想必也是当今时代许多人的共同感受,我们变得不专注的同时,极度渴望使用网路的讯息填满自身。影片也好、FB通知也罢,然而这些东西注定留不下印象,如同一只胡乱把食物塞进嘴里的巨兽,饱食(量)的价值远超过美味(质)的价值。所有人都在杀时间。
在简略提过网路世代的特征之后,作者转而谈到神经科学的发现,如何有助于我们理解网路成瘾。旧时科学家认为大脑的可塑性集中在未成年时期,一旦塑形成功,往后终生都只能进进出出,而大脑这个容器本身不会改变。这种看法逐渐被后来的神经科学发展推倒。事实上,神经一辈子都在建立新连结,切断旧连结。
我们愈老,可塑性会愈低,大脑多少还是会固定下来,但是可塑性永远不会消失。我们的神经元一直不停地切断旧的连结和建立新连结,全新的神经细胞也不停生长。奥兹观察到:「大脑有即时重新设定的能力,以此改变它的运作方式。」
基于这种看法,在哲学上的过往争论,即人究竟是原本就具有天生样板,还是说人是具有无限可能性的白板,神经科学似乎给出了综合两者的答案。
海兔实验证实了「两种看法都有道理,事实上还会互补。」我们的基因「预设」了许多「神经元之间的连结,换句话说,它们决定哪些神经元会在何时与哪些其他神经元产生连结。」这些由基因决定的连结就是康德所谓的天生样板,也就是大脑的基本架构。但是我们的经验会控制连结的强度,或者可说「长期下来的效果」;这会造成思想不间断的形塑以及洛克所主张的「新行为模式的表现」。本来对立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在神经突触中找到共同点。纽约大学神经科学家李窦在《突触构成的自我》一书中说明,先天性格和后天教养「其实说的是同一种语言。它们都藉由塑造大脑突触组织的方式来达到心智和行为上的效果。」
读者在读到这里时,或许会认为此种发现揭露人类的自由可塑性的面向远远高于固着性。然而实际上这是一把双刃剑,愈是强的连结,强化的欲望就愈强,成瘾过程愈没有阻碍。而愈是弱的连结,像被摆在角落柜子底层的相片,可能一辈子都不会翻开,直到搬家忘记带走,永远消失在生命中。
神经具有可塑性并不等于带有弹性:我们的神经回路不会跟橡皮筋一样弹回原始的状态;它们改变后就会保持改变的状态,而这个新的状态当然不一定是让人称心如意的。坏习惯跟好习惯一样,都能轻易烙印到神经元里。帕斯科里昂认为:「可塑性造成的变化,对特定的个体而言不一定是行为上的加分。」可塑性除了是「发展及学习的机制」之外,也有可能是「病理上的原因」。
接下来作者开始论述历史上的智能科技是如何影响人类看待世界的方式,以时钟为例。
机械时钟改变了我们看待自己的方式,而且和地图一样,也改变了我们思考的方式。一旦时钟把时间分割为一系列等长的单位,我们的头脑开始注重将事物切割、度量等等有系统的脑力工作。我们开始在所有的事物和现象里看到组成整体的小单元,再看到组成小单元的更小单元。我们的思考变得如亚里士多德一般,强调找出物质世界背后的抽象排列。时钟扮演了关键的角色,把我们带出中世纪,推进文艺复兴和之后的启蒙时代里。
正如地图和机械时钟的故事所述,智能科技一旦受到普遍运用就会促成新的思考方式,或是把原本仅属于少数菁英的既有思考方式带给广大群众。换句话说,每一种智能科技都包括一种智能规范,一套人类头脑如何运作(或是该如何运作)的假想。地图和时钟有着相似的规范:二者皆重新强调测量和抽象化,以及观察、阐释超出五官感受的形式与过程。
智能科技与智能规范的概念,是我认为本书最重要也最有普适性的概念。智能科技不仅改变了行为的难易程度与广度,同时带来的智能规范隐含的世界观知识与视角才是重点。我们在面对新科技时,往往看到的是智能科技能帮我们做到什么,如同班雅明所谓旧世界的未完梦想,我们是以旧世界的观点看待新科技,带有乌托邦不切实际的幻想。智能规范往往是隐而未显的危机,甚至,如果有人提出警告,会被视为阻碍进步的古板老头。
我们的祖先发展出和使用地图,并不是为了增进概念性思考的能力或发现世界暗藏的结构。这些效果只是这些科技带来的副产品,但是这些副产品是何等重要啊!到了最后,影响最巨的是发明里潜藏的智能规范。智能规范是一种媒体或工具植于使用者脑内和文化里的讯息。
虽然个人或社群团体可以对要使用哪些工具做出不同的决定,这并不表示人类整体有办法有效控制科技进步的方式和速度。我们「选择」使用地图和时钟的说法让人难以信服(好像在说我们有办法选择不要用),更别说我们「选择」接受这些科技的种种副作用:前面已经说明,我们开始使用这些新科技时,经常没料到会有副作用。据美国政治学家温纳提出的观察,「如果我们从现代社会的经验里学到任何东西,肯定是科技不只辅助人类活动,更是重塑这些活动及其所代表意义的强烈动力。」我们虽然很少察觉到这个事实,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例行公事有许多早在我们出生前就被科技定型下来。科技也不能说是完全独立演进,毕竟在我们接受和使用工具背后有经济、政治和人口等等重要考量;但是「进步依照自己的逻辑向前走」的说法一点也不夸大,而这种逻辑不一定和工具发明人和使用人的想法、期望相呼应。工具有时候会依照我们的指示运作,但有时候我们会为了迎合工具的需求来调整自己。
这种观点到了今天依然是许多争论的核心,我们是否有能力控制科技,科技是否会失控。工具是否真的是中立,是否取决于使用的人,仿佛科技是无能为力的物,我们与物之间的关系永远是单向的。可以看到,作者是绝不同意此种观点,我个人也不同意。认为网路只是为人所用,取决于人,而非植入脑袋里的寄生生物,这种看法,多少有点天真。
作者在下一章谈到了书写与书籍,正是我最感兴趣的部分。比如下面这段历史简述。
我们现今很难想像,但早期书写里单字之间没有空格。抄写员写下的书籍里,文字在每一页的每一行里从头相连到底,毫无间断;这种写法现今称为「连续书写」。不间断的文字反映出其口语渊源。我们说话的时候并不会在每个字中间插入间隙,而是音节不停成串从我们口中流出。最早从事书写的人完全不会想到要在单字中间加空格:他们不过是直接写下口说的语言,凭听觉动笔。 (即使在今日,小孩子刚开始练习写字时,也是把所有单字连在一起。他们跟早期的抄写员一样,都是凭听觉动笔。)抄写员也不太重视单字在句子里的顺序。在口语里,意义透过抑扬顿挫和话语中强调的音节来传达;这种口述传统也继续影响书写行为。在阅读中世纪早期以前的书时,读者无法从语序看出句子的意义。这些规则根本还没发明出来。
「连续书写」是口语传统的遗物,可想而知,标点符号和空格则是书写所创立的规范。书写使语言有了意义的分割与停顿,被分割的意义才有堆叠的可能。如今我们或许很难想像,不在脑中切割对方说的句子。或许我们的书写也造成了当今的口语文化,与以前是大不相同的。反过来说,「连续书写」与当今一些小说中的长句子有类似之处,或许与其将这些句子视为「异类」,倒不如说是一种「回归」,难怪那些句子往往传达出一种急切的语气,仿佛一个将死之人急切要把最后的话说完。
那阅读呢?在书籍能大量复制的时代,阅读又将造成怎样的改变?
读书要的是一种不自然的思考方式,需要对一个不动的物体保持长时间不间断的注意力。以艾略特在诗作〈四首四重奏〉里的描述,读者需将自己置身于一个「旋转世界的不动点」。他们必须训练大脑,让它忽略四周一切事物,抗拒在感官信号之间转移注意力的本能。为了不要分心,他们必须打造或强化抑止本能的神经连结,「由上而下」对他们的注意力加强控制。照伦敦国王学院的心理研究员佛汉·贝尔的说法,「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件工作,少有间断」代表了「我们心理发展历史上的奇特变异。」
作者在此处提出读书是一种不自然的思考方式,对应的是人类历程中自然的「分心状态」。人类的演化需要时刻关注周边事物,为了获取资源或察觉危险,以做出有利于生存的决定。阅读是一种反其道而行的行为,它要求人类关注一个不动的事物,并将周边环境抛诸脑后。作者在此提到这点是有用意的,往后他将会再次提起,并说明,人类似乎再次回到了自然状态,那种不断抓取视觉中幻美泡泡的冲动,充斥在虚构的网路空间里。
在这样的网路空间中,当我们将熟悉的文化形态办到线上,绝非只是将一模一样的内容从一个框搬到另一个框。在这个过程中,内容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传统媒体(甚至包括电子传统媒体)在转换到线上发行时,正经历再塑造、再定位的过程。网路吸收一项媒体时,会依照网路自身的形象重新创造该媒体。它不仅让媒体的物体型态消失,还会在其内容里置入超连结,把内容切割成可搜寻的区块,更会用它吸收进来的其他媒体内容来包围住新的内容。内容的形式改变后,也会改变我们使用、体验,甚至理解内容的方式。
以FB为例,大报放的小说愈来愈短,每一篇都配有一张绚丽的图,来自年轻绘师。小说开头往往需要马上抓住读者注意,谁死了,谁发生了什么。读者往往在读了两三段后又跳到结尾,并很快打开留言栏看其他人说了什么,如果有吸引人的评论则又回头跳到小说中间,期间略过数千字,但似乎还能读下去。很难想像在FB上能读到《荨麻》这样的小说,开头三段的模糊与沈默会被读者略过,别说厌恶,甚至连一点印象都留不下来。
正如经济学家泰勒·科文所说:「资讯容易取得时,我们通常会偏好简短、有甜头、轻薄的资讯。」
对于电子阅读器的连线功能,作者也提出了批判。
当纸本书籍转移到有网路连线功能的电子装置时,它就会变成很像网站的东西。它的文字会身处在网路连线电脑的种种扰人事物中,它的连结和其他数位增强功能让读者到处漂流。它丧失了已故美国作家厄普代克所谓的「边棱」,消失在网路的无边汪洋中。纸本书籍的直线特征变得支离破碎,同时这种特征在读者心里唤起的宁静感也被打破了。
我在10年前接触Kindle,后来也用过Readmoo,但近年来如非必要,像是绝版书或上班摸鱼,实则几乎不再使用电子阅读器。实际上,当我在使用电子阅读器时,也极少会使用连结或翻译解说,这些功能的确会削减读者的注意力。同时,电子阅读这种与萤幕互动的行为,或许在神经连结上与使用手机的行为过于相近,而电子阅读所带有的时间、背光、阅读进度、阅读字数等等数字化的行为,也改变了阅读本身的私人性质,强化了社交属性。如同Readmoo会办阅读马拉松的活动,或许多读者沉迷于阅读的数字游戏,不断过关斩将升级,以得到徽章或惊人的时数字数,那些将文字捏碎后得出的无意义数字,仿佛变成了主菜。我们吃饱了,但不知道自己吃了什么。远在电子阅读器兴盛以前,豆瓣就已透过类似的方式,将阅读量化,读了什么书不重要,得到什么精神感悟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读了多少书,读得又有多快。这些数字最终都脱离了书本独自存在,仿佛一缕寄生幽灵攫取了主人的肉体,发出震耳欲聋却没有意义的尖叫。比起一辈子只钻研几本书的学者,人们似乎更渴望看到杂学家,而且愈来愈不在意杂学家说了什么,只要定时发出声音就好。人们在杂学家身上看到了自己的无知,同时又仰慕杂学家的数字是如此醒目。
书本为了因应无声阅读而改变形式,其重大影响之一便是促成私人写作。作家可以假定一个知识与心灵层面能与之交流的用心读者「终有一天会到来,并且会感谢他们」,于是迅速跳脱社交语言的巢臼,探索多元面貌的文本形式,其中许多也只能以书页的形式存在。如前文所述,私人作家享有前所未有的自由,多方的实验手法增加了字汇规模、延展了语法极限,也使得语言整体来说变得更有弹性、更有表达力。今日阅读的脉络又从私人的书页转变为公众的萤幕,作家也会再次改变写法以因应趋势。他们会逐渐调整作品的风格,以符合散文作家克雷恩所谓「群众感」的周遭环境;在这种环境下大家阅读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有参与感」,而非个人启发或娱乐。当社交因素凌驾于文学因素之上时,作家似乎一定会扬弃写作技巧与实验性,转而使用乏味但容易被人接受的写作风格。写作未来仅存纪录七嘴八舌言谈之用。
谈完了阅读,作者将火力对准作家。一个人人能写作的时代,并不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反倒成了一个鹦鹉学舌的时代。作家变得绑手绑脚,他们更加取悦于读者,更难以挑战。因为挑战意味着被隔绝在网路空间之外,而如今网路空间就意味着几乎所有的空间。所有人都希望从作者身上看到自我,而一旦看到怪异的不能理解之物,则赶紧用手指滑开,如同捏死一只碍眼的苍蝇。作家被迫说陈腔滥调,也或许,很多人是愿意说这样的陈腔滥调,因为他们渴求读者。在这个流量为王的世界上,作者与读者都穿着西装抓着对方的阴茎抽动,怕弄痛对方的同时,假装彬彬有礼。
我们在使用电脑时,不论是有意或是无意的抉择,都与书籍赋予我们的知识传统相违,不再要求全神贯注、集中精神。我们已经把赌注押在杂耍人的身上了。
网路抓住我们的注意力,却又将其打散。我们聚精会神在媒体本身(即不停闪烁的萤幕)上面,但是这个媒体带来快速连发的讯息和感官刺激,又使我们分心。
网路各种感官刺激的喧嚣让有意识和潜意识思考都短路,使我们的大脑无法进行深入或有创造性的思考。我们的大脑变成只能简单处理讯号的工具,把资讯匆匆带进有意识思考里再匆匆带出。
网路拼命抓住我们的注意力,以分割的视窗打碎它们,在不断重组与分散的过程中,时间终于被我们变得一文不值。在时钟将时间分割成暴力的刻度之后,网路再次剥离了时间的意义。我们与时间彻底变得水火不容,于是,时间只好整个吞下我们。一根骨头也不剩。
我们上线时没有在做的事,也会对神经系统造成影响。一起发动的神经元会连结在一起;同理,没有一起发动的神经元就不会连结在一起。如果我们浏览网页的时间多过阅读书籍的时间、互相传递简短文字讯息的时间多过写出完整章句的时间、在网路超连结里跳来跳去的时间多过宁静沉思的时间,这些旧有的心智功能和思想追求就会变得脆弱,并且开始瓦解。大脑会回收无用的神经元和突触,用在更迫切的工作上。我们会得到新的技能和观点,但会丧失旧的。
时时刻刻流进我们工作记忆的资讯称为「认知负荷」。当这个负荷超出头脑储存和处理资讯的能力时(换句话说,就像是水满出顶针来),我们就没办法保存这些资讯,或是让它与长期记忆里的资讯产生连结,亦即我们无法把新的资讯转译为基模。我们的学习能力大减,对事物的理解也无法深入。由于工作记忆也跟我们保持注意力的能力相关,一如柯林柏格所述,「我们必须记得自己专注在什么上面」;过高的认知负荷会加强我们感受到的纷扰。大脑负载过量时,我们便觉得「让人分心的事物更会让人分心」。 (有些研究认为注意力缺失症与工作记忆过载有关。)实验证实我们在到达工作记忆上限时,更难分辨要紧与不要紧的资讯,容易把真正的讯号和杂音搞混。我们于是成为无脑的资料使用者。
这显示了知识的一个悖论,愈多并非愈好。这其实很好理解,循序渐进地吞食总是更有益于健康。三头六臂并非人类被设计成的模样,而只是一种神话。当我们沉浸在杂乱的讯息海时,我们能抓住的东西远远少于在溪流嬉戏的孩童。因为他们总是专注又惊奇地抓取世界饱含深意的微小启示,而我们却在大海里活活淹死。
从我们如何在网路上阅读就可以看出来。根据实验,我们实际上是以F型进行扫读。
尼尔森为他的客户总结这些研究结果如下:「F代表的是『快速(fast)』。网站的使用者就是用这种方式来阅读你的宝贵内容。几秒钟的时间内,他们的眼睛会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扫过网站上面的文字,阅读的模式跟以前在学校里学习到的方式大大不同。」为了佐证他的眼睛追踪研究,尼尔森还分析了一个德国研究团队建立的庞大网路使用习惯资料库。这个团队监视了二十五个人的电脑,平均每人长达约一百天,并且纪录他们在大约五万个网页上的停留时间。抽丝剥茧之后,尼尔森发现网页上的文字愈多,造访者停留的时间也会增加,但只有增加一点点。一般来说,网页每增加一百个字,使用者只会在这个页面上多停留四点四秒。由于阅读能力最强的人也只能在四点四秒里阅读大约十八个字,尼尔森告诉客户:「当你在网页上放上文字时,你可以假设你的客户只会阅读百分之十八而已」;而且,他还警告说这几乎一定是高估了。研究里的受试者不太可能把时间都花在阅读上;他们八成还同时在看图片、影片、广告等等其他内容。 ⋯⋯这也证实尼尔森于一九九七年首次研究线上阅读后所言。当时他提出问题:「网路使用者在网路上如何阅读?」只得到一个简短的答案:「他们根本不读。」
那么,网路真的使我们变笨了吗?这要看你怎么看,如同作者所说,
我们广泛使用网路和其他萤幕为主的科技时,使得「视觉——空间能力得到普遍且高度的发展。」举例来说,我们在大脑里旋转物体的能力就比以前更强。但在得到「视觉——空间智能的新优点」同时,我们「深度处理」的能力也减弱了,而这种能力正是「有意识地吸收知识、归纳分析、批判思考、想像和反思」所必须的。换句话说,网路的确让我们变聪明了,但必须是以网路对智能的定义来看。如果我们用更广义的传统定义来看智能,亦即用思想深度而非速度来判断,我们会得到不一样的结论,而且是相当负面的结论。
这种深度思考能力的丧失,其最大的标志之一是沉思的丧失。沉思被认为没有效率,一个聪明的人最显著的指标是速度。这也如同上面提到的阅读行为数字化。虽则我们总说又快又好,但快总是比好更重要。在网路上写作时总被告知,网路是一个这样的环境,你需要把文章缩短,缩短,再缩短。速度总是第一考量,然后才是好。我们很难坚持长文的价值,我们甚至排斥深度思考的价值。一篇文章写得太难太长,总归被认为是不够好的。即便沉思与冥想被这个时代的人拿来使用,其意义也已经改变。休息、沉思与冥想,是为了高效率存在,为了之后的工作而存在。我们休息、沉思或冥想是为了更好地做到什么,这一类看法,其实也就是一种功利的看法。我们不再认为深度思考本身有意义,如果有,也必定是为其他意义服务。
Google和其他网路公司强调高效率资讯交流是知识成长的关键,这种想法也不是最近才出现的:至少从工业革命开始时,这就已经是人类思想史上的常见看法。这种看法和美国超验主义思想家,以及稍早的英国浪漫主义思想家所主张的大大不同:他们认为真正的启发必须来自沉思与自省。套用马克斯的说法,「机器」与「花园」之间更广大的冲突(亦即「工业的理想」与「田园的理想」,反映在这两种观点之间的张力里;而机器与花园之间的角力,也在形塑现代社会里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
依霍桑之见,工业理想下的高效率会对田园理想的宁静沉思造成致命的伤害。这并不是说让资讯可以快速发掘、取得是一件坏事。若要发展出健全的大脑,必须同时具备找到广泛资讯并将之快速分析的能力,以及天马行空冥想的本事;换句话说,必须有高效率搜集资料的时间,也需要有低效率反思、操作机器、在花园里闲坐的时间。我们必须有办法在Google的「数字世界」里正常运作,但还是需要有时退到沉睡谷里。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失去了在这两种脑部状态找到平衡的能力;就脑内活动而言,我们一直处在恒动的状态。
资讯处理的科技愈是进步,寻找和过滤资料的工具愈是精准,相关资讯的洪流只会更势不可挡,我们也会看到愈来愈多自己感兴趣的东西。资讯过载已经成为常驻的病症,而且愈治疗愈严重。我们只有一种应对的方式,就是增加扫视略读的分量,并且更加仰赖这些反应奇快的机器,即使这些问题当初就是这些机器造成的。李维指出,今天「我们可以取得的资讯远比以前还多,但可以应用这些资讯的时间变少了,更别说是稍经思考后才拿来使用。」
这种网路时代的思考方式,和阅读时代的思考方式,也是一种从众和个人的差异。在阅读时代,
由于每个人可以自由规划阅读方向和学习过程,个人记忆渐渐不再是受到外在社会定义的结构体,反而成为架构个人独特观点和个性的基础。受到书籍的启发,世人开始视自己为个人记忆的作者:莎士比亚便托哈姆雷特之口,称他的记忆为「我脑里的书卷」。
因为阅读是如此孤独的一件事,也就造就了在长时间的阅读冒险中,我们必须自我消化,为知识找到个人诠释,才能放进脑袋中。记忆是带着扭曲与变形的,更准确的说法是,一样事物未经过扭曲与变形,不带上个人印记与误解,是无法进入记忆。这需要长时间的孤独,而阅读时代提供了这种孤独。如今我们的阅读成了一种社群行为,跟风行为,数字比武行为,使阅读贬值。
更有什者,我们选择将记忆外包给机器。我们认为记忆是一种物,是可存放在他处存取的。这是一种非常错误的看法,如若知识不在脑中形成有机的架构,它就无法被交叉运用与创新融合。
那些高声赞扬记忆「外包」给网际网路的人,被一个错误的譬喻误导了。他们忽视了生理记忆的有机生长特质。人类真正的记忆之所以这么丰富有个性(当然也让它既神秘又脆弱),就是因为它的偶发特质。人类记忆存在于时间的流逝之中,跟着身体一起改变。事实上,光是我们把回忆唤起来这个动作,就会重启整个固化的过程,包括促成新蛋白质的生成,以形成新的突触末端。我们把一个外显的长期记忆召回工作记忆里面时,它又变回短期记忆了;这个记忆再次固化时,它会得到新的连结、新的脉络。正如李窦所说:「负责回忆的大脑和当初形成记忆的大脑不同。如果现在的大脑要了解以前的记忆,它必须更新这项记忆。」生理记忆永远处在更新的状态中。相较之下,电脑会把记忆分成一个个固定片段,不论你把这些片段在磁碟之间移动多少次,它们仍然会保持原型不变动。
当学校在一九七零年代开始允许学生使用计算机时,许多家长反对这个作法。他们担心小孩子依赖这些机器后,会降低对数学概念的掌握能力。后续的研究证实这些大多是白担心了。因为不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在基本运算上,许多学生反而对于习题背后的原理有更深入的认知。计算机的事情现今常常被拿来当成正面的证据,认为仰赖线上资料库并无害处,甚至是一种解放。根据这个说法,网路让我们摆脱记住事情的工作,可以把更多时间投入创意的思考上。但这样类推是有问题的。口袋型计算机减轻了我们工作记忆的负担,让这个重要的短期储存区可以用在更抽象的思路上面。从数学学生的经验来看,计算机让大脑更容易将工作记忆的想法转移到长期记忆里,以概念基模的方式进行编码,藉由这种重要的方式建构脑中的知识。网路造成的效应则相当不一样:它反而让工作记忆的负担更重,不只会从更高阶的思考程序里抢夺资源,还会阻挠长期记忆的固化,以及基模的发展。计算机的功能强大但效用单纯,最后成为辅助记忆的工具;网际网路则是促进健忘的科技。
计算机的例子最近也被拿来为ChatGPT辩护,我想作者的此段论述是极佳的反驳。计算机节省了学生低阶的运算负荷,是为了满足高阶的抽象思考。这些抽象思考才是考试要考的东西,也是如今我们认为真正重要的知识,而非运算的准确度与速度。然而如果我们将抽象思考的任务让渡给网路,只会造成知识成了一块块独立的铁块,它们再也无法在脑袋中融合,带上个人印记。这些知识已经死了。
我们上线时接收到大量的讯息,彼此争相吸引我们的注意力;这些讯息不但使得我们的工作记忆过载,还会让我们的额叶没办法专心在任何一件事情上。记忆固化的过程甚至根本没办法开始。再者,正因为神经通道具有可塑性,我们愈常使用网路,就愈是训练头脑保持分心状态,可以用高效率快速处理资料,但是无法维持注意力。这说明了为什么很多人即使离开电脑也很难专心。我们的大脑变得擅长遗忘,不擅长记忆。我们愈来愈依赖储存在网路上的资料,这可能正好是一个自我延续、自我扩大的循环:使用网路后,我们更难将资讯储存在生理记忆中,只好更加依赖容量无穷又容易搜寻的网路人工记忆,即便这样子做会让我们的思想愈来愈肤浅。
我们接受科技带来的力量,付出的代价就是被孤离,而智能科技造成的代价可能尤甚。我们最贴身、最人性的天生能力就是理解、认知、记忆与感受的能力,但心智层面的工具在强化这些能力之时,同时又会使它们麻木。机械时钟虽然带来无数的好处,却让我们丧失对时间流动的自然感觉。孟福说明现代时钟如何「创造出一个信念,相信一个由数学测得的序列组成的独立世界」时,他也强调时钟造成的后果,是「切断时间与人类事件的关系。」怀森鲍姆再拿孟福的看法来扩展,认为计时机器促成的世界观「一直是旧时世界观的残缺版,因为它拒绝了旧有现实立基其上(甚至可以说用以建构)的直观经验。」我们不再顺从自身的感官来决定何时饮食、工作、睡觉、起床,反而改遵照时钟。我们变得更加科学了,但也变得更加机械化了。
伊凡斯在二零零八年的《科学》期刊上说明这个违反常理的发现时,提到自动化的资讯过滤工具(如搜寻引擎)常常会放大原本已属热门的事物,快速建立起资讯重要与否的共识,并且不断强调这个共识。再者,超连结容易引领使用者点击下去,使得上线的研究人员「略过许多有些微关系的文章;使用纸本资料的研究人员」在翻阅期刊或书籍时却经常会扫读这类文章。伊凡斯认为,学者愈是能够快速找到「当道的看法」,就愈有可能「追随它,使得愈来愈多的引文引述愈来愈少的文献。」虽然在图书馆做研究的古老方法远比搜寻网路来得没效率,这种方法却很有可能让学者的视野变广:「浏览和使用印刷资料会带领研究者走过不相关的文献,有可能促成更广泛的比较,引导研究者进入更早的时间。」最容易的方法不一定是最好的方法,但我们的电脑和搜寻引擎却不断怂恿我们采用最容易的方法。
我们变得肤浅,也更容易分心。我们在分辨讯息的速度和精准度上更胜一筹,却不知道拿这些资料怎么办,只好假装它们不再重要,实则是人类不再重要。我们无知,但我们甚至无法看出自己的无知,自作聪明倒是很在行。我们遗忘,遗忘了自己的遗忘。网路承诺了什么?网路承诺了更大更宽广的世界,但如果这个世界注定变得更同质乏味,一群白痴被另一群白痴追捧,这样的世界,真的是你我想看到的吗?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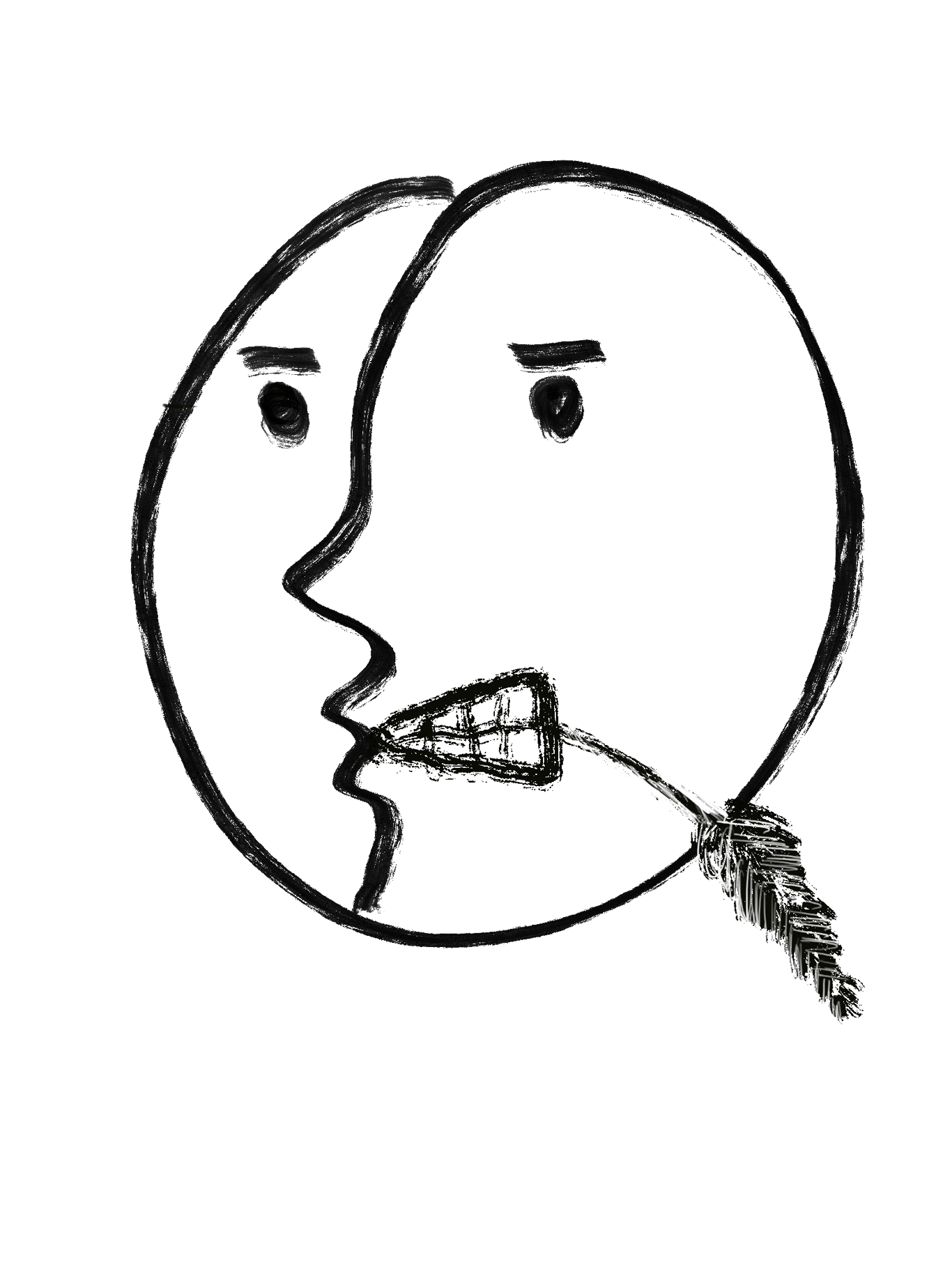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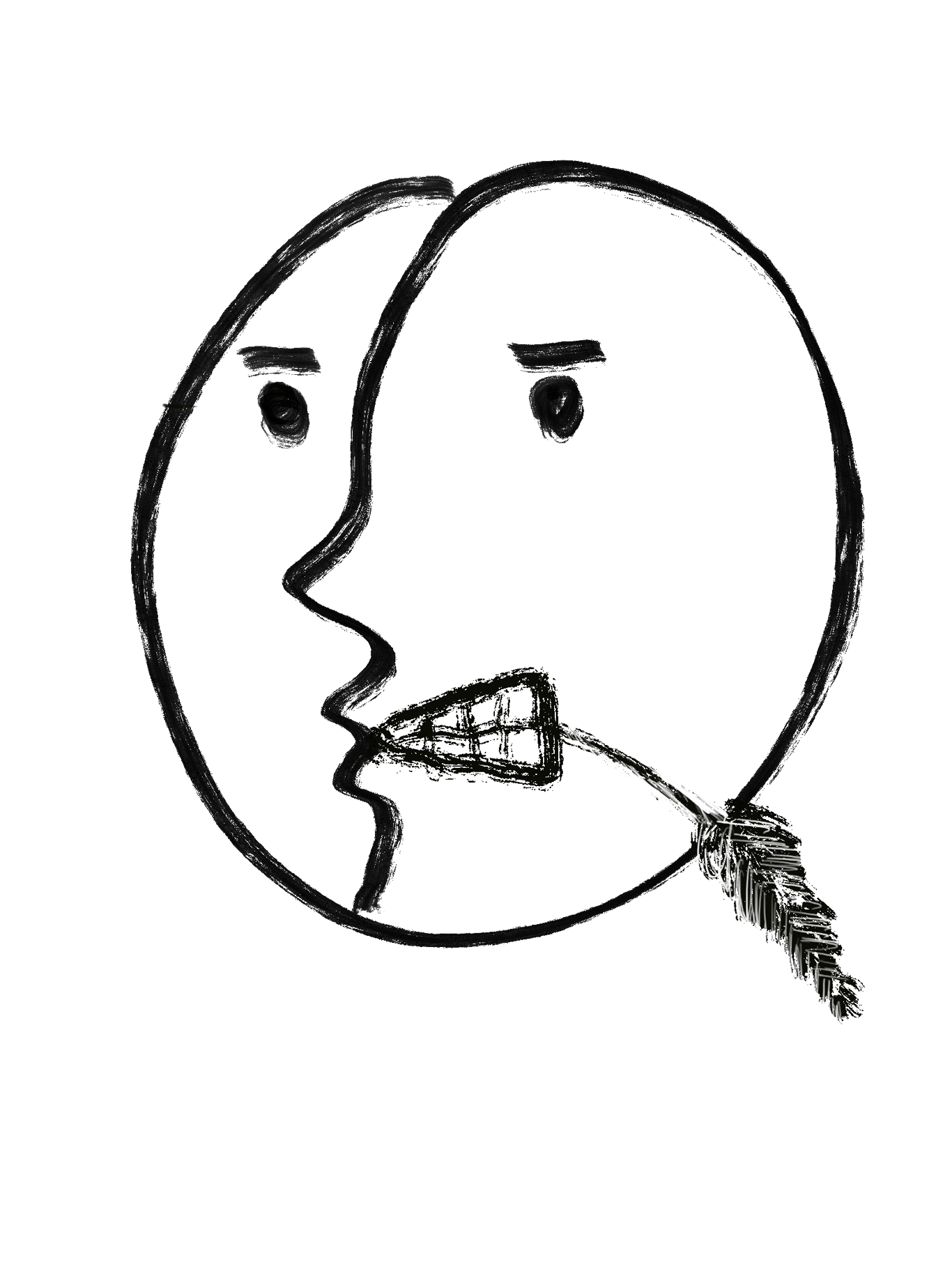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