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清明,和无数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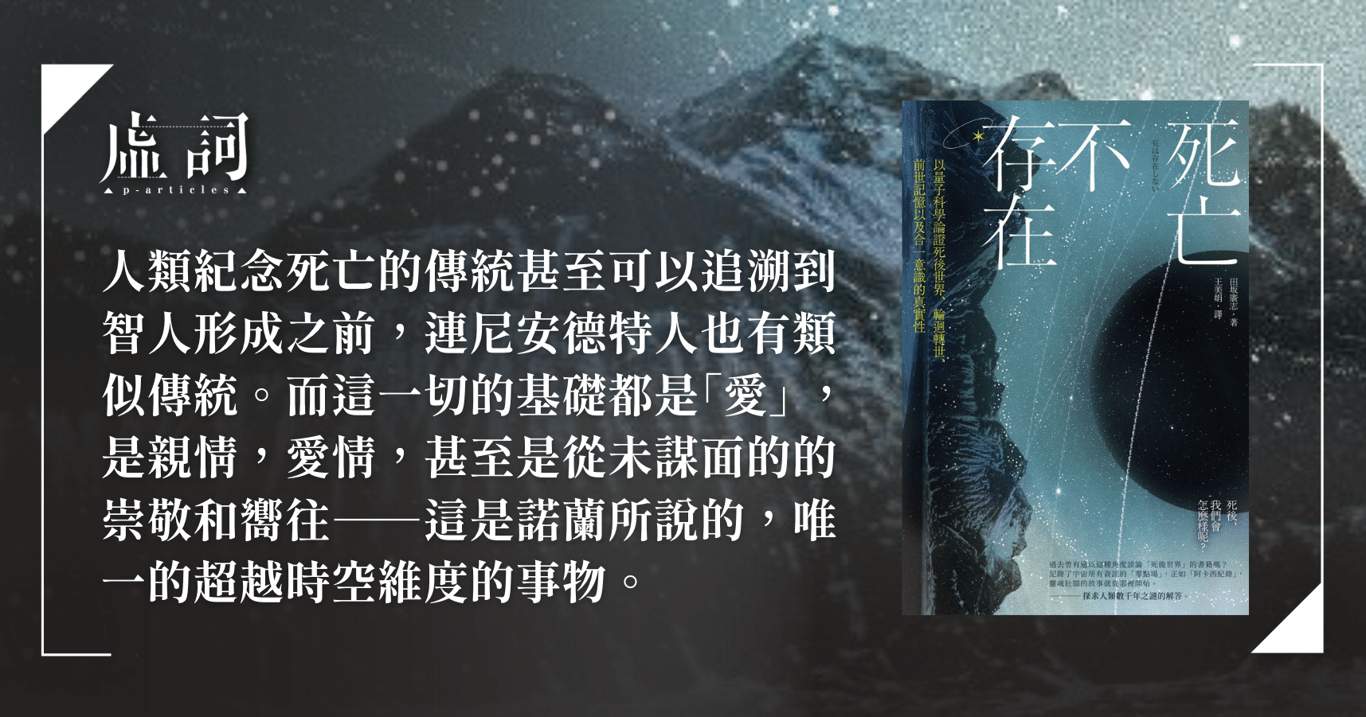
文|王峥
清明节并不是新加坡的法定节日,但这并不影响街上的悼念活动,像某种可控的火灾一般,点亮了以秩序和整洁著称的狮城,在海雾中酝酿着一股不知飘向何处的忧愁。在每个排楼组屋的街口,政府都设有一个巨大铁桶,不知是锈迹还是油漆,在夜色中闪着暗暗的红色。从晚饭开始,这些本用来收纳垃圾的容器,如今被赋予更神圣的功能:等待那些在熟食中心,办公楼,和地铁站陆续走出的人群,以新的身份重聚为铁桶前的悼念者,开始燃烧生者世界的两大特产——冥府的新加坡币以及新加坡护照。不知在那里,这些是否还是硬通货呢?似乎在亚洲文化中,悼念是我们谈论死亡的唯一方式。我们无法真正了解死者的想法,所以只能猜测;而正因为猜测,悼念更像是我们对于自身的慰藉。在每年的清明节,新加坡的武吉布朗,世界上最大的华人公墓,一群致力于保护其不被政府拆除的现代「守墓人」都会邀请全真派道士为一群无名的死者举办一场集体的悼念。这位名为皮特的道士说:「我们就是他们;我们太关注未来,有时忘了过去,所以清明节是一个礼物」。
在田坂広志的畅销书《死亡不存在(死は存在しない)》中,这位曾经的医师从量子力学的角度解释了「死亡」并不是终点,而是一个通往下一个阶段的过渡。但这本书并不能完全消解人类对于死亡,首先是他人,然后是自我死亡的一切情感和历史。科学和艺术仿佛都是为了解释同一件事情:如果死亡是终点,和更多看起来永恒的事物相比,我们短暂的生命意义在何?当然如果按照田坂的解释,死后世界、轮回转世、前世记忆以及合一意识均存在,那么悼念将不仅仅是一种遗憾,而带着某种庆祝的心情—祝福死者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足以将让「欲断魂」的悲哀转化成一种「踏歌声」的祝愿,即所谓「喜丧」。人类纪念死亡的传统甚至可以追溯到智人形成之前,连尼安德特人也有类似传统。而这一切的基础都是「爱」,是亲情,爱情,甚至是从未谋面的的崇敬和向往——这是诺兰所说的,唯一的超越时空维度的事物。清明节,作为一种文化仪式,将以物质和非物质的形式,不断提醒着这种超维度的力量,如何将一个在白日里不苟言笑的城市,在夜晚变成一个情断丝连的剧场。但当我走近他们,却也无法再保持一个外来者的矜持。我想起了童年时的清明节,外祖父曾在一个陌生的坟头一边扫墓,一边对着我说:「有一天你也会来这么看我」。
于是我久违地和外祖母打去电话,发现家里长辈都回去了,这是春节后再一次难得的重聚。隔着一整个南海,我也只能以电子扫墓的形式参与其中。现在扫墓甚至可以扫码了,但是相比于物理运动,也许电磁波可以更好的地传递感情,如同田坂书中所述。总之是给我外祖父的一点悼念。由于童年时父母忙于工作,我和外祖父的时间远大于和父母的时间。作为书画家,外祖父总是精神矍铄,对于一切含有文字和图像的事物都乐此不疲—我常常是他的观众和读者。在病榻上仍坚持写作,也许代表了某种东亚文人的理想形象;但他从未对我多言他因政治动乱而伤残的左腿,直至离世。之前因为他罹患的胃癌甚至想过要学习医学,但实在缺乏这方面的天赋,在美国大学时就已放弃。但后来在艺术中仿佛又找回童年时候那段和外祖父在桂林附近四处临摹和旅行的日子。他有些不稳地骑着自行车,仿佛又出现在悼念的人群中,如海市蜃楼。人生是多么奇妙的轮回,上周向香港一家英文杂志解释七年前写的第一首英文诗「瑶族葬礼(An Iu-Mien Funeral)」,写的便是外祖父作为民国时代的左派知识分子,却选择一个极具民族和宗教意涵的葬礼形式。当时我无法理解,但从新加坡回想美国和中国的一切,突然觉得可以明白,人面对死亡时的感受。
外祖父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是:「让他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无论怎样总是可以活下去的」。想到这里时,新加坡已入深夜。满街的烟火在铁桶中次第熄灭,只剩下了一簇火星,和无数团雾气,还在树梢游荡着。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