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舞伎町的新年:和風俗店姊姊們的年夜飯
以下文章來自BIE別的,作者BIE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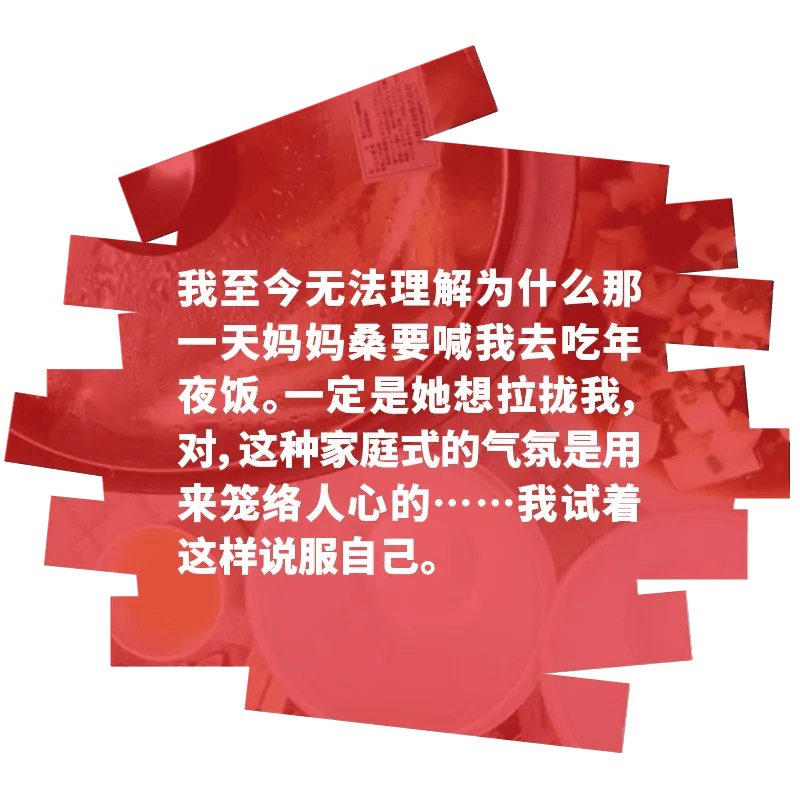
這是「東京按摩女日記」系列連載的第二篇,前情請看:
東京按摩女日記:成為按摩女第一步是學習功夫
東京按摩女日記:我去華人的「大保健店」面試了
22 年1 月31 日,中國人的除夕。這一天,我是在自己打工的地方── 新宿的大保健按摩店度過的。
日本人不過除夕,他們的新年是1 月1 日。所以很顯然,除夕這天我們店並不會放假。下午五點,我發了一條微博“提前祝大家新年快樂”,就背上包出了門。
01 明天的我是11 號
明天開始我就會正式上班,今天正在抓緊最後的時間練習。 「女王」 7 號姊姊幫我拍了照片,是要發在店家主頁上的。照片拍的很奇怪,醜醜的,我拿著美圖軟體怎麼p 也p 不好,最後作罷。
真奇怪啊,原本還以為在這裡工作的人大家都該很擅長拍照才是。結果也並非如此,主頁上大家的照片都很奇怪,完全沒有現實裡的本人好看。
現在想來,這種想法也不過是種刻板印象。這裡的按摩女郎,年齡從20-50 歲都有,大家都是普通人。
我的號碼被設定為了「11 號」 ,從此以後,大家都會叫我「 jyu ui chi bann(11號的日文讀音)」。在這家店裡,我們所有人都沒有名字,也沒有花名假名,只以數字相稱。
後來我問媽媽桑,11 號是什麼意思。店裡有5 號,7號,沒有10 號,看著也不是按照數字順序排的。媽媽桑告訴我,數字是按照「印象」 取的,每個數字都有店裡約定俗成的含義。例如1 號會是年長的人,2 號是經驗豐富的人。
“ 11 號是年輕,高個子的人。”她這樣告訴我, “因為11 數字小,看起來又細細高高的。”
我想了下,感覺並非全無道理。從明天起,我是11 號。
02 風俗按摩店裡的男性員工
店裡除了我們這些按摩女孩和女性媽媽桑以外,還有兩位男性員工。
其中一人是日本人,大家叫他“原先生”,是專門被雇來和日本客人的交流的。
店裡的女孩都不太會說日語,除了媽媽桑以外,剩下的人儘管都長年在日本生活,也只能說幾句最簡單的日語。她們一直住在華人圈內,日本人打來的電話都不會接(後來有時是我去接電話),一旦和客人發生了複雜的口角便容易說不清楚,這時候就輪到這位日本人出馬負責協調。
原先生自稱以前是建築師,但歌舞伎町的話不能全信。我與原先生沒有那麼熟悉,但因為能說日語的人不多,我也是店內平時和他說話最多的人了。他是那種在歌舞伎町的從業人員圈子裡常見的,不好也不壞的人。
我在店內扮演的「人設」 是單純的傻白甜女大學生,從年齡到學校都是謊報,但原先生曾經偷偷把我喊去,用日語小聲對我提醒道:「你也不要太相信這裡的人,多留個心眼。
我訕訪笑著,明明自己在說謊,但原先生卻真的擔心我。我有些愧疚地笑著對他說「謝謝您,我知道了」。
另一個就是17 號。是的,按摩店的17 號員工是個男生。
從口音聽來,他應該是東北人。我也不知道店裡為什麼有男性員工,他平常也基本上不在店內,聽說是在其他系列店。不過,曾經有兩個日本女生錯把我們店當成普通的按摩店誤入時,媽媽桑就讓她們在外面的按摩椅躺下(而我們都是在裡面的隔間接客),然後打電話把17 號喊來幫她們按摩了。
17 號跟我們說話不多,按摩手藝很好。除夕那天,他不知為何來店裡露了面,手上提著些大包小包,好像是7 號和媽媽桑喊他去買的東西。
他順便圍觀了一會兒我和越南妹妹15 號學按摩的樣子。
「這裡手法不對。」他說著要我伸手,手指按住筋脈中間往上一撥,我「嗷」 地一聲發出慘叫。
“這樣才對。”
17 號面無表情地說。平常可以用小腿練習撥筋手法,因為小腿大多沒有脂肪,很好找位置── 這樣的練習技巧,也是他教我的。
我點頭學著,不時偷偷看他和15 號的對話。 15 號就是那個靦腆害羞,但笑起來很可愛的越南女孩。她沒有固定居所,就住在店裡,在自己的隔間裡裝了小鏡子,還放了好幾個大布娃娃。
雖然15 號原本就容易露出害羞的笑容,但17 號來了以後,她臉上的笑就沒有停下來過。我練習的時候,他們兩個人就小聲地,用中文夾著日文有說有笑地交談著。我看到15 號的臉紅彤彤的,看著17 號的眼睛亮晶晶,笑得也比平常更多了,好可愛。
03 “今天過年!”
我和15 號、17 號練習了一會兒,到晚上八、九點的時候,媽媽桑突然拉開簾子,對我說:
「別做了,休息吧!今天過年,大家一起吃年夜飯,你也來吧!”
她笑盈盈的。
「年夜飯?」我茫然地說。 15 和17 號卻對此早有準備的模樣,立刻收拾了起來。媽媽桑挽著我,跟我說店裡都是一起過年的,7 號姊姊在附近買了房子,叫大家一起去她家吃飯。
我有點呆呆地應著。我還是第一次和別人一起吃年夜飯,也是第一次在日本吃年夜飯。我原本以為,今年我也不會過除夕了。店裡的其他姊姊都已經做好了分工,有人提著中華物產店的大塑膠袋,裡面裝著食材,有人從冰箱裡清點庫存,有人算著還有沒有忘了買的東西。我還看到了一位姊姊的日本人丈夫,他是來開車送我們的。
一群人各自分工忙活起來,關了店,掛上「休息中」 的牌子,然後浩浩蕩蕩出了門。到此為止,我都完全沒有過年的真實感。約有八、九個人,我們擠上麵包車,一排坐三個人擠成一堆。 7 號姊姊的房子就在新宿車站附近的公寓。她們說晚上要吃火鍋,媽媽桑想起火鍋底料還沒買,17 號立刻說他去買,15 號也跟著他一起去了。
路上還接了個別的女孩子。她也是留學生,現在已經不在這家店做了,好像在自己單幹。簡單來說就是當爸爸活。但是媽媽桑還是給她發了訊息,她說要來,就在歌舞伎町的堂吉訶德門口接上了她。
接到人的時候,她看起來喝過酒,整個人的狀態很嗨,上來第一句話就是“我在堂吉訶德買了酒!有沒有人要喝!”
媽媽桑道:“我不喝!你小姑娘在外面也少喝點!”
「有什麼嘛!」小女孩叫嚷著,她很年輕,看起來比我年紀還小,穿著時髦,就和歌舞伎町的日本女孩子一樣。我笑起來,舉手說我想喝,她立刻從包裡掏出一個小瓶子塞給甚至彼此不知道名字的我, “這個是曲奇味的!很好喝!”

「怎麼喝?」 我問。
她說:“你就直接喝。”
手上的小酒瓶不到半個巴掌大,我扭開瓶蓋,仰頭一口喝完了,也確實只有一口的量。度數不低,但是甜甜的,奶油曲奇餅乾的味道。
「好好喝!謝謝你。」 我對她說。她低頭「嗯」 了一聲,手中忙著擺弄手機,我瞥到是line 的對話頁面,便回過頭沒有再看。
我還不知道她的名字,她也不知道我的。
04 “家”
店裡的所有人都不知道彼此的名字。
這是一件很神奇的事,但是歌舞伎町就是這樣。有十幾年友誼的陪酒女夥伴會一起旅遊,甚至生了孩子後互相幫忙照顧小孩,但是都不知道彼此的名字,只會喊源氏名。
我們這裡更加離譜一些。
到了7 號姊姊的“家”,才發現這和我以為的“家” 不太一樣。房間裡散亂一看就是來自於許多不同的人的物品:有一個很大的冰箱,客廳裡放著奇怪的中式椅子,牆上掛著大幅的刺繡畫,角落裡放著瑜珈墊和瑜珈球,還有小孩子的玩具,但是房間裡並沒有小孩子的身影。深處可以看到有一個類似會議室的書房,架子上堆著滿滿的雜物。
我看著客廳和店內同款的椅子感到一陣困惑,欲言又止。
而店裡的其他女孩們卻熟絡得就好像這是自己家一樣,另一個來自越南的姐姐很熟練地打開冰箱拿飲料出來喝,5 號則是自然地走到廚房裡開始分揀帶來的食材。
我問媽媽桑和5 號“這到底是什麼情況”,她們和我解釋說,這裡不是7 號和自己的丈夫孩子所住的那個家,更像是工作間隙去休息的地方,但是大家常來這裡玩和休息。
屋子裡的東西七七八八,冰箱裡的食物是不同的人塞的;奇怪的中式椅子和刺繡畫是店裡之前換家具淘汰下來的,就乾脆搬來用了;瑜珈墊和瑜珈球是兩個越南女孩的,她們也常來這裡住;小孩的玩具,來自於5 號和7 號自己的小孩,孩子還小的時候,她們經常把孩子帶到這裡,兩個人誰閒下來就負責照看。
我覺得好奇妙,好像某種原始的女性部落,或是什麼互助公社。就我而言很難想像現代社會的人會這樣緊密地連結著,像這樣互相介入對方的生活。
普通的職場關係裡會有這樣親密的同事關係嗎?雖然我沒有上過班,但想來大概也不是這樣的。普通的工作,應該不會有大家一起分享一個房間,照顧彼此小孩的狀況吧。
這種情誼好奇妙,但匿名卻親密,這種形式的友誼或許只會存在於紅燈區的人們之間。
7 號總是買很多好吃的分給大家吃,她還把自己賺錢買的房子免費給其他女孩子用。那兩個越南的女孩沒有自己的居所,所以也常來這邊休息睡覺,我看到冰箱裡塞著她們倆的零食飲料。
在外人看到的歌舞伎町或是風俗題材作品裡,總會把所有女人刻畫成彼此競爭,算計加害的關係。可事實並不是這樣。或許正是因為在這樣的環境裡,才會誕生這種情誼?我不知道。
我坐在沙發上,手腳局促得都不知道該放在哪裡。此時,還有以後的許多時刻,我都會突然感到一陣愧疚,那是一種自愧不如帶來的窘迫感。我其實不太理解人要如何……互相幫助,如何接受來自他人的照顧,並且自己也去照顧他人。
這個業界充滿謊言,歌舞伎町一整晚能賣出的金錢總額等同於一夜間謊言的數量。我總是留著心眼,我告訴自己不可以相信這裡的任何人:我不會相信對我很溫柔的媽媽桑,我也不會對店裡的人說一句有關自己的真話。這是必要的,即使那會讓我永遠無法取得如她們一般真誠的聯繫,但再來一次,可以重新選擇,我還是會對所有人說謊。
可是我至今無法理解為什麼那一天媽媽桑要喊我去吃年夜飯。我絕對不會承認那原因中哪怕只有一小部分,是她出於好心,只想喊我吃頓飯。一定是她想拉攏我,對,這種家庭式的氣氛是用來籠絡人心的……我試著這樣說服自己。
在我說服自己的時候,就表示我心裡並不相信這個答案了。
05 年夜飯
現在能做的,只有幫忙煮飯了。廚藝算是我身上勉強還稱得上是長處的一點。
這時候東北男孩和一起去買食材的越南女孩也回來了。我看到裡面有火鍋底料,還是我平常自己愛用的那款柚子雞湯口味。
在做飯的是東北男孩,越南女孩去和另一個越南女孩貼在一起,坐在沙發上看影片了。我繞到廚房裡面總想幫忙,但好像根本插不上手。
因為對方的手藝太好了。
我很震驚地看著他快速且極具技巧地處理著十幾種食材,那畫面簡直像是在看《地獄廚房》的現場版。不管是切菜的速度、手法,還是給雞腿肉去骨的專業水準和俐落程度,都和我根本不是一個次元。

如果是自己做飯的人應該明白, 當面對一個做飯流程嚴謹流暢的大廚時,隨意幫忙只會破壞那份流暢,就像現在的我站在旁邊根本插不上手。我試著幾次幫忙切菜未果,只好悻悻然在旁邊看著。

他同時進行所有菜式的處理,幾個爐子一起開著,轉眼之間桌上就堆起了皮蛋涼拌豆腐,油爆蝦,黃瓜炒雞蛋,虎皮蛋……與此同時火鍋的食材也全部切好了。我只能負責傳菜。
「去吃吧!」東北男孩很少說話,我問他之前是不是專業廚師時也不回答,現在只對我說了這一句,我應了聲好,就把剛做好的虎皮蛋拿去客廳。茶几上也已經滿滿噹噹。媽媽桑在幫大家分飲料,問我喝茶還是汽水,然後也讓我坐下了。
“乾杯!”
桌上擺放著不知誰的手機,在轉播遙遠故鄉的春節聯歡晚會。我們圍在旁邊的沙發上,把小椅子也拖過來坐了一圈。
其實我很少和別人坐在一張桌上吃飯。
很小很小的時候,在我還不知道家裡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的時候,我的夢想就是和爸爸媽媽坐在一張桌上吃飯。像是電視劇或課本插畫裡那樣的,一家人坐在桌邊吃著家裡做的飯的場景,對我來說就像是夢一樣,是「世界上居然也有人過著這樣的生活啊」 的幸福幻想。
為此也做過很傻的事:故意在學校裡闖很大的禍,然後死不低頭認錯,直到班主任把媽媽喊來也不夠,又把爸爸喊來了。那時候我不知道他們已經離婚了,好像幾年來第一次看到他們都在。回去的時候已經很晚了,所以只能一起在外面吃飯,我說要吃肯德基,然後故意在點餐的時候說:“要吃全家桶!”
像白痴一樣。我以為吃了全家桶我們就永遠是一家人了呢。
那時候常常輾轉在不同的「家」 裡,學校裡要填表格,問你家在哪裡的時候,我常常都要支支吾吾很久,因為我不知道說什麼,答不出來。
好像要嘛是在百貨公司的地下一層餐廳吃飯,要嘛是冰箱裡凍著冷藏的飯,要嘛是家人從公司食堂打回來的飯。後來全家便利商店開到我出生的城市,冰箱裡就會放著一週份的便當。有一段時間,家裡會開火的情況只有做速凍水餃和速溶紫菜蛋湯。我好討厭一週都不會變化的冷藏飯的味道。
我大概就是因此才開始學習做菜的。剛開始學做菜的時候,我常常不知道要做什麼,因為我不知道人們會吃什麼,所以都是學的動漫裡出現過的菜色。如今的我絕對不會讓一道菜留超過一天。我過去曾吃不出冰箱裡放了一周的菜的腐敗味,現在我好不容易讓自己變得能吃出來了,便決定再也不要吃到它了。
現在,我面前的桌上有一大堆,明明也不難做,但是很好吃,是我從來沒有見過的飯菜。我好像是第一次吃別人親手為我做的飯。周圍還有很多人,雖然我不知道他們的名字,只知道編號。
我很喜歡很喜歡那一頓飯,雖然我快不記得味道了。我記得吃了柚子湯底口味的雞肉火鍋,我吃了很多涼拌豆腐。
也並不是完全沒有吃過別人做的飯。有一段時間住在外婆家裡,外婆會做飯。大概八、九歲的一天吧,我看著外婆突然想到,如果不是因為我們的血緣關係,這個人一定不會為我做飯的。
但是面前的飯是只因為我是我,為我而做的飯。我只是默默吃著,誇獎好吃。
媽媽桑,還有女孩們其實都在各做各的事。中間一起看了一下春節聯歡晚會,大家聊起今年的小品如何,其實我也接不上話,因為我之前也沒怎麼看過春晚。每次春節跨年的時候都是和朋友在網路上聊天度過的。但還是很開心,我沉浸在這樣的氣氛裡,在這個異國他鄉第一次有了過年的實感。
大概十點開始就更熱鬧了。大家都拿著手機在傳訊息,還有人在打影片。我看到媽媽桑超級開心地拿著手機開視訊通話,和她的女兒說「春節快樂」。其他人也在用微信和家人聊天,互相祝福。小小一個一室一廳裡居然有十幾二十個人的對話聲,原來過春節時人們是這樣的。
我隨便應付了幾個需要回的微信,然後想起還有個作業沒交,抱著手機寫選修課的報告。交上報告的時候正好是日本時間十一點,國內的零點。手機上放著春節聯歡晚會的倒數計時,媽媽桑帶頭舉起飲料: “新年快樂!”
我們也都舉杯,「新年快樂,萬事如意!」「恭喜發財」雲雲地說著吉利話。
無論如何,這是我度過的最熱鬧的一個春節。

06 新年快樂,明天開始我是歌舞伎町的按摩女
我會在這個店裡乾三個月。
雖然當時對店長說的是要幹個一兩年,但是我很清楚,我只會乾三個月,之後就要回國。我要在這三個月賺足夠的錢,回國後一個人開始新生活,這就是啟動資金。
所以這一定是我唯一一次和大家一起吃年夜飯。事實上,這也確實是我唯一一次和店裡的人一起吃飯。
之前在日本的店裡工作的時候,我從來沒有遇到過這種問題。我是說,那種所有人緊密相連的氛圍。日本人的店裡並不崇尚這種「 家庭式經營」 的氣氛,大家的關係大多很淡,尤其是和經管層,有交情的也只有共同幹了幾年甚至十幾年的女孩同伴。現在感受到這種氛圍反而讓我不知所措,我大概永遠沒有辦法融入其中吧。
當然,我知道,或許這裡的所有人都比我更精明。或許是一半謊言,一半真實地活著;或許對他們來說,這根本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但我做不到,我連一半的真實也拿不出來,我也做不到心無芥蒂地接受好意和給予好意。我並不知道與人互相幫助生活是什麼樣的,即便只是交換利益的,我也無法想像那種心境。
我會永遠和所有人都保持距離,起碼那時候的我是這麼想的。
年夜飯結束後,除了7 號姐姐,我們都回到了店裡。已經很晚了,媽媽桑對我說,今天就在店裡住下吧。
住在店裡的人很多,比如那兩個越南女孩,她們在日本沒有住處,好像是一直住在店裡的,簡單來說就是「黑」 在日本。深處的幾個隔間,也有其他姐姐常住。
我一看確實早就錯過了末班電車的時間,我也不想在日本打死貴死貴的計程車,便也應下。按摩店已經熄燈關店,我們就在平常客人用的洗澡間簡單洗漱。媽媽桑收拾了廚房,把沒吃完的年夜飯凍起來,廚房裡傳來蟑螂爬行時窸窸窣窣的聲音,樓下的新宿街道也已經安靜了,只有喝醉的日本大叔偶爾傳來的叫嚷。
睡覺的地方就是隔間的按摩床,床就那麼點大,沒辦法翻身。媽媽桑幫我拿來薄棉被,隔間開著暖氣,但還是很冷,帶著潮濕霉味的被子也很薄,而且很短。我把脫下來的羽絨外套蓋在被子上面,裙子蓋在被子遮不到的腳上,脫下的毛衣和店裡拿來的毛巾拼成枕頭,就這樣直接睡下了。
明天中午12 點起床,媽媽桑告訴我,已經有客人預約我了。 「有好多預約呢,都排滿了。」她說得很開心,我也很開心。風俗業的新人期是很短也很珍貴的,這是最賺錢的時期,幾乎所有常客都會去點店裡新來的人,這樣的「嚐鮮期」 約有一個月。一個月後能留下的客人,還會來第二次第三次的,他們就會成為常客。
這是一個月內的決勝局。雖然也有很多人會在新人期一過就換店做,永遠當新人,永遠靠著新人期賺錢。
明天開始—— 哦,不對,零點已經過了—— 今天開始我就要在這裡接待客人,正式開始作為按摩女的生涯。
會是什麼樣的客人呢?
我這樣想著,睡在又硬又矮的,不那麼舒服的枕頭上。脖子好痛。其他燈都熄了,但走廊裡還有淡淡的昏黃燈光,只有簾子隔開的小隔間,還能聽到隔壁其他女孩兒的鼾聲。
這是一個睡得很不舒服的新年,也是我至此過得最好的新年。
屬於我的2022 年就這樣開始了。
「新年快樂,新宿。」我抱著一種反正也沒什麼可以失去的心情,看著頭頂的天花板,用日語小聲地說,然後合眼睡覺。
(未完待續)
//作者:匿名
//編輯:Rice
//排版:板磚兮
版權所有,未經許可請勿轉載
BIE別的女孩致力於呈現一切女性視角的探索,支持女性/酷兒藝術家創作,為所有女性主義創作者搭建自由展示的平台,一起書寫HERstory。
我們相信智識,推崇創造,鼓勵質疑,以獨立的思考、先鋒的態度與多元的性別觀點,為每位別的女孩帶來靈感、智慧與勇氣
公眾號/微博/小紅書:BIE別的女孩
BIE GIRLS is a sub-community of BIE Biede that covers gender-related content, aiming to explore thing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females. Topics in this community range from self-growth, intimate relationships and gnowway and art. We believe in wisdom, advocate creativity and encourage people to question reality. We work to bring inspiration, wisdom and courage to every BIE girl via independent thinking, a pioneering attitude and ified.
喜歡我的作品嗎?別忘了給予支持與讚賞,讓我知道在創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續這份熱忱!



- 來自作者
- 相關推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