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僅20歲」時感染了HIV,我想挑戰主流防艾話語
寫在前面:這篇文章寫在去年12月初,最初發佈於706青年空間的公眾號。因為需要終身服藥,所以我為自己取名為「藥罐兒」。除去接受一位記者朋友的採訪,這篇文章也是我第一次以感染者的身份面向公共空間發聲,非常感激我的兩位朋友在我寫作前後提供建議和幫助。
2019年12月1日我度過了我的第4個世界愛滋病日。當我醒來時,就一如既往地從朋友圈的照片、訂閱號的推文中感受到撲面而來的節日氣氛。如今的防艾宣傳已經十分普遍,尤其在世界愛滋病日左右,各方也都卯足了力氣。但我認為,其中廣泛使用的一些話語仍然值得商榷。
今年也是特別的一年,在它到來之前,我剛好度過了確診感染後每天按時服藥的一個月。

當我親身經歷了確診、用藥和向信任的朋友出櫃,過去那些零碎的思考,重又被喚起。但因為感覺到自身在邏輯與專業上的限制,便在約了位社工背景的朋友聊了聊。在此,便透過這篇文章對我們的討論成果進行梳理與闡釋。
"安全永遠是第一位的"
安全性行為是防艾宣傳的核心倡導,因而「安全永遠是第一位的」一直有相當高的「出鏡率」;與此相對的,那些試圖透過不戴套來獲得更多性愉悅的行為,則被批評為「尋求刺激」。在公共衛生視角下,將安全視為第一位的,似乎具有天然的正義性。個體把安全當作個人價值觀中發生性行為的前提、底線更無可非議。但不容忽視的是,從其它視角看待性,或許就會得出完全不同的結論。例如,從反性騷擾的角度出發,「同意」是第一位的也完全成立。而個體因為對性不同的認知與多元的價值觀,更會為「發生性行為時,什麼是第一位的」提供豐富的解答。那麼這些不同的視角,又有誰該當作首要的考量?
更要注意的是,對安全的片面強調,常與將性視為禁忌、危險的文化合流,樹立起「安全」與「刺激」的二元對立。其中,遭遇貶斥的不僅是人們對情慾解放的追求,性對於個體的其它意義──建構性別認同、表達愛與親密、尋找認同與歸屬、釋放壓力等,也都難以被正視與討論。
事實上,性安全和性愉悅也並非互為正反、彼此對立的存在。就如避孕手段的持續發明,為人們帶來了性愛與生殖的分離,安全的保障可以讓我們免於對風險的憂懼,帶來情慾與身體的解放。而為我們對性愉悅的需求正名,建立對它的客觀認識,也可以為安全的落實帶來更多的動力。保險套的不斷改進,將情趣和愉悅納入考慮的各種特殊套的出現,都是對此最好的證明。反觀「尋求刺激」的批評,反而可能強化一些人「不戴套更爽」的刻板認知,變相鼓勵了ta們帶有僥倖心理的「越軌」實踐。
"安全=負責"
「安全=負責」的防艾話語同樣常見。生活中的確有很多人會因為責任意識的缺乏,在發生性行為時沒有全程使用保險套。尤其在異性性行為中,女性相比男性更直接承擔了意外懷孕的風險,讓部分男性覺得避孕與自己無關。因此對自身與性伴侶的安全責任必須得到充分的強調。
然而,安全與負責的捆綁讓我們時常架空性行為發生的具體情境,對我們身處的性別文化與情慾文化也缺乏探討。個體的行為選擇被簡單粗暴地歸因為道德失範,ta們的需求與境遇,以及和性伴侶之間的權力關係都常常被忽視。潘綏銘、黃盈盈和李楯在《中國愛滋病「問題」解析》一文指出,只有關注到個體行為、意識和特定社會文化裡的具體情境的相互作用,我們對「高危險性行為」的理解才可能具備深度與廣度[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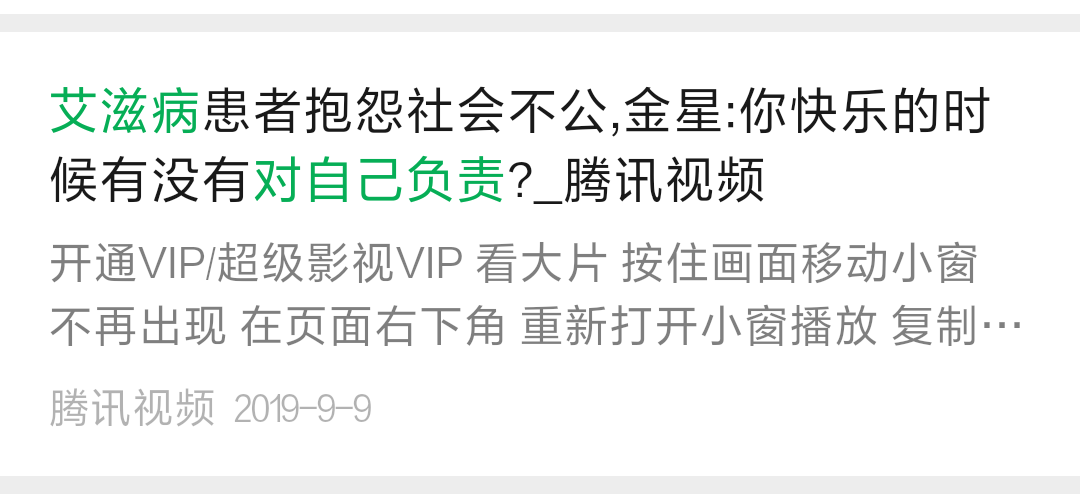
在避諱談性的文化中,人們不僅戴套的意識淡薄,也往往不具備「性前商議」的意識與習慣,更難以在性行為發生的過程中嚴肅、坦然地表達意願。一旦其中一方提出「不戴套」的邀請,更以「愛」與「信任」為由,另一方很可能會陷入不知所措的境地。在實際的生活情境中,「愛」與「信任」並非都是出於主觀意圖的情感綁架,要被歸咎於輿論廣泛詬病的「渣」與「虛偽」。當我們僅僅強調保險套避孕、防病的作用,長期的宣傳中又在社會意識層面構築起「正常人/普通人」與「愛滋病相關群體」(帶因者、易感人群)的區分與隔離,確實容易造成個體對自我與性伴不論在健康或德行上沒有「缺損」的盲目相信。這樣,出於疾病預防的戴套行為,反而會被視為對雙方信任與「健康」「正常」的自我認同的破壞。根據張有春2009-2011年間在西南龍城市開展的社會調查,受訪的性工作者表示在與客人發生關係時能夠堅持戴套,但與男朋友或配偶發生性關係時則很少使用[2] ,或許能為以上論述提供例證。
如何面對對方的信任、撒嬌、示弱與軟磨硬泡,處理自我在內心的健康焦慮與道德焦慮,我們都缺乏經驗與思考。即時的靈活應對經常是奢侈的幻想,柴幹火烈之際開展一場「戴不戴套」的辯論持久賽對於許多人來說同樣難以實踐。這其中不僅需要表達的技巧、應變的能力和拒絕的勇氣,更蘊含著難以應付的情感和權力層面的較量。不對等的性別權力束縛著弱勢一方的性自主權,讓ta們的意願無法被真實地表達,也無法被對方認真地對待。在這種情況下,個體如何認識自身面對的責任與風險,性安全在ta的價值排序中又會被置於怎樣的位置,都可能是作為旁觀者所難以想像與共情的,同樣也難以被「不負責任」這一道德歸因所解釋。
而當安全與負責的捆綁轉化為感染者自身的悔恨與自責,以及外界針對ta們「自作自受」「不自尊、不自愛」的道德審判,感染所要承擔的不僅是疾病本身帶來的影響,更是由社會轉嫁的責任與施加的羞辱。於是,愛滋病蔓延的社會問題一面被各方大肆渲染,一面又在不斷與個人德行的捆綁中被囿於私人領域,最終造成的將是解決路徑的曲折與防艾工作的低效[1],社會也將因此負擔更多的代價與高昂的成本。
更令我心痛的是,有些感染者對自身的反思甚至責問,那些被塑造、篩選和引以為鑑的個人書寫,最終成為媒體與社群進行大眾教育的經典文本。 ta們並沒有被視為完整的“人”,而因為健康與道德的“缺損”被作為宣傳工具,成為主流防艾話語的共謀。
較常見的就是「一次不戴套就感染」的故事。雖然出發點是希望受眾減少僥倖心理,然而一旦脫離了情境和前提,這一敘述既是對受眾恐艾心理的利用與強化,也會因為對故事主人公行為邏輯的簡化,增加人們對感染者的誤解與防艾及反歧視宣傳的阻礙。
“傳染”與“傳染”
此外,我們也要對「傳染」與「被傳染」的醫學話語保持謹慎。王浩在《「有色」眼鏡裡的「變色」--論一個防艾研究與報道中的「七大罪」一文中指出:「其實每個經過性傳播的艾滋感染者都可以說是被人感染的,每一個人都可以向上追溯,於是艾滋病來自非洲等等帶有價值偏見的判斷一度滿天飛。其實,按照這個模式,每一個艾滋感染者在被感染之前都是'無辜'的,都是被'壞人'傳染的。於是,這樣一個荒唐的邏輯出現了:艾滋病傳播基本上就是壞人惡意傳播壞人並繼續惡意傳播壞人的過程。”[3]
在醫學視野下,病毒傳播的確存在方向,然而這話語已被賦予更多的社會意涵。不僅是性傳播,還有經常引爆輿論的職業暴露,感染雙方的責任往往難以劃定,背後更可能存在社會結構、管理體制與職業規範等深層的原因。然而,病毒的傳播方向已經在向人們揭示,不論在道德上失範與否,最初攜帶病毒的人就是「原罪」。而當這種認知與其它刻板印象合流,不僅是「愛滋病來自非洲」的種族偏見,「大叔傳染小鮮肉」「社會人士傳染學生」的文本也都得以流傳。因此,建議在防艾宣傳乃至日常表達中更多使用“感染了”而不是“被傳染”,避免造成對感染者的進一步污名。
「要愛不要艾」"遠離愛滋病"
最後,我想聊聊我們對愛滋病的「不要」和「遠離」。當這些口號被人們高呼著,似乎我們就真的可以把它永遠隔絕在自己的生活之外了。
但你有沒有試過,如果自己有一天要面臨確診感染的可能?
前天有位朋友問我,確診後心態這麼好是不是因為之前曾想過自己會感染。突然的一問讓我有些錯愕,旁邊的朋友也立刻提醒她「誰會想過這種事呢」。然而,我之前確實覺得「『感染了』其實是一種可以接受、可以擁抱的狀態」。不可否認,我在確診後沒有經歷痛苦,是因為獲得了足夠的社群支持,擁有可以講述的伙伴;雖然自己也擁有多重邊緣的社會身份,卻依然在不同的階層維度享有特權。但也像一位朋友所說,「你本來對這個就比較有思考,這些年也算是有一些成果了」。
如今的心態,該是最大的成果了。

而在當下的防艾宣傳中,我們千方百計地告知受眾如何防艾,卻沒有告訴ta們存在防不勝防的萬一——就像我確切地知道自己是在全程使用安全套的情況下感染的。同樣,我們也很少告訴ta們一旦感染了HIV,要如何進行心理建設、獲取友好的同伴支持,更極少討論要怎樣用今後一生的時間與病毒共存,如何在十來歲、二十來歲這些所謂「人生剛開始的時刻」就要開啟堅持每天固定時間服藥的日常。我們“重在預防”,也常常程式般地講述著“愛滋病沒那麼可怕,如今已經成為一種可防可控的慢性病”,但很少真正體味過這句話的分量,接受它要為我們關於疾病的認知與價值觀所帶來的改變。我們心底仍在發出恐懼的尖叫,生活裡仍缺乏對疾病本身無所避諱的直視與探討。我們的宣教與文化仍試圖用一層薄膜的力量,固守住舊的關於「健康」與「疾病」的等級與秩序-當那些恐懼的訊號藉由「遠離艾滋」「要愛不要艾」的話語傳遞,不僅會加重個體面對感染的病恥感,更可能加劇社會對感染者的歧視,在「不要」與「遠離」中築起針對感染者的社會障礙[4]。
所以,當我成為新感染者,愛滋病毒就此讓我們變成兩種完全不同的人類。也不論我們誰更注重養生和保健,誰更主動或被動地消耗著自己的身體——熬夜、吸煙、酗酒、被資本與制度奴役......愛滋病帶來的「缺損」讓我永遠更遠離所謂「健康」的完美定義。當我接受醫院與疾控不夠專業、友善的服務,在接連的盤問、訓誡與惋惜中遭受凝視,最終被醫學話語的霸權與人類關於健康的理想拒斥在「正常」的定義之外。
年復一年的“反歧視”,我們又立足於怎樣的立場?
結語
朋友提醒我“批判只是手段和過程”,當我寫下這篇文章,固然有混雜著委屈、憤怒的諸多不滿,但也更加希望當這些問題能被看見,更加多元、更側重賦能、更少的道德綁架、也更能讓受眾共感的防艾話語可以被創造。

身為行動者,我曾數次發出微弱、稚嫩的聲音。如今,當我擁有新的身份,更能感受到那些隨時要衝破這軀殼的倔強。我無法代表更多人,雖然從未放棄對自身特權的反思,但也難以全然掙脫個人境遇與階層造就的限制。我亦無力改變更多的現實,但仍寄望於每一次拼盡全力的吶喊,願能一直為自己作為一個「人」的尊嚴而戰。
參考資料:
[1]潘綏銘,黃盈盈,李楯.中國愛滋病「問題」解析[J].中國社會科學,2006(01):85-95+207.
[2]張有春.愛滋病宣導教育中的恐嚇策略及其危害[J].思想戰線,2017,43(03):18-24.
[3]王浩.「有色」眼鏡裡的「變色」-論一個防艾研究與報道中的「七宗罪」.
https://mp.weixin.qq.com/s/T95eVCZf5cd4n8-f-jinCw
[4]徐若菲.高校防艾宣傳活動中的隱性社會排斥與消解策略-以北京N大學為例[J].黑龍江社會科學,2019(04):91-98.
喜歡我的作品嗎?別忘了給予支持與讚賞,讓我知道在創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續這份熱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