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按摩女日記:今天的客人是醉酒老頭和流浪漢
以下文章來自BIE別的,作者BIE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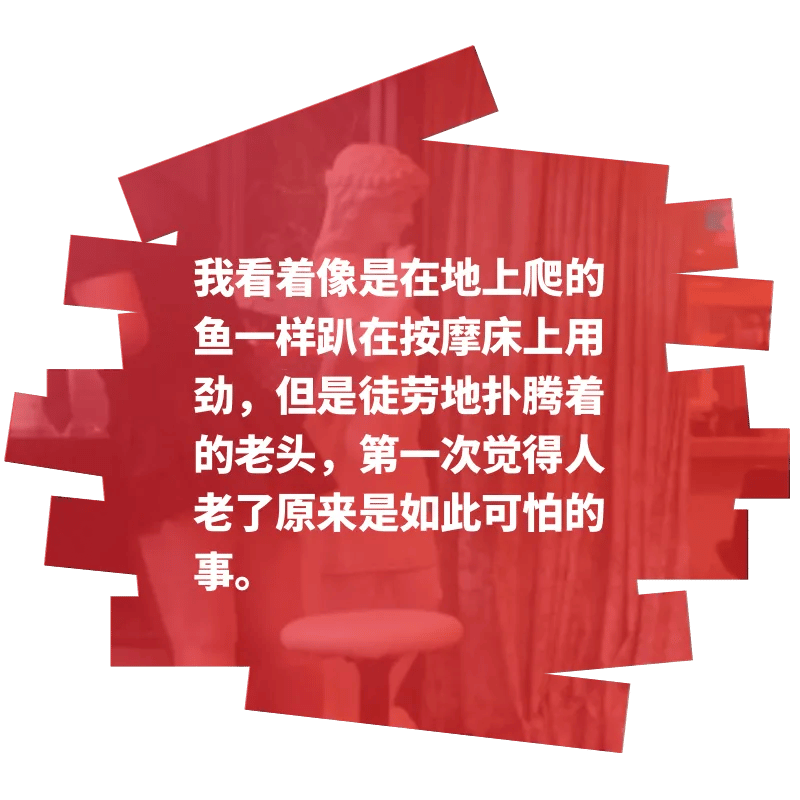
這是「東京按摩女日記」系列連載的第四篇,前情請看:
那一頓年夜飯結束以後,我就開始了作為按摩女的正式工作。
除了在店裡醒來的大年初一,大部分情況下,我還是回自己租的房子住,我還有貓要照顧。我每天中午或下午到店,帶著一堆化妝品,先用一個小時仔細化妝,也有的時候客人來得急,我就只有半小時能化妝。

也有幾個年輕的姊姊是不帶妝上班的。我是店裡化妝最用心的女孩,因為我很清楚,我的賣點就是這張臉,還有更年輕的身體。別看那些賣座的銀座陪酒女會出書教授社交術,說什麼這行最重要的是社交技術,實際上業內的人誰都清楚,這就是誰最漂亮又願意脫,誰才能賺錢的行業。
但我的臉很醜,儘管說是這家店裡最年輕好看的,可過去讀書時,我是班上那個被起外號“醜女” 的女孩,漫長的欺凌一直持續到了我轉學為止。還好現在我擅長化妝,我會花很多時間給自己施上“變身魔法”,在帶妝的時間內,我看起來完全是另一個人。
曾經班上那個最漂亮,最招人喜歡,交過最多男友的女孩從耶魯畢業,而我卻在用這張臉做風俗賣身,真是神奇啊。不過我也不是特例。
業內有好多女孩都是這樣的,尤其是那些年輕漂亮的日本風俗娘,都是以前在學校裡被稱為醜女,不招人喜歡的孩子。現在大家化上濃妝,就搖身一變成了用臉賺錢的風俗女了。反而是那些學生時代受歡迎的女孩子,很少踏入這行。
網路上有句很土的話,愛和錢都會流向不缺愛和金錢的人。雖然,說難聽點,也就是那種真正的漂亮女孩,就算想用身體換錢,也會通過和我們不一樣的管道就是了。例如那些出入銀座社交派對的港區女子。
但只要在做這樣的事,大家都是商品。
我作為底層擦邊風俗店的商品,在店舖官網上放上了全身照片供人挑選。照片拍得很醜,我們不像那些高級風俗店或俱樂部,會帶女孩去歌舞伎町裡那些水商風俗業者專用的攝影室拍照(話雖如此也就是大學生攝影作業水準)。但這也不那麼重要。

我們店的經營方式是客人打電話或發line 預約,基本上,所有客人都是熟人。早在我開始正式上班之前,媽媽桑就已經在電話裡,或者在對方來店的時候對那些熟客提過了: “來了個新女孩,很年輕哦!”
01 第一份工作是通宵喝酒
最開始,也是最有人氣的時候,我從中午12 點到晚上10 點幾乎排滿客人,忙起來的時候基本上沒有休息時間。
只不過,其中不少都是以後賺不上錢的客人。我每天都等著客人喊我推油,因為又省力氣,同樣的時間裡賺得又多。只按摩一小時,不加鐘也不推油的客人,壓根沒有「培養價值」 。
其中,越是有些怪癖,熟稔於此道的,越容易掏錢。這可能有些反直覺…實際上,越是不怎麼來風俗店的「風俗初心者」 越摳門,或者說是他們還不理解這裡只有純粹的買賣關係,往往同時兼具摳門和警惕心/自我意識過剩;越是長年都在用風俗店的人,他們反而清楚,我們這些女孩與他們就是買賣關係,總之—— 多多掏錢是一種禮儀。
我遇到的第一位這樣的客人,他來風俗店不為別的,就是想找人喝酒。
我接待他的時候是晚上八點多,媽媽桑提前和我打了招呼,說下一個客人個性很好,「他就是喜歡看女孩子喝酒吃東西,你陪他吃點喝點聊聊天就行。 」
預約時間到了,來的人果然提著一個塑膠袋,裡面裝著樓下便利商店買來的啤酒、燒酒、下酒菜,還有肉包子。臉上樂呵呵的,大概五十多歲吧,不過我都忘了他的臉了。但我還記得我對他的第一印像是「在這條街上待了很久很久的人」。
就像是之前當陪酒女時遇到的那個數學老師……那些在這條街上待了很久的,平均每週都要去一次平價風俗店或者陪酒女店的“歌舞伎町老顧客” ,他們的特徵往往是:看起來四五十歲年紀,普通的勞工階級打扮,衣著樸素。
這樣的客人有一套自己的禮儀和規則,我們進了隔間,他先從便利商店的塑膠袋裡拿出兩瓶熱茶給我,讓我選自己想喝的那個,然後對我說,「辛苦了。
“初次見面,” 我收下茶鞠躬,然後眨眨眼,“ 怎麼稱呼您?對了,可以的話,可以喊我chiyo 。”
這是我的策略,說是狡猾也未嘗不可—— 我會讓「值得發展」 的客人直接喊我的名字。雖然,店裡的大家都是以工號稱呼的,但也因此,擁有名字的我會不一樣。我的優勢除了年輕,還有會日語,我能像陪旅館裡的那些日本女孩一樣接客。
說穿了就是色戀路線。
02 我的價格
當我問對方要不要推油時,他拒絕了,只要按摩。但只按了大概十分鐘……我腦子裡還在盤算著,就像是學生時代背課文一樣背著按摩步驟,他卻突然示意可以了,然後坐了起來:
“來喝酒吧。”
不用費力氣喝酒就能賺錢,我當然樂得輕鬆,喜笑顏開地說好。然後我坐在椅子上,他坐在按摩床上,從塑膠袋裡拿出酒來喝。
“ 您喜歡喝酒嗎?” 我問。
這是陪飯店裡的定番台詞,實在沒話可以聊的時候就可以說這個。他說當然喜歡啊,問我喜歡不喜歡,我就順著酒開始說起來了,談論起了日本酒和日本產的威士忌。當然這也是為了討好人,日本男人聽到外國人誇日本酒,多少都會高興。感覺這真是全世界通用的技巧。
「 你日文好好啊。」客人這樣誇我。
雖然我的日文程度在日本的留學生裡根本不夠看的,被這麼誇了也沒什麼值得開心的,但是我還是裝出喜出望外的模樣,若無其事地提起了,「其實在來這家店之前,我是在歌舞伎町的Girl's Bar 工作的呢。
我正在自抬身價,放在第三者看來應該很可悲吧,我洋洋得意地向對方暗示著「我的價值」 。以前我是花6000 日元也只能一起喝酒聊天的女孩,在這裡卻能肢體接觸。能摸哦,像這樣暗示著,購買我是不虧的。
對不做這行的人來說,提起這種經驗只會感到丟臉吧,但是嘛,我們做這行就是不能把自己當人,一定要當商品來看的。
如果不能把工作時的自己當成商品,精神就會出問題。
我笑著談論自己價值6000 日元一小時的價格,果然對方也表現出了極大的驚訝和興趣,立即表示能這樣一邊喝酒一邊聊天的女孩,在這家店裡可不多,今天一定要一起好好喝個痛快。
“當然啦”,我笑著說。
我們喝著酒,聊些不痛不癢的話題。一個多小時過去,眼見酒喝完了,雖然還在按摩時間內,他乾脆準備帶我去樓下便利商店買酒,並且包我一整晚。
「 一晚?」我略微驚訝,第二天還是工作日呢。
「 對,我常常就睡在你們店裡的。」愛喝酒的客人說道, 「 我從以前開始,只要下班晚了就來這。店裡還能洗個澡,洗完澡就在這睡覺過夜,第二天直接去上班。
很難想像這到底是怎樣的生活方式。
我想像社畜下班就去風俗店,在風俗店裡和女孩子喝酒聊天,然後就在風俗店裡洗澡睡覺了,第二天穿上那身西裝外套,繼續去上班。混進地鐵站的人群,和周圍成百上千個黑西裝社畜沒有兩樣。
這樣的人該不會在日本很多吧?我心想著,打量了一眼他臉上的皺紋—— 如果不是單身,那孩子都起碼該上中學了。如果知道爸爸是個會晚上不回家直接在風俗店過夜的人,是怎樣的心情啊。
我用幾秒鐘想像了一下一個這樣的家庭。算了,這也不是我該想的,更何況,這裡是歌舞伎町。
會來這裡的也都不是什麼正經人,說不定,這傢伙也有一段奇妙的人生,所以才過著如此奇特的生活。這裡是東京的低窪,聚集在這的人都各自有原因。
一切都進展得很順利,我們走出隔間,我去休息間取了自己的外套披上,開開心心地去和媽媽桑打了個招呼,就拉著客人下樓了。
媽媽桑當然樂意,看我把客人哄得開心,她也高興得不得了,一邊用日語問客人,果然這孩子不錯吧,一邊送我們到門口下樓。我能感覺到自己離開店時背後的目光,心裡不禁有種驕傲的感覺,覺得自己剛才的樣子還蠻帥的,真是能幹的風俗女啊。
沒錯,我很能幹,我會證明僱用我是個好選擇,我會讓對我很好的媽媽桑感到物有所值。
有這種想法或許有些可笑,別說放在風俗業了,放在一般產業都會被人笑話吧。當然啦,她是為了她的目的,我也是為了自己的目的才努力工作賺錢的,而且我討厭欠人東西。媽媽桑出於自己的目的而待我親切,我就要創造比她所期望的還要多的價值。
我要把那份親切扯平到,以後不管是突然跑掉還是乾了什麼,都不會為此有任何良心不安的程度。或者說,起碼我心裡平衡了就好。
我想證明我起碼在當風俗女時是有價值的。
還是第一次周圍會有人因為我在而感到快樂。
吹著外面的冷風時,頭腦稍微冷靜下來,突然這樣想到。
03 瘋癲老人日記
我們在便利商店買了酒,回來的時候,客人喊來媽媽桑加鐘。
“哎呀,真抱歉啊”,媽媽桑滿臉歉意地說,“她原定晚上一點開始還有另外一個客人。”
還有另一個客人?這連我都不知道,而且居然是從一點起定,那已經是我們店的打烊時間了。
愛喝酒的客人悻悻然地說好吧,不過依然決定延長到晚上十二點,之後就在店裡住下。我們繼續喝著酒,聊了會,喝完了也吃完了,他乾脆躺到按摩床上,讓我也躺上去。我穿著自己的衣服:一件短袖上衣,一條半身裙,下面是很厚的黑色打底襪,就這樣爬上去也靠著躺了會,聽著旁邊一身酒味的大叔說著無聊得我都記不住了的話題。
晚上十二點多,他結了賬,我送他去洗澡。媽媽桑收了錢,然後就給店裡關了燈。大家都已經下班了,只有我一個人還有客人,走廊的燈也都關了,只有幾個店裡女孩自己住的小隔間的頂上漏出一點點燈光。
“下一個客人有點怪癖,反正是個老頭,你糊弄過去就行。別擔心,他也是常客了。” 媽媽桑這樣囑咐著,“你今天要不要住在店裡?”
我想了下,“我要等早上六點的第一班電車,然後回家睡覺。”
媽媽桑於是囑咐我,走的時候只要帶門就可以了,會自動上鎖,我點點頭。
我稍微休息了一會兒,也送洗完澡的客人回房間睡覺了,我朝著媽媽桑之前指給我的下一間隔走去。那是位於最角落的隔間,空間比其他隔間稍微大一些,我道了聲「打擾」 就進去了。
進去的一瞬間皺起了眉。
房間裡有股淡淡的說不出來的味道,像是老家具腐朽後散發出的氣味。和其他隔間相比,這間隔間很有生活氣息,多出來的角落空地裡放著旅行箱,但是也沒有女孩子住在這的跡象,房間裡沒有化妝品。更何況,要是店內女孩自己住的隔間,那這會人也該回來睡了。
讓人皺眉的主要是躺在按摩床上的客人本人。
那是一個看起來少說也有六、七十歲的老頭,頭頂基本上已經禿了,兩側卻還留著長髮。那頭髮也不知道多久沒打理過,油膩得像是廚房裡的抹布。他背朝上趴在按摩床上,身上蓋著店裡的薄被子,露出瘦骨嶙峋的肩膀和胳膊,在玩連著充電器的手機。
他看見我來了,抬頭對我笑,那張臉也好奇怪,像是貓。乍看之下我還以為是女性,看到裸露出來的乾癟的脖頸和胸口才確認是男的。
就像是……新宿車站門口的那些流浪漢。瘦得像是我按摩時手勁稍微大一點就能把他的骨頭折斷。
緊接著就來了。他蜷縮著身體從床上爬起來,呵呵地對我笑著。身上的薄被子掉了下去,露出下面全裸的身體,還有垂在胯下萎縮搖晃的生殖器。
我努力繃著臉上的微笑。
然後走上去,拿起毛巾蓋在背上,遮住身體,把人又按了回去。
「那我開始按摩了。」我不帶什麼情緒,彷彿沒看見那根雞兒一樣地說。
老頭髮出矯揉造作的假哭聲,試著揮動胳膊,我乾脆隔著毛巾把他的胳膊也按住,開始先按摩手臂。我面無表情,甚至還帶著點營業聲線地問,“這樣的力氣可以嗎?”
我知道對這種人反應越大,他越會得寸進尺,享受他憑這副身體早就無法體會到的戲弄女孩的感覺。所以我不會讓自己露出任何表現出驚駭或噁心的反應。無視,全部無視,只是專心按摩。
老頭一得空就伸手去解我的上衣連結。是那種一排羈扣的襯衫,他解開第一顆時我沒有動作,只是瞇著眼睛,解開第二顆我就伸手揮開,然後重新把兩顆紐扣係好。
於是他便無止境地來來回回解那兩顆永遠解不開的釦子。手放到胸部時,我就直接用力抓住,然後似輕柔地放到按摩床上,開始按摩手臂。
為什麼是第二顆釦子呢,因為如果從第一顆就開始製止他,反而就沒完沒了了。從第二顆再開始按下他的手,讓他知道不管他再努力,這裡是我說了算。
我看著按摩床上故意擺出噁心的哭喪臉假裝抽泣的老頭,客觀來看或許還怪可憐的,應該是有精神問題吧。一個無家可歸的流浪漢,頭髮都沒洗,都這樣了還把錢花在風俗店,無論怎麼想,大概都是精神不正常的,已經被日常的社會開除了的人吧。
都這樣了還在被下半身支配,像個動物一樣,還對著年輕女孩裝哭,人類真是奇怪的動物。
但是要同情也是永遠不可能同情的他的。我也不會真的去思考這個人到底是怎麼回事,怎麼變成現在這樣。如果我是一個社會工作者,或是記者或什麼的,可能還會同情這樣的老年人,想想他們造成這種生活狀態的原因和裡面的社會問題。
但是現在我是風俗女。在這樁生意裡,風俗女是有無限的道德豁免權的。風俗女不會同情客人,客人被做了什麼,都是客人活該。
到了站在他前頭按摩肩膀的環節,流浪漢老頭開始推我的腿,用乾枯的手指頭試著去扯我的緊身褲。褲襪很厚,是保暖型的,他扯不開,於是又開始用力推我。很遺憾,同為動物,我是更年輕、更有力量的。在年輕人裡我力量算弱的,但對上一個骨瘦如柴的老頭,卻有絕對的優勢。我死死站住不動,於是他怎麼也無法把我推倒。
人類老了就會變成這樣嗎?我看著像是在地上爬的魚一樣趴在按摩床上用勁,但是徒勞地撲騰著的老頭。那,蒼老還真是怪可怕的,我第一次覺得人老了原來是如此可怕的事。
於是他開始試著張開嘴巴用牙齒啃我腿根的褲襪。
到了這一步,確實有點想報警的心情。大概有人要說了,報警啊,就當是為民除害呢。但當然,做這行也是不可能報警的。且不說風俗店裡不管發生什麼事都不可能用報警的方式來解決,何況我自己還是違法打工,我們店還是違法店,店裡甚至住著沒有居留卡的黑戶。在風俗業裡遇到這種問題,我們都是用別的方式解決的。
原來如此,是因此特地約了這麼晚的時間啊。店裡人都走了,要說能算是武力威脅的日本大叔員工也回家了。所以才特地選了這個時間吧。也不知道現在我大喊大叫起來,睡在其他隔間的姊姊們會不會醒來。
我想到囑咐我晚上還有一個客人時的媽媽桑的臉,果然以後不用再對她有任何虧欠心了,我能全都記在這一筆賬上。
我拍掉老頭的手,又用力把他壓回床上。好想揍人,不過我的薪水還沒結,所以不能揍客人。之前媽媽桑問我是周結還是日結,我說隨便,現在下定決心就算顯得很可疑,也要日結。
“時間到了。”
我說完,拍掉他的手,收拾了自己的手機,拉上隔簾走了。
收拾東西的時候,發現撕扯的過程中,內衣釦子不知何時開了一顆。好想殺人。雖然一般來說,按照我的性格這時候會像說口頭禪一樣說一句「好想死」 ,不過現在確實是想殺人的心情佔了上風。
這樣一趟折騰完已經是早上快四點了。
04 第一次出禁
我走去洗手間洗手,又撩起水和洗手液洗褲襪。幸虧沒有沾過老人的唾液,不然這條襪子就該丟了,好歹是在唐吉訶德(日本的平價連鎖商店) 買的三條打包裝。
最後後來也不是沒有給客人打過手衝,讓客人脫我的衣服摸胸部,不過是要加錢的,我開價五千日元。以現在的匯率來算不到三百元人民幣。而就算是加錢,瘋癲的流浪老頭我還是敬謝不敏了。
洗衣服的時候,睡在附近隔間的喝酒大叔好像也醒了,我順便去打了個招呼。
「遇到了變態老頭,想摸我呢。」我笑著說。
於是大叔也笑著,“真可憐啊,就是有那種不守規矩的傢伙。要來一起休息會嗎?”
“不了”,我說。他點點頭,“晚安。”
現在距離早班車還有一個小時,但我也不想留在店裡。我回自己的隔間收拾了背包,穿上外套,快速走去玄關,開門。
門鎖著。媽媽桑好像說過,只要怎麼扭就能打開,但我有些忘了,試了幾次也沒打開。我在漆黑的店裡轉了一圈,試著找類似鑰匙的東西。走過靜悄悄的休息間,黢黑的廚房,窗子隱約透出幾點外面的街燈,可以看到電飯煲上有蟑螂在爬,淅淅索索,好幾隻,一溜就沒影了。
平時店裡的姊姊們也就是用這個電鍋煮飯吃。
我又轉頭回了現在讓人有些不快樂的隔間走廊,找到了正在睡覺的五號師父。我拉開簾子,小聲地喊了聲「姐」 走了進去。人熟睡著,我推了推,那手臂熱呼呼的。沒醒,還說了夢話,看起來睡得很香甜。於是我又去找了二號,這次終於把人推醒了。
“姐姐,不好意思,我現在要回家。店裡的門我打不開。”
我小聲道歉,被打擾了睡眠的二號當然一臉不耐煩的樣子,抓了一把頭髮,但是也沒說什麼,從床上爬起來,幫我去扭了兩下,打開了門。
外面冷風灌進來,天色一片漆黑。我對著二號姊姊鞠躬小聲說著道謝的話,她關上門……然後發現自己也關不上,乾脆擺擺手作罷,說算了,然後又回去睡覺了。
我關上門才鬆了口氣,現在還有一小時,我準備去外頭找個地方吃點東西,然後等早上的第一班電車。
不過在那之前。
我拿起手機,打開微信,找到媽媽桑,然後噼裡啪啦發了一串帶著怒氣的文字過去。那怒氣可能比我自己感受到的更甚吧,我用相當憤怒的語氣痛罵了一頓剛才的變態老頭,然後用不容拒絕的語氣說: “我絕對再也不接他了。也讓他以後別來店裡吧。
意思很明顯,要嘛讓他滾蛋,不然我不會再來這件事。我很清楚媽媽桑不可能拒絕這個要求。一個只點最低價套餐的流浪漢老頭,和店裡現在最能賺錢的年輕新人,站在店鋪利益角度,要選誰很明顯。
這就是我們這行解決問題的方式了,也就是所謂的「出禁」。在夜職界裡,遇到壞了規矩的客人,我們能做的終極反擊方式就是出禁,禁止這個人以後再來這家店。風俗女會對差點強暴自己的客人這麼做,陪酒女和牛郎也會用這種手段限制鬧事的客人。
倒是聽說百合風俗業也會出禁客人,不過一般比起肢體矛盾,多是感情方面的,也有會跟蹤女孩的女客。地下偶像那邊也有這種規矩。
發完微信,又在微博上痛罵了一頓發洩,我才走出大樓。
抬頭發現,外面下雪了。
2 月9 日的凌晨4 點,天還一片漆黑,東京開始下雪。
我開始消磨時間,等待早上的第一班電車。四點的新宿,街上還有人,空蕩蕩的街道上偶爾有東倒西歪地走著的上班族,還有剛下班在笑嚷著到處找飯吃的其他夜職女子。要是往歌舞伎町走,這樣的人會更多。
這個點是夜職人員通常下班的時間。亞洲最大紅燈區此刻展現出另一種面貌,恐怕這是只有夜職者才知道的面貌吧。新宿歌舞伎町,常被說成是有兩幅面孔的街道,一面是白天身為繁華商業街的樣子,一面是到處充斥著謊言、金錢與愛的泡沫的不夜之城。
但是,我想歌舞伎町還是有第三幅面貌的。那是只有在這裡工作的人才知道的,風俗街下班後的模樣。穿戴著用錢堆出來的精緻妝容和服飾,在這條街上出賣謊言與愛的人們,他們,或者說我們自己的生活,從這個時間才開始。
在這個時間點,不用言語也知道身邊走著的都是同行。我們上班的時候,新宿是最熱鬧的,到處都有好吃好玩的,順便好玩的裡面也包括我們。
不過我們下班之後,這條街上就冷清很多了。這個點還能吃飯的地方屈指可數,我全都能記在腦子裡:少數幾家還開著門的深夜烤肉店、松屋之類的連鎖快餐,二十四小時便利商店。歌舞伎町的便利店,到了深夜就會有老鼠吱吱叫著從門口溜過。
我倒是也沒有興趣現在再去歌舞伎町散步,又下著雪,於是隨便找了個店開始玩手機,刷手機遊戲和資訊流陷入沉睡的社群網站。
這時我刷到一則好消息,最喜歡的插畫家開了中國的社群帳號,取了一個中文名字,叫「南」。不知為什麼,現在看到這個名字,竟然對簡單的漢字產生了類似感動的心情。
05 雪與南國小島
南上傳了新作插畫。
那個人總是在畫南方的島嶼,新作也是一樣。她總畫沖繩,畫那些綠色的繁茂的樹,來自熱帶的植物,畫熱帶才有的對比度極強的光影,時常是陰天降雨前的大海,皮膚曬得通紅的黑眼睛孩子。一看就是那個南國的小島。夏天,東京是沒有這樣的景色的,我出生長大的城市也沒有。我因為喜歡她的畫去了沖繩,在海邊的小屋住了一周,發現確實就是畫裡的那樣。
即便是對日本人來說,沖繩也是像徵暑假的小島。
夏天,島嶼,彷彿無盡頭的暑假,用島崎藤村的《海》 裡的話來說—— 就是好像一切都沉入無光、無熱,也無眠的夢中。沖繩有個詞叫“島嶼時間”,因為這裡的一切都很慢,島嶼時間是近乎於永久停滯的。
好想去南國啊,我突然這樣想到。
我賺錢,這麼努力賺錢,是為了回國後可以脫離家庭遠走高飛,所以要很多錢。但現在,我卻又突然好想立刻坐飛機衝去南國的小島。雖然現在還是冬天,春天也快來了,但是距離夏天又還有很遠。
即便如此也好想去啊。
外頭還在下雪。要是東京能就這樣沉進海裡,被雪覆蓋就好了。
看了會「南」 的畫,心裡不可思議地變得平靜了下來。如果能去南方的那個小島,那相較之下,現在的一切都不算什麼了。
我回了家,五個小時後還要出門上班。第二天,外面的雪還是沒停,這是讓人高興的事。我檢查手機,媽媽桑果然也附和著我痛罵了一通客人,並且安慰我“沒事寶貝,我們以後再也不接他了。”
又問我:“今天幾點上班?下午一點已經有預約了,是很好的客人。”
我回十二點半到店,合上手機。
外面還在下雪,所以我拿上傘出門。特地拿了水母造型的傘,這還是之前準備送給一個百合風俗女孩的,但沒送出去。於是家裡有兩把水母傘插在傘桶裡,我拿了一把。
外面的空氣是很清冽的味道,雪花落在鼻子上,讓人想到涼涼的甜水冰沙。
白色的雪片顆粒從頭頂的高空中落下來,凝結在水母傘上,很不可思議,很浪漫。透過透明傘膜可以看到青色的城市,往頭頂看去,好像整個東京都沉在海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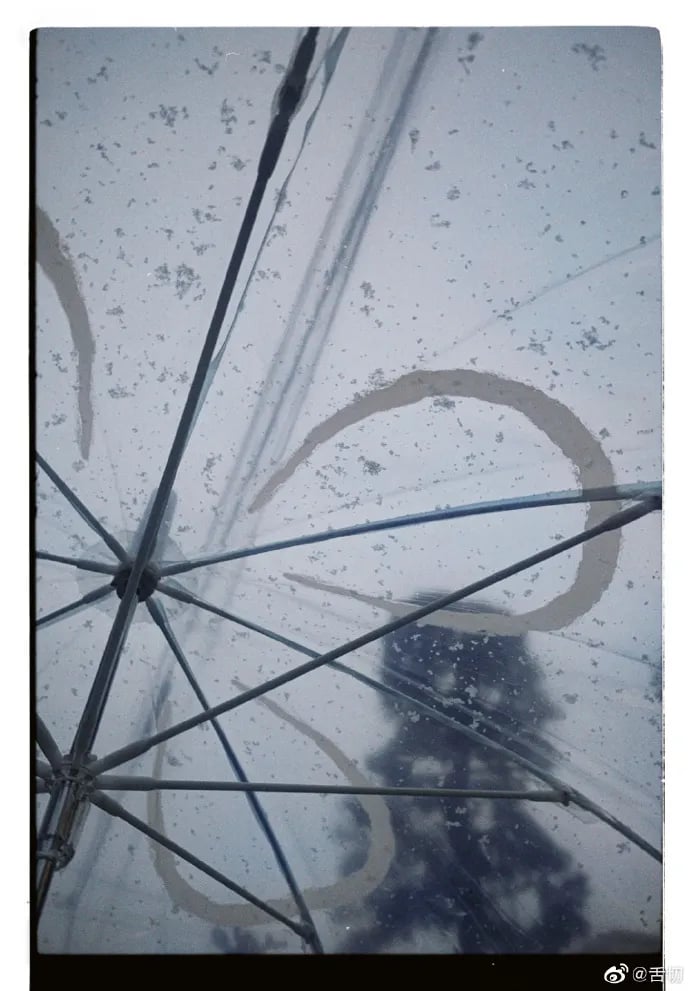
潛水的時候,我們會將海中的白色微粒物,也就是海洋動物的糞便與身體,稱為「海雪」。而此刻,名為東京的海裡正不停地下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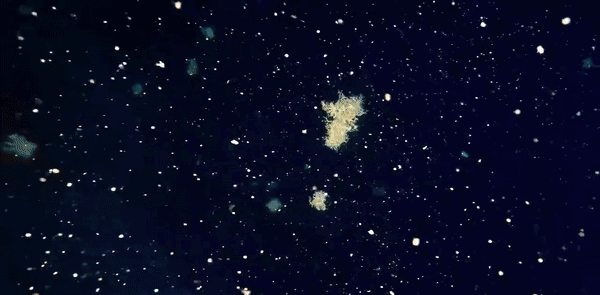
22 年2 月10 日,東京下了海雪。我匆匆出門上班,開始繼續當風俗女賺錢的一天。因為下雪了,所以上班前去吃湯咖哩吧,我想到。
22 年2 月10 日,我在日記裡寫:
因為昨天發生了討厭的事,今天一覺醒來,竟然發現東京沉了。東京沉入瀨戶內海,下了好大的一場雪。因為是瀨戶內海,所以雪花落在鼻子上,嗅到了稍微有點涼涼的檸檬冰沙似的味道。話雖如此,我今天還是要出門上班。
*本文應作者要求匿名發布
//編輯:Rice
//設計:板磚兮
版權所有,未經許可請勿轉載
BIE別的女孩致力於呈現一切女性視角的探索,支持女性/酷兒藝術家創作,為所有女性主義創作者搭建自由展示的平台,一起書寫HERstory。
我們相信智識,推崇創造,鼓勵質疑,以獨立的思考、先鋒的態度與多元的性別觀點,為每位別的女孩帶來靈感、智慧與勇氣
公眾號/微博/小紅書:BIE別的女孩
BIE GIRLS is a sub-community of BIE Biede that covers gender-related content, aiming to explore thing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females. Topics in this community range from self-growth, intimate relationships and gnowway and art. We believe in wisdom, advocate creativity and encourage people to question reality. We work to bring inspiration, wisdom and courage to every BIE girl via independent thinking, a pioneering attitude and ified.
喜歡我的作品嗎?別忘了給予支持與讚賞,讓我知道在創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續這份熱忱!

- 來自作者
- 相關推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