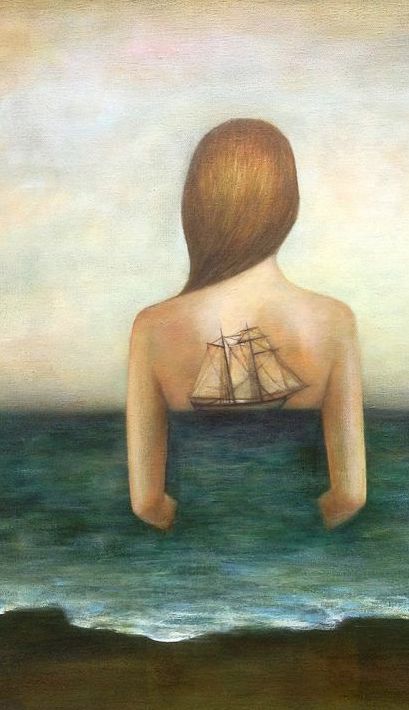
错置。游荡。务虚。
影像世界之真實:延伸蘇珊桑塔格「論攝影」(三)
一張照片是一個故事,觀看一張照片分享了一個在地的二手經驗。然而蘇珊桑塔格不曾親歷數碼照片的時代。今天的人還得考慮的一點是影像不僅是二手經驗的載體,還是原先載體的數碼複製品。
假設以每個人的手機屏幕——手機屏幕很重要,想像不同型號和版本的手機大小,色差,甚至是久了不同主人磨損出的裂痕吧,這些都是看照片的「周遭」——為單位給一張數碼照片標號,複製品的號碼是難以窮盡的。本雅明認為機械複製即是「把原件的複製本放置在原件本身遙不可及的環境中。」但這句話產生於膠片拍攝出的照片被印刷在紙媒上的時代。今天的情況已經不再是(相機中的)原件與其複製品(印刷的照片之照片)的關係,而是(發佈在社交媒體上的/ 打水印的)複製品與其(二次傳播/ 截圖/ 觀影時屏攝)孿生復製品們的關係。如此,二手經驗被進一步稀釋成三手,四手,直至完全剝離語境。
// 屏攝指在觀看院線電影時用手機拍攝熒幕上的電影畫面。如果留心「少年的你」院線場,或許你能從後排看到前排高高舉起,對準某一演員的手機攝像頭。
今日的世界是影像的世界。然而從充沛的影像裡回到未經調味的現實時,人覺得嘴裡寡淡。一方面,現實不如影像激動人心。這反過來激勵我們在每一個「可拍攝」的時刻留下影像,佐證自己的生活並非乏善可陳。另一方面,影像給予一種虛幻的精神飽腹感。這即是蘇珊桑塔格在憂傷的物件一章中說的「攝影那超流動的凝視使觀者感到愜意,創造一種虛假的無所不在之感,一種欺騙性的見多識廣。」我們已然「見過」富士山峰,看過「非洲大草原」,瀏覽過「貧民窟人的生活境況」,但不曾目睹。
相反,新的無信仰時代加強了對影像的效忠。原本已不再相信以影像的形式來理解現實,現在卻相信把現實理解為即是影像。費爾巴哈在其《基督教的本質》第二版( 1843)前言中談到“我們的時代”時說,它“重影像而輕實在,重副本而輕原件,重表現而輕現實,重外表而輕本質”——同時卻又意識到正在這樣做。
——蘇珊桑塔格
歌頌攝影,尤其手機攝影,是歌頌人人皆有創造影像之權力的民主。傳統美術裡,「有些表現對像被認為是重要、深刻、高貴的,另一些是不重要、瑣碎、卑劣的。」攝影將整個世界,連同它的乏味尷尬腐壞醜陋,作為素材,推上舞台。那些不忍畫下的景象,就讓相機(手機攝像頭)完成。而無論按下快門有多麼輕巧,攝影不可避免地是從某雙眼睛望出去的景象。一張照片讓人對攝影者所處的位置浮想聯翩,因為攝影必須有一雙主體的眼睛。鏡頭替人觀看。
這看似對動態攝影是一樣的。紀錄片和電影的影像也存在一個隱沒在鏡頭後的主體。對紀錄片來說這個主體常常就是攝影師本人,偶爾是被拍攝對象。電影則有更多可能性,通常是虛構的人物,有時是監控攝像頭,還有時是詭秘的幽靈(壁櫥縫隙中,天花板上,下水溝裡——各種人不去的位置);試圖打破次元壁的電影則把主體放做導演本人。影像的主體譬如是受欺負的小男孩,大概會引起觀者的同情;如果主體視角突然切換到瘋子,鬼魂或者突然跳出次元壁的導演之類,則是個對無法代入主體的觀者的一次提醒,造成出離或戲劇感。
動態影像的創造者對她們的作品有極大的掌控力:在既定的幾個小時裡,你的視角受攝像頭的擺佈。靜態影像則不同。這是由於單張影像缺乏語境,也無法對觀者形成控制——同讀書那樣,我們能控制盯著一張照片多久,又怎麼盯著它。
此外,數碼照片可被直接保存截屏屏攝,這類進一步將一張照片拽離它本身的語境的動作讓觀者也能輕易修改並再次發布影像,在復刻的動作中成為詮釋者之一。有時傳播者帶著無辜的意圖,有時卻可能意在創造奇觀,引發騷動。總之,影像被再創造,再限制,再篡改的同時,其真實性也落入一個謎團。
——也落入了福柯定義的權利網絡:「權力以網絡的形式運作在這個網上,個人不僅流動著,而且他們總是既處於服從的地位又同時運用權力。」在人與人的網絡中,人人是媒體,人人定義其影像;經驗被複製,被再創造。
照片並非只是記錄現實,而是已成為事物如何呈現在我們面前的準則,從而改變了現實這一概念,也改變了現實主義者一概念。
——蘇珊桑塔格
相機捕捉一隻飛鳥的動作十分短暫,但已經在飛鳥的影像與飛鳥之間創造了一道不可見的物理關係:飛鳥的影像具有索引(indexicality)性,令人索引到鳥本身。一種Truth Claim 就伴隨攝影誕生了,這種信念認為傳統攝影總忠實刻畫真實(reality)。事實上,攝影一度成為形容某事「精確真實」的修辭。 (否則『實物不符圖片』時,我們也不會這麼憤怒。)攝影,本是薄切的生鮮現實。
對攝影的信任也傳遞到動態影像裡。電影有個古老的名字:動態圖片(motion pictures)。如果說靜態圖片僅僅捕捉一個同時孕育過去未來的時刻,電影真正捕捉過去與未來。 Lev Manovich 稱之索引的藝術(art of the index)。遇見罕見的奇觀——一幕落日,一次別離,一場地震——感嘆之餘,人人喃喃「簡直和電影一樣」。
不過,今天我們默認攝影與電影不真實的時候更普遍,而這不僅僅是說後期用技術處理過的攝影和電影。這是因為「生命不是關於一些意味深長的細節,被一道閃光照亮,永遠地凝固。」照片卻是。影像通過摒除人在場時感官接收到的雜音,重新表徵一層真實。這個摒除可以通過十分簡易的環節完成:取景,旋轉裁切,調色,甚至是抹除。
而得益於技術進步與商業浪潮,雜音不僅是能被抹除,而且是「一鍵抹除。」照片後期軟件不僅簡化這些環節,而且標準化自動化它們。拍甜品有專門的色調;夏天有自己的濾鏡;拍攝自然風光和人像需要的氛圍感也都被精心營造;還有齊齊消失的面部斑點和皺紋。不僅是照片後期軟件,照片呈現的媒介也大力推動這一標準過程——每張16:9, 2:3, 3:4, 5:4規格的照片都被平等地分配進1:1的模具中,成為2x2, 或3x3的格子之一。
//有標準化,就有有心的創作者極力擺脫這一標準:給橫幅照片加上上下白邊,豎幅加上左右白邊以控制照片在流媒體上的呈現如她所願。
在傳統美術裡,無數筆觸疊加下顏料能順著力道拱起又落下,形成可觸摸的紋路;或是難以蓋嚴實的塗錯的棕褐色丙烯,在一次次鮮紅和米白的混合下,漸漸將後者化作低飽和的灰粉。揣測一幅畫的原初形態很難,但並非不可能。攝影下的影像呢?膠片的加工或許可以,而數碼照片被塗抹了多少層「真實」是不可眼見的。
如今面對照片,我們已經不能確定它的本體,它的源頭,以及它的塗層數量。唯一警醒感官的是直覺,一種隱隱作響在心頭的不真實感:
我所看到的是真實嗎。
“誰告訴你的?”
卡夫卡把頭歪向肩膀。
“攝影把你的眼光集中在表面的東西上。因此,它遮掩了那隱藏的生命,那生命像光和影的運動那樣閃爍著穿過事物的輪廓。你哪怕用最敏感的鏡頭也捕捉不到它。你得靠感覺去把握它……這部自動相機不會增加人的眼睛,而只是提供一種奇怪地簡化的蒼蠅的眼光。”
——古斯塔夫·亞瑙赫,《卡夫卡談話錄》
喜歡我的文章嗎?
別忘了給點支持與讚賞,讓我知道創作的路上有你陪伴。
發布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