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原生家庭 | 在家族历史中重新看到自己与社会
医学人类学家凯博文曾在中国进行“神经衰弱”的研究。1980年代,凯博文作为第一批来到中国的研究者,见证了中国人在集体创伤后用头疼、疲惫等躯体形式所表达的苦难。在精神分析的术语下,这被称之为“躯体化”,一种“原始”的心理防御机制。加之对政治语境的分析,许多学者都认为,这源于被压抑在潜意识中的焦虑和恐惧。诉说那些被称作神经衰弱的症状,才是安全的。
而在那项经典研究的二十年后,凯博文在接受拜访的时候谈到,他并不认为当年的一切应该被病理化。甚至说,在当今世界,这些都弥足珍贵。他认为,一个中国的妈妈不会像美国人那样在嘴上说“我爱你”,却会在给你准备的吃食、为了奔波的事情里表达她的爱意。这是中国社会的美德,与过度心理学化、过度个人主义的世界产生了鲜明的对比(Shayla Love,Science and Chinese Somatization)。这样的说法稍有些“东方主义”的色彩,也就是将东方作为一种理想的对照物。但不失为对个体心理学解释过度泛滥的一种反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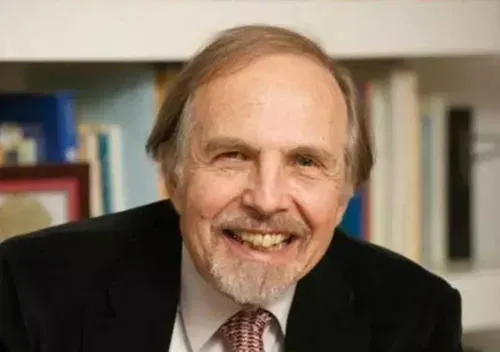
本文会从原生家庭说开去,谈谈集体创伤和代际创伤,在其中穿插解放心理学、社区心理学等尝试突破传统心理学局限的理念与实践。最后我会介绍夏林清的“斗室星空”方法,作为一种连接个人、家庭生命经验与社会、历史经验的路径。
原生家庭的滥觞
“原生家庭”这个术语俨然成为了大众话语的组成部分,对于自身的苦痛和局限,原生家庭给到了几乎无所不包的解释。不可否认,原生家庭作为个人早期社会化的空间,对一个人的社交技能、解释风格等等有非常深刻的影响。但是,“原生家庭”一词的滥觞恰是过度心理学化的表征,单紧抓着原生家庭一词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
- 我们到底多大程度被所谓的原生家庭所限制?从另一方面来讲,我们能多大程度上突破原生家庭的限制呢?
- 原生家庭除却会带来局限和创痛,还给我们了哪些财富?会不会“父母皆祸害”的口号阻碍我们看到家庭经验的全貌?
- 原生家庭一定程度上让我们了解了自己,可是这个概括性的词能否帮助到我们认识原生家庭本身?原生家庭又是如何被形塑的呢?
- 原生家庭相伴的话语几乎全部解释了我们的由来,可是在家庭之外,我们所处的时代、城市、学校对自己的影响作用到了哪里?
中文的“问题”一词非常丰富。正好表达了这些是需要我们去探索的问题(questions),也是需要我们去解决的问题(problems)。那么,为了丰富“原生家庭”的话语,我在这里介绍两个词:集体创伤(collective trauma)和代际创伤(transgenerational trauma)。
集体创伤
集体创伤常常发生在大屠杀、恐怖袭击还有其它灾难之后。但集体创伤并不仅仅体现为对危机的反应,长期制度性的压迫同样也会招致集体创伤,譬如美国的奴隶制、欧洲对犹太人的系统性排斥等等。
很类似许多孩子在一个糟糕的成长环境中并不会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而是会出现发展性创伤(developmental trauma)那样。许多集体创伤的亲历者也不会有PTSD的问题,创伤事件与压迫给他们带来了更微妙的影响。
在《物尽其用》一书中,有一个很好的例子。1953年,赵湘源的父亲被送入大牢。父亲被带走的那一年,她才刚刚15岁。失去了家里的经济来源,她和她的母亲“居住面积从40平方米变成了14平方米”,“湘源知道了生活的艰难和贫困的涵义。……这种挣扎中训练出来的节俭随即成为湘源一生的习惯,即便当她的生活条件最终得到了改善,她仍然不断地堆积布头和布块。”(巫鸿,“治疗的记忆”,《物尽其用》)
湘源在那个物质缺乏、充满不确定的年代中成长起来,又遭遇他父亲入狱的切实影响,非常自然地就有了在我们看来过于节俭的生活习惯。许多人家里的老人家都非常节俭,我们都非常难以理解,我想这就是时代与家庭给他们留下的烙印。
我个人也受益于这样的洞察。我本科时借着口述史还有生命故事课程的机会,为我的爷爷整理了他写的回忆录及家史。而在去年底参加的创伤知情课程上,我又重新挖掘了这份宝贵的材料。就拿一个直观的例子来说,我爷爷在我小时候抽烟抽得异常厉害,而这个习惯源于1967年,他当时被安排到大旅社里与其它被斥为“走资派”的人同住,成日写着检查,苦闷异常,这才开始有了抽烟的习惯。
我们对创伤做出的回应都是一种“求生存”的行为,需要被放到当时的社会历史脉络中去理解。而这种“求生存”的行为在时过境迁之后,渐渐失去了它的适应性,但还是保持着它的惯性。故而我们常常将其视作一种病态,但这样的观点也是片面的。就好像我们每个人的性格一样,很难说我们性格的每个面向都能够转化为优势,但这些棱角便组成了我们的棱角。即便是“无用”的部分,它也体现了我们独一无二的存在、体现了我们所珍视的价值。湘源囤积东西的原因在一开始是对未来生活的担忧。她从1960年代便开始储存肥皂,有些同事洗衣服少,用不了太多肥皂,便把购物本给她用。她怕自己的孩子长大以后像自己一样每个月为肥皂发愁,就买了肥皂存起来,想留到孩子结婚时给到他们。如此求生存的行为体现了母亲深深的爱。随着时间的推移,没想到她的孩子已经用不到了,可她还是保留着它们,因为它们所含有的感情价值。

需要强调的是,集体创伤超越了临床的观点,它暗示着社会、社区的问题如若没有解决,创伤会不断地发生。面对集体创伤不仅需要对个体心理的关怀,还需要集体的行动。弗朗茨·法农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便发现,只要战争的恐怖还在无止境地延续,对阿尔及利亚人的临床治疗就几乎是无效的。因此他强调创伤的社会根源,并投身到了解放运动中去。他还鼓励被压迫者团结起来,以抗争来应对创伤。
对于这个部分,解放心理学是一个很棒的理论资源。他们认为,心理学家的角色应当是在被压迫者解放、变革的历程中陪伴和协助他们。具体还可以看看去年我翻译的这篇“解放心理学与行动研究”。批判取向的社区心理学与解放心理学一道,将社区与社会作为干预的对象,也突破了个体心理学的局限,想要了解更多,可以阅读我摘录的这篇“社区心理学与解放心理学”。
代际创伤
集体创伤和代际创伤呈现了一个完整的链条。假如问题从原生家庭中来,那么家庭的问题从何而来呢?第一代的家庭成员作为集体创伤的亲历者,又将苦难以代际创伤的方式传递到了后代。
代际创伤的发现源于对大屠杀幸存者子女的治疗。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大屠杀幸存者孙辈被转诊到精神科的比例是对应人口组的三倍。对犹太族裔大屠杀幸存者的研究则得出了一个对中国人来说非常熟悉的假设,受到创伤的父母由于没有经历对创伤的完整哀悼,他们会将对孩子的高度期待作为自我的组成部分。很大程度上,这是父母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与自己有同样的缺失。对红色高棉屠杀幸存者的研究则看到,来自柬埔寨的难民拒绝谈论他们的创伤,孩子会在这种家庭环境中习得沉默以及对求助的拒绝。
弗莱雷在他的《被压迫者教育学》中,提出了一个简明概要的词——“双重人格性”。被压迫者在苦难中挣扎,在不知不觉中,又或者格外地希望成为压迫者。压迫在这个过程中再生产了。俗话说,“媳妇熬成婆”,假如这是一个所谓“恶婆婆”的生产过程,便体现了“双重人格性”。内里的机制是女性遭到婆婆作为父权制代言人的压迫,在这种权力关系下,被压迫者内化了对方传递的信息。在极端的情况下,在她熬成婆的时候,便是成为压迫者的时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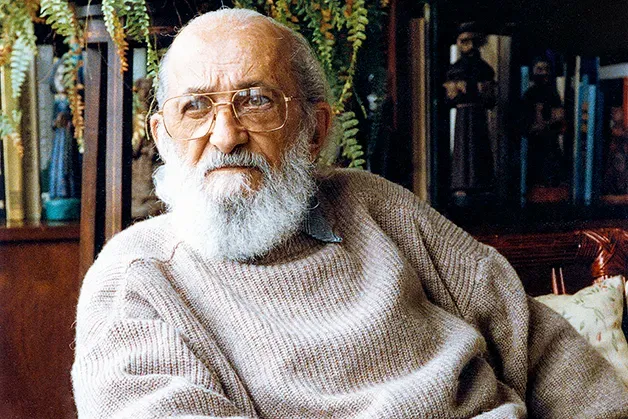
从后现代的视角来看代际创伤时,我们能够转化或是丰富“家长作为加害者/压迫者”的观念。就好像过度地希望自己孩子成才一样,他们带来的压迫源于他们的缺失。而这里边虽然有着非人性的部分,但这里边同时也有着深沉的爱意。当然,理解并不意味着认同。如何让彼此从压迫中解放出来,才是重点。
在中国,“传宗接代”是父权制压迫的“理论基础”。在梁军老师的文章中,我看到在一场参与式培训班上,带领者先是问了“传什么、传给谁”,又问了“对‘传者’有什么好处”,最后在大家猝不及防间问说“对‘传者’有什么坏处”,“像是一下子触到参与者的痛楚,当时就像是‘炸了锅’,他们讲述了生活中的大量事例,颇有‘悲愤填膺’之感,把刚刚还在津津乐道的‘传宗接代的好处’推向了另一个极端。”(梁军,《悄然而深刻的变革》,收录于《行动研究与社会工作》)这种对话实践带来的变化,被弗莱雷称作“意识觉醒”。是一个明确自己受到压迫,看到压迫根源的重要时刻。
另一方面,我们不仅传承了创伤,我们也传承了智慧与韧性。集体叙事实践和社区弹性模型都看到的创伤的另一面,我们的韧性和抗逆力(Resilience)。
“在2013年波士顿马拉松爆炸事件发生后,我乘飞机到了波士顿,与一群人道主义救援人员一起工作。……简单介绍寒暄以后,我们开始询问他们一个‘开放式’的问题,鼓励他们表达头脑里所想的东西,一些人开口谈论,因各种原因,他们害怕和愤怒的情绪有所增加。于是我把话题转到了心理弹性问题上。我问他们:‘你们是怎么克服这个困难的?现在有什么可以帮助恢复波士顿?’令人温暖的反馈如溪流源源流出,如邻居的慷慨、宗教信仰、深远的爱以及对波士顿人精神的赞美等。”(伊莲·米勒-卡勒斯,“第七章 社区心理弹性模型(CRM)”,《重建应对创伤的心理弹性》)
每每有灾难与创伤,便有抗争与疗愈。以叙事的话来说,我们要做到双重倾听(double listening),既听见我们已经组织出来的故事,也要听见不被我们重视的“支线故事”。在创伤的故事下,也有我们如何坚持着走到如今的故事。
关于集体叙事实践,可以看我之前写的这篇“人类学+社区工作+心理咨询=集体叙事实践”。还有歌子从藏传佛教的角度聊传承加持的文章——“从代际创伤视角理解藏传佛教的传承加持”。
家的社会田野
香港中文大学的黄宣颖教授指出了当代中国的“心理热”(psycho-boom)现象,尤其是在新一代的中产阶级中,身心疗愈和个人成长尤为盛行。而台湾辅仁大学的夏林清教授却要与心理治疗师的角色做切割,立志作为社会教育工作者。以心理剧为例,她看到了它去脉络化、商品化趋势,指出要回归莫雷诺原初的意涵,将心理剧作为“一种推进社会实验的的行动探测方法”。夏林清拒绝把病历与社会问题化的标签简单地贴在个人与婚姻家庭经验上,而是以说故事的经验学习方式,让同学的家庭与生命经验能被看见。(夏林清,“第八章 斗室星空~家庭经验晒谷场”,《斗室星空》)这个过程中,便发现家庭关系是“社会关系作用力量的载体”。
不论是两岸关系,历史事件中夫妻分居,还是说父母作为工人的生命历程,都不可避免地形塑了台湾家庭独有的面貌,这样社会历史动力“转置”到家庭当中,亦对台湾青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大陆同样如此,倘若这些社会历史文化的大变革,作用到家庭当中,只是被轻描淡写地被概括成“原生家庭问题”,我们能够理解到的实在太少。
即便是代际创伤,也只是家庭历史的一个面向。格尔茨在《仪式的变化与社会的变迁:一个爪哇的实例》一文中讲述了一个葬礼的生动例子,显示出了家庭在文化与政治下所遭遇的割裂。
在当时的爪哇,玛斯尤米是以伊斯兰教为基础的政党,而波迈是一个坚决反对穆斯林的团体。卡曼是一个积极的波迈成员,他的外甥派贾恩在他那里突然过世。传统的爪哇葬礼因为宗教融合,有浓浓的伊斯兰教特色,所以举行非伊斯兰教的葬礼实际不可能。可负责葬礼的莫丁则被玛斯尤米领导人要求,不准参加波迈成员的葬礼。没有宗教人士的参与, 派贾恩的葬礼仪式没有办法进行下去。在勉强的行进过程中,死者的姨妈崩溃大哭。这在爪哇的葬礼中是极为罕见的情况,对哀悼者来说,他们在葬礼中要产生的是一种超脱的“不在乎”状态。这也让其他参与葬礼的人格外焦虑。在之后的葬礼中还出现了许多冲突,使得家庭关系格外紧张。卡曼的妻子三个月之后都还没有缓过来。
在对我家史的不断重读当中,以及对家里人的追问里,我也得以从家庭经验中重新理解生养我的小小场域承载了多少沉重的东西。就拿我爷爷对我的放心不下来说,他从小就希望我待在他身边,对我现在成人要到其它城市而感到异常难过。这些感情都是非常厚重的。
我爷爷在那个年代里,到市里工作,孩子都交由她的母亲在农村里抚养。每周末才能踩着自行车回来看看自己的孩子。在六十年代的经历里,更是担心自己连累家人。而我大伯当时还偷偷给我爷爷送来地瓜,他被造反派发现,却没有被吓到,还是把地瓜送到了我爷爷手里。我爷爷写到,“看到天真可爱的孩子,而我又不能与儿子在一起,感到很痛心。”所以,能够陪伴在我身边,看着我长大,对他来说是多么大的安慰啊。
斗室星空不止是回看自己的家庭历史,还是在彼此参看中重新理解自己的经验。
创伤知情的课上,我就有幸在一个安全的空间里得到彼此见证的机会。京文在一次课上聊到了自己的爷爷,说他爷爷在他动身去美国之后说自己可能再看不到他了。京文安慰爷爷说,只是过去一个月,回来还能再看到的。却没料想到因为疫情航班取消。回来时已经和爷爷天人永隔了。说到一半,京文已经泣不成声,我也忍不住鼻头发酸、眼眶湿润。我突然真正理解了我爷爷每次跟我道别时的难过。因为我一直觉得我爷爷身体非常健朗,他却担心自己不知道哪天会走掉。可能我们就此一别,便是此生最后一面。
虽然做得还不够多、不够好,但我还是开始试着更多在他身边,去听那些我不曾听过的故事。
参考文献
巫鸿,《物尽其用:老百姓的当代艺术》,上海人民出版社
伊莲·米勒-卡勒斯,《重建应对创伤的心理弹性:创伤与社区弹性模型》,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译林出版社
杨静,夏林清等,《行动研究与社会工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夏林清,《斗室星空:家的社會田野》,財團法人導航基金會
夏林清,《斗室星空:“家”的社会田野》,《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https://www.psychspace.com/psych/view
YoviaXU,中国普遍存在「代际创伤」吗?产生的原因是什么?的回答,知乎,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2084237/answer/63662711
Shayla Love, Science and Chinese Somatization, https://undark.org/2017/10/02/science-chinese-somatization/ (译文见:曾经中国没有抑郁症|文化如何影响自我感知)
Wikipedia, transgenerational traum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ransgenerational_trauma
Wikipedia, collective traum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ollective_trauma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