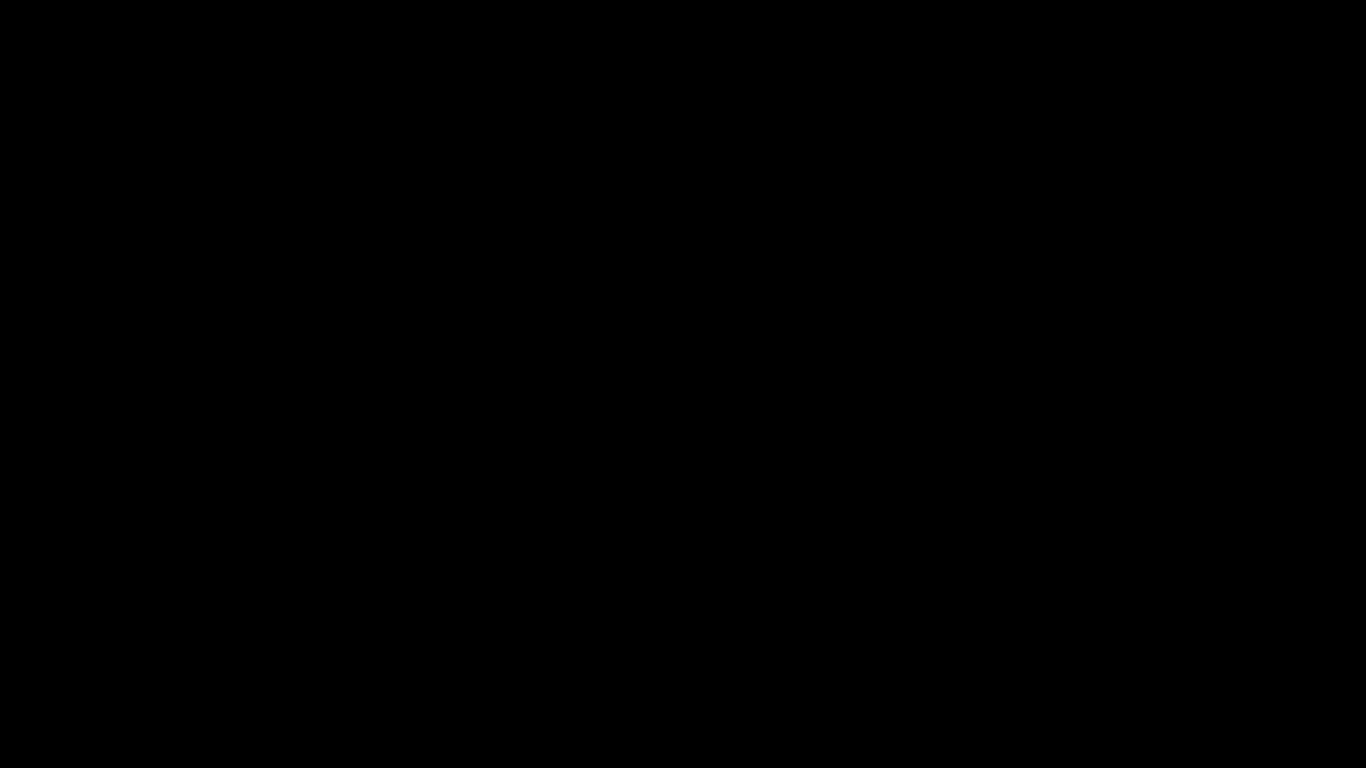二〇二〇年三月杂谈三则
本文原载 telegra.ph 于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七日。原文轉爲簡體。
(一)
每个人都「只想管好自己的事情」,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和被灌输的事情比起来动手和动脑学到的事情几乎没有。连感觉和想象都被为吸引注意力无所不用其极的短视频应用和规定了每篇必须有一张图片的微信公众号文章碾碎而不自知。
他们生产的也是这种东西,不易被保存的、不易传播的、绝大部分都是冗余的的、高度重复和滥用的、不尊重原创的、没有个人意志介入的发在不能登录就无法使用的、在特定时间或者任何时间不能说特定但又没有明确的话的网站上的信息。
嬉皮笑脸的、幼稚的、无知的、反智的、一锤定音的、一笑置之的、不鼓励你深究的。「杠精」、「认真你就输了」被他们挂在嘴边。他们似乎比任何人都懂什么叫表达。
再怎么严肃的东西都能拿来俗用,什么样的悲情都能拿来调侃。不会共情,没有感动。他们有一些值得拼上性命去保护的东西吗?也许有。即使那不是什么俗不可耐的玩意儿,你也从他们的脸上看不出什么。
规定永远是最尊贵的、凌驾于人之上的东西。「坚决彻底」、「毫不留情」、「坚定不移」、「重拳打击」。
「该干什么干什么」是他们的格言。效率和方便即是无上追求。他们会有一天摸到到这牢狱的墙角吗?站在、或者跪在那里向上看,他们究竟会看到什么?
甚至只有那些和身体感官联系紧密的艺术才有被他们当成茶余饭后谈资的资格,那些感官带来的好像还必须是「积极正面」的感受,「真善美」是他们评论艺术的三字经。当然,「真」其实排在最后,「美」也和美学无关。
被教会了太多周围是什么样子,如何才能在这个社会上生存下去,如何才能将自身利益最大化。精明得不像人类。不愿意相信有他人为了利益之外的目的来行动,于是自己也成了那样的人。
「听话,这是为你好。」是他们诉诸感情的逻辑谬误的根源。「学习是为了找个好工作,能挣更多钱出人头地。」扼杀了所有好奇。「超纲」的问题的问题不要问,「和学习无关的事情」不要想。
给自己的人生赋予意义这样复杂的事情不要做为好,那样就会轻松一点。从此以后我说什么就是什么,不要听别人怎么说,想听你也听不懂的。总之放弃思考,然后为我效劳吧,你们是我指哪打哪、任劳任怨的棋子。
(二)
可能是小学,大概是初中,我有一个用来收集什么的纸箱子。收集我认为值得留作纪念的玩意儿。我可能有收藏癖,这个定义对那时的我实在是宽广,所以那箱子里什么都有,几乎是个垃圾场,但我视其中的每一件为宝物。
里面有一些谁赠与的、甚至是自己购入的、通过一些特殊事件来被我赋予意义的摆在桌子上用的玩物。碎掉了的、内容物泄漏出来的什么,让我用纸包起来,有时粘上透明胶带,或者写上几个字。在什么地方和谁做了什么事情后,用剩下的什么东西,让我拿回家,用纸包起来放进箱子里。同学之间传的纸条、家人留的字条。最终那个箱子里都塞得满满的,几乎快不能塞进床下了。
至于箱子里有什么,经历了从高三到大四暗黑的四年的我已经完全无从想起其中任意一样。现在动起笔来写那时候的事情也是因为自己最近又通过回忆找回了那时候的一些什么的碎片,一些当时被我和母上称为「多愁善感」的感情。现在是对于试图留存这一行为的失望。
就现在——2020 年 2 月 29 日,几乎每四年才一次的日期——我仍然会被 CLANNAD 里被烧掉的信件和书籍和村上春樹『風の歌を聴け』里我再也没有见过左手只有四根手指的女孩子(左手の指が4本しかない女の子に、僕は二度と会えなかった。)的描述所打动。我不知道它们还能打动我多久。
我那时似乎常常伤心地哭。哭一些事情再也没有办法复原,哭一些事情不会再发生第二次。具体是什么事情也不太能记得了。我想我的大学给我的伤害已经是无法复原的了。大二的我若懂得从一些事情中积极地逃避,恐怕也不会造成今天这个结果。但是,那一年——或者过去的每一年——我的出來事(できこと)已经称为了「我」的一部分,没有任何一件事我都不会今天坐在电脑前写这些。但我也可以说「其中一些事情若没有发生的话,结果可能会更好」。这种把特定的什么事情从当时的所有事情中抽出来的讨论曾让我痛苦,以后大概也会让我痛苦。每一件我后悔的事情,后面都跟着一个自己现在的人格成立的重要时期。这个循环使得讨论没办法太简单。也让我看问题更加悲观和破罐子破摔。
想过死,当然了。但不如说是对死前自己究竟能产生什么样的感受,回忆起什么样的事情,接下来又会做出什么样的决定。死是人能做出的最后一个决定,但有些人到死也没做个这个决定。
也就是说,我对死的妄想其实是对获得了另一双眼睛的自己看目前(これまで)的人生的想法的好奇,以及对未知人类情感的体验的好奇。好奇心支撑着我活下去。
我们说「什么什么不是人生的全部」,但我要说人生的全部(each)不都是人生的全部(all)吗?
我可能在等一个出会い等得太久。
(三)*
最近开始意识到自己和身边有相同成长环境的人之间思想差异的原因可能和小时候就知道要反抗有关。在我在浑浑噩噩的忘掉它们(或许实际上已经忘掉不少了。)之前,在这里写一些能写的。
小学时,班主任教语文。而所有科目中我最讨厌语文。不知道有没有什么老师能把语文课讲得让当时的自己喜欢,我也不知道那时自己有没有这个问题的答案。总之我相当讨厌他,但原因不只是他的课。
此人喜欢配合漂亮但呆板的楷体板书在上课时间训导学生,制定想制定的一切规则来管理他想管的一切。有次他神经质地说了些什么后被我们误解,过几天又横眉竖目地站在讲台上教我们「自讽」这个概念——当然——配合那似乎用全身力气刻在黑板上的那两个大字。用黑板擦清理恐怕都要多用点力气才行。
原因忘记了,但我有一次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把语文课本拍在桌子上后站起来和他对峙。似乎我对高中班主任也干过一样的事情,除了把语文课本换成了手掌。
此人以磨除学生个性为乐,条条框框数不胜数。有次语文作业的填空题,可能是出于对自己的答案非常自信,我把答案写得很大,虽比应该在横线上的文字的正常大小大了三倍,但卷面毫无乱象,答案亦一目了然。我极其清楚地记得此人课中在黑板上用巨大的字写了我的答案作反面教材以痛批。「这老师不行」,我清楚地记得讲台下的自己当时这样失望地想过。
不行的事情还在后面,我因为需要测量物理实验中一些电子元器件的温度,托父上买了一支电子激光测温枪给我,还是高级的外国货。价格问了父上,被蒙混过去了,因而想必很贵。此人后来通过母上借走了它。怎么想都觉得奇怪,小学语文老师要激光测温枪好干什么?更奇怪的是,那时还不流行微信,小学语文老师怎么知道我们家有,就算知道,来找学生家长借这种无关紧要的东西算什么?不过当然,如果只是这种程度的事情也不会怎么就「不行」了的。他把它弄丢了,连同他的公文包一起。我没有收到赔偿,没有听到他表示丝毫的歉意。「老师也丢了不少钱,赔偿就算了吧。」,母上对我说。这话从未使我信服。她这么说(但不一定这么想)可以理解,但你是什么?强盗吗?
小学时另一个班主任虽更令人生厌,但关于她的回忆也几乎只有因我把同学的书本扔进水里而被用素手暴打天灵盖的激痛了。因其包括各种体罚措施在内的暴政,我经常用各种自创的方法诅咒她。
我以数学满分,语文 65 分的成绩顺利进入小学初中一贯的以校风闻名全市的学校的初中部。该校规定「男生一律留平头」。关于女生发型的部分忘记了。我没有一刻停止过质疑这规定的合理性,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用实践来反抗。奇怪的是我现在不记得我在无数次被「办公室喝茶」和「叫家长」时自己用了什么说辞。也许那时只是闭口不言,才有在办公室连罚站四节课站到放学的经历吧。有次和其他用实践来反抗的同学一起到学校附近的理发店
* 未完。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