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曾經在這裡:讀Emily Wanderer 《害蟲的生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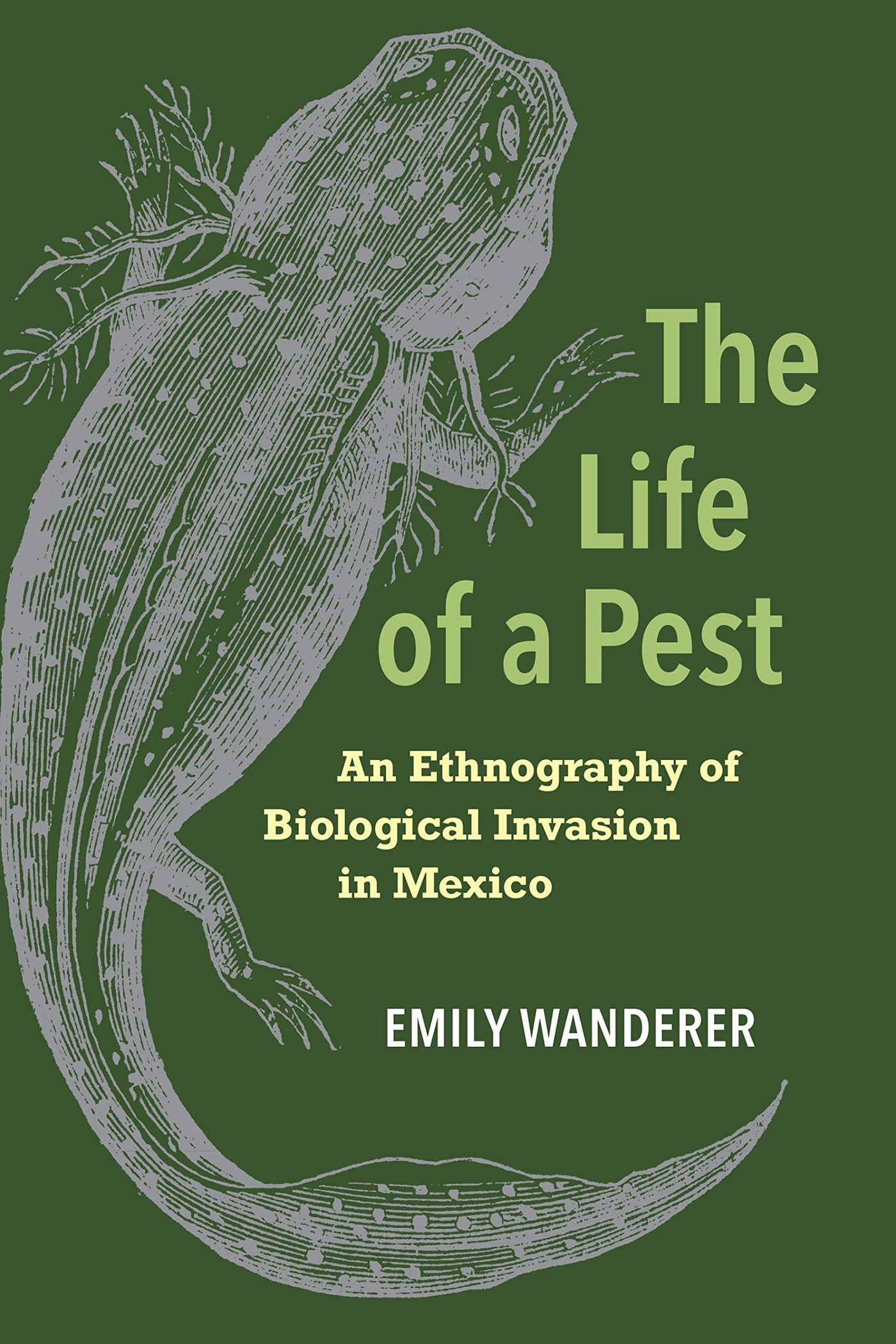
Emily Wanderer, 2020, The Life of a Pest: An Ethnography of Biological Invasion in Mexico.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我們在這裡,我們曾經在這裡;我們就是這樣,我們曾經是這樣。」──愛德華多.加萊亞諾
《害蟲的生命》一書封面很簡單,軍綠色背景上印著大大一隻猶如異星生物的蠑螈圖樣,配上副標「有關墨西哥生物入侵的一本民族誌」,很容易讓人以為作者要講的是這種生物大舉侵入墨西哥的攻防故事。不過這完全是誤導:這本書並未聚焦在單一外來種(事件)的討論;更何況,封面的蠑螈也不是外來種,而是如今備受科學家關注、瀕臨滅絕的墨西哥鈍口螈(Axolotl),用通俗的說法,身世血統純得不能再純了。
雖然不是「害蟲」,不過被作為全書結尾的墨西哥鈍口螈或許最適合幫助我們快速理解這本民族誌的主軸。墨西哥鈍口螈是墨西哥特有種的兩棲類生物,主要棲息在墨西哥南部的一座古城霍奇米爾科(Xochimilco)。這座城市裡留有阿茲提克人所建的運河遺址,水道縱橫,串連起周圍的人工島,成為特殊的溼地生態區。

墨西哥鈍口螈和牠的棲地,反映的正是人類與自然的相互糾纏。一方面,複雜的運河與人造的島嶼,都是在農耕需求下經由大型水利工程打造出來的產物;但也正因為人類的這些活動,同時造就了適合墨西哥鈍口螈生長的棲地。另一方面,墨西哥鈍口螈獨特的幼態延續特徵也顯示了人造環境的影響。相較於普遍的兩棲類,墨西哥鈍口螈並不會經歷變態的過程,終其一生都用鰓呼吸。這樣演化的分歧關鍵,也在運河提供了墨西哥鈍口螈持續的水生空間,讓牠無需像其他蠑螈一樣需要轉變自己的身體(成熟時由鰓改為肺呼吸)來適應多變的環境。
透過墨西哥鈍口螈,人類學家要強調的是自然保育和人文活動的難以切割。Wanderer指出,當過往西方持續將文明與自然區分開來,想像一個「原始」、「未受開墾」的自然時;我們在墨西哥所能看見的卻是完全相反的圖像。墨西哥鈍口螈生長與演化過程始終與人類開發自然的過程緊密連結,牠是人類的農業與運河所孕育出的墨西哥特有種生物。如今在政府的計畫裡,保育墨西哥鈍口螈也不只是保護棲地「不受破壞」;而是要重建人與墨西哥鈍口螈的共生關係──正如過往工業發展之前,人們在小規模農耕生活裡創造出合宜墨西哥鈍口螈生活的居所那樣。
Wanderer更進一步告訴我們,當墨西哥政府喊出「更好的生活」口號,將「保育墨西哥鈍口螈」、「維護墨西哥的多元生態系」、「打造人與自然共榮的生活」畫上等號,試圖勾勒一幅美好墨西哥的藍圖時,這項保育計畫也擴寫了傅柯所講的生命政治。從「人類」之生延展到整體生態界的繁榮,權力的治理不再只是透過人口統計等技術掌控國民的生與死,而是整個生態系──從人類、動物、植物、甚至到我們肉眼不可見的微生物,彼此糾纏影響,被牢牢串連與控管。終於,生命政治升級成新.生命政治。
簡單地說,《害蟲的生命》要講的重點就是這樣兩項:自然生態與人文活動的難以切割,以及新型態且更加無遠弗屆的生命政治。在這樣的基底上,Wanderer考察了各種科學研究與保育計畫,從不同的「入侵」情境裡看見當代墨西哥科學家如何讓自己的計畫(未必有意識地)與一套國族想像與治理綁定。
例如開場,Wanderer先帶領讀者抵達墨西哥西邊的偏遠離島瓜達盧普(Guadalupe),參與了當地的羊群撲殺計畫。這群山羊原本是作為食糧資源被刻意帶到島上,隨後卻開始氾濫成災,幾乎啃食了島上所有的植被,隨後被墨西哥政府認定是有害的「侵入種」,開始實施撲殺計畫。Wanderer先回顧了山羊與當地島民的互動歷史,再提醒我們看見山羊怎麼在新的政府藍圖裡從原先的資源轉為危害「墨西哥本地」生態的害蟲。在此,「為了墨西哥好」,當地生物被快速劃分成應當要活與應當要死;而在主打著「必須保護墨西哥生態系」的時候,政府對領地生命的管制從人類延伸到山羊與植被。這正是Wanderer反覆強調的,不再侷限於人類的生命政治。
又像是另外一章,Wanderer帶我們來到墨西哥的傳染性疾病研究中心,聽科學家們說明墨西哥人的基因與外來流行病的關聯。以HIV病毒傳染為例,HIV病毒有許多變種,世界各地的病患未必同享相同的病毒株。Wanderer指出,當科學家們強調墨西哥人(由於族群歷史以及生活環境)獨特的基因庫使得感染的HIV病毒變種往往不同於其他地方時,他們也強化了疾病入侵與國族之間的連結。於是,整個國家在科學家的顯微鏡下成為一個群體,必須特別防範特定病毒的入侵。
Wanderer野心勃勃,從動物、植物到微生物的入侵,書寫的範圍極廣極遠。然而讀到最後,我也忍不住想,Wanderer似乎衝得有點太過猛烈。像是在瓜達盧普島的羊群撲殺計畫章節,Wanderer也還談到羊群和當地執行滅絕計畫的科學家間的複雜情感關係,描述科學家們如何在日常的生態觀察與研究中深刻認識研究對象(準備要被撲殺的羊),並產生特殊的親密感。而在全書最後一章,Wanderer聚焦於墨西哥政府對基因改造作物的管制模式,並花了大量的篇幅討論政府的官僚模式如何主導了對基因改造作物的理解。這些橋段當然都充滿趣味與省思,只是它們似乎不在同一條線上,猶如被強湊一桌的宴席菜,主打超值的過年福袋。
最後我也就想到全書眾多的田野記錄中的一段描述。那是在瓜達盧普島上,與羊群撲殺計畫團隊相處的時光,Wanderer說,這個團隊除了是緊密的合作夥伴以外,團隊之間彼此同桌共食的習慣,讓他們還同享著某種微生物的連結。在不可見的世界裡,微生物相互傳播分享,久而久之,大家身體裡就寄宿著相同的微生物群,「成為同一種形狀」。
Wanderer的記錄到這裡就停止了,沒有繼續往下解釋,在後來的章節裡也再沒有提起人與人之間的微生物連結,彷彿這個片段不過是一段軼事而已。我總覺得這段故事彷彿成為全書的縮影──故事反覆岔出歧路, 似乎指向了遙遠的關鍵,卻又無法通往最終的結果,以致於最後讀者就這麼迷失其中……。
Emily Wanderer是麻省理工大學(MIT)的人類學、歷史、科技與社會研究博士,受業於Stefan Helmreich,目前擔任匹茲堡大學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人類學系助理教授。《害蟲的生命》從博士論文擴寫而來,是Wanderer的第一本著作。
關鍵字:生物安全、醫療人類學、多物種民族誌、生命政治、墨西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