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逼无奈”的俄罗斯与“活该”的乌克兰:地缘政治的知识霸权
一 本文的背景和目的
根据媒体报道,俄罗斯于2月24日对乌克兰采取了军事行动。此前,克里姆林宫刚刚承认乌克兰东部的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地位。这一系列干预行动是2014以来俄乌冲突的延伸。对此,俄罗斯声称,北约的多次东扩和在其邻国部署军事设施的行为严重威胁俄罗斯的战略安全。尽管俄罗斯坚称其采取的是“特别军事行动”,但其派遣军队进入独立的主权国家乌克兰,显然是一种发动入侵的帝国主义行径。
目前这一冲突的结果尚未明朗。有网友指出,简中互联网的信息较为混乱,由冲突双方提供的信息可能服务于政治目的。我们在当前网络舆论中,则可以看到一系列流行论述: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是“被逼无奈”的决定;乌克兰的亲西方政府冒犯了俄罗斯,是自作自受;乌克兰政客没有认清自己的国家处境并制定正确的国家战略,等等。许多国内媒体、博主、“专家”(甚至专业的大学教授),也开始供应相关的观点。这些论点不仅是特定政治立场的产物,从惯常的国际政治学观点来看似乎也颇具合理性。
本文的任务正在于将一些习以为常的地缘政治论断“问题化”。无论是“选边站”的立场论述,抑或“理性”的“现实主义”分析,这些地缘政治知识的前提是什么?它们又是如何被正当化、自然化(naturalized)的?这些论述及其前提是政治上合理、乃至政治中立的吗?对于小国的所谓“政策自觉”的语言规训,折射出怎样一种全球秩序想象?
我们不谋求对具体国际事务进行经验分析,仅试图提供一个关于“如何理解国际争端”的视角,以批判性地看待有关地缘政治的大众知识生产。我们认为,战争(除了其中具有反侵略、反殖民性质的部分)不仅在客观上是人道主义灾难,还是被人为策划的、服务于社会特权集团利益的集体暴力。现有的地缘政治知识生产的预设和逻辑,仍然将强化全球性的、国家之间或一国之内的政治不平等。

二 常见的国际冲突论述
目前的大众论述中,至少包括两种并不完全互斥的话语。首先是反战人道主义,认为无论战争的理由、目的、结果为何,民众都会受苦。这种对战争后果的经验性判断和对民众的同情是无疑是合理的,但它要么跳过了对战争和冲突的分析,从而可能错失对战争的政治经济与意识形态的洞察;要么不得不将这种处境自然化,如政治精英的野心、国家的“客观”需求。因此,这种朴素的人道主义可能难以抵御、或不得不向我们接下来要探讨的第二种话语妥协。
第二种话语经常被各国政府、媒体和不同背景的普通人所采用。它宣称,某大国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得不”采取某种行动,即使这种“被迫”的回应或反击将造成伤亡以及各种非正义的结果。这种话语在两个层次上被自然化和正当化:
1)尽管在冲突中这个大国占据明显的强势地位,但它被假设是在与一个更加庞大、邪恶的势力作斗争。于是,在局部它似乎是在向小国发挥支配性的权力,但在另一层面上它却被认为是一个霸权的抵抗者。
2)更深层的逻辑是,大国有权力/权利在无政府主义的国际秩序中保障自己的利益、维护自己的势力,因为最终这将保护该国公众的利益。
基于对大国(综合实力强势、对周边政治实体有一定影响力的政治实体)干预或入侵的这两个自然化、正当化层次,一系列支持战争、批评反战者的“天真”的说法就变得合理了。事实上,它们也经常被大国用于说服公众、为战争行为提供道德理由/借口。第2条在某种程度上更深刻地反映了“现代”民族国家体系的政治哲学和文化想象,即公民通过让渡权利、缔结社会契约结成“国家”这个政治共同体,因而国家代表本国(而非外国)公民的利益。
三 为什么说这是帝国主义?
两种正当化理由共同构成了一种“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及其修辞)的基础。它是怎样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呢?
1)“反霸权”的霸权及其修辞
尽管大国宣称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是为了保护民众的利益,乃至反抗外国的压迫,但那些同样受到侵犯的国家和人民只被当作了工具,被剥夺了“说话”和自主行动的空间和资格。这种反抗外国压迫势力、保护本国安全的政治正当性,只在一国范围内成立(参考上文第2条)。于是,所谓“反抗霸权”的二元观点排除了现实情境中多元、多层次的霸权或国家间权力关系,仅仅“目光向上”关注大国的所谓“生存权”和“安全”。
它的另一个问题是,“安全”本身不仅是实体性的,也是修辞性的。在政治/道德正当性论述的传播情境中,我们并不容易知道,这种正当性的限度是什么。基于“反霸权”而施行的霸权主义如果具有直接的合理性,那就意味着在一个“多头”的国际政治秩序中,任何拥有局部性、地区性霸权的国家,都将借此轻易获得干预周边国家内政的正当性。
一些人可能会质疑(根据上文第2条的政治假设),大国本来就只需为自己的民众负责,而安全风险在一个丛林式的国际秩序中可能也是实际存在的,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指出,对国家(利益和代表性)的想象本身也是成问题的。
2)国家作为分析单位的政治意义
国家被作为一个基本的地缘政治分析单位。地缘政治的惯常想象是这样的:一个无政府主义的丛林社会,每一个国家作为一个整全的行为者而决策和行动。这不仅是对“国家”作为一种社会政治制度的观念反映,也是对国家代表性的文化建构、假想方式。换而言之,国家的行为如同个人的行为;国家的利益是国民利益的体现,对于该国之内的社会和人民而言是政治中立的“公意”的体现。
这种想象把国家当成了铁板一块的、就其内部而言政治中立的制度实体和行动者。然而,国家内部包括不同的社会力量和具有不同利益的社会群体,其所宣称的(一国之内)普世的政治权利/公民权并不能反映实际的在阶级、性别、种族/族群等社会维度上的利益分配和平等程度,也不能掩盖从属地位的群体与上层统治精英的现实区隔。事实上,尽管政治科学主张国家具有一定的制度自主性,为不同利益的协商提供可能,但其基本语境仍然是:国家利益往往被统治精英扭曲,为自己的利益集团服务。对帝国主义来说,则是为它的统治集团所具有的跨国利益而服务。
在此,所谓小国“活该”论无非是承认了大国(帝国主义)有权干涉其他国家的自由自主,并且规劝这些弱小国家及其人民接受自己的从属地位。这种话语进一步合理化了当前帝国主义多头共治的压迫性全球秩序,也泯灭了弱小国家和民族作出反抗的正当性和可能性(这并不意味着把乌克兰当局的一切行为等同于这种反抗),实质上与各种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沆瀣一气。
此外,这种地缘政治的大众知识生产也受到应用、实用至上的相关专业知识的形塑。当代主流学术体制中的地缘政治、国际关系研究,相当程度上共享上述的国家(行为/利益)假设。尽管学术研究并没有无视非国家行动者的影响,但这只是由于它们——例如政治精英、公众——是政策和政治变动的影响因素。民族国家等强势力量被置于分析的中心,这不只是由于这些机构有很强的影响力,还因为主流的知识生产主要依托大学、智库机构,它们从国家、国际组织和跨国企业获得资金,并为之服务。与此同时,这些知识也通过大众传媒来潜在或有意地影响公众认知,强化人民与国家的意识形态绑定。于是,专业知识的生产需要对这些机构和控制它们的强势集团是“有用”的,而不是对人民负责。
四 反帝论述如何可能?
上文已经探讨了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如何将国家的利益、政策、意志(主要服务于其统治集团,并且被统治集团中的一小群精英所直接操纵)说成是“民族”、人民的普遍诉求和目的。综上所述,为了创造反帝国主义的话语空间,我们需要注意帝国主义的两个关键层面:
1)国际层面:帝国主义的决策本身的政治经济动力是超越国界的。一方面以当前全球民族国家体系为基础,另一方面国家决策本身的协商过程也受到(以诸帝国主义为中心的)地缘利益网络所影响。
2)国内层面:帝国主义宣称自己的对外干预是为了其人民的基本利益,然而这种被普遍化、自然化的“超阶级”的国家利益本身就是一个神话。它往往有利于在该帝国主义体系中获利的统治集团及其支持的政治精英,却牺牲大多数社会从属群体的利益,甚至以强迫或爱国主义感召的方式将平民送上战场。
对战争的态度从来不只有两个选项。我们不必仅满足于坚持朴素的反战立场,也质疑和拒绝所谓“理性”的、“现实主义”的、为战争提供正当化理由的各种政治论述。我们已经在理论上说明了后者的神话性质、其作为形形色色的国家主义(军国主义、帝国主义)的基础和产物所发挥的意识形态作用。只有清理和反思现有地缘政治论述、以及这种论述之前提中的政治倾向,才可能发展一种反战、反帝国主义、属于人民和为了人民的地缘政治论述。
需要说明的是,我并不反对必要的、作为分析工具的地缘政治和国际关系视角,但应该在反思其假设的基础上运用这种视角,以避免将国家的利益和议程从分析范畴异化为分析目的。此外,帝国主义的干预手段不仅有军事干预,还包括经济制裁等。帝国主义参与的冲突可能不仅是其自主的野心使然,其与其他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合作、妥协也值得关注。但正如上文已经阐述的,这并不意味着为任何一种帝国主义行径打开方便之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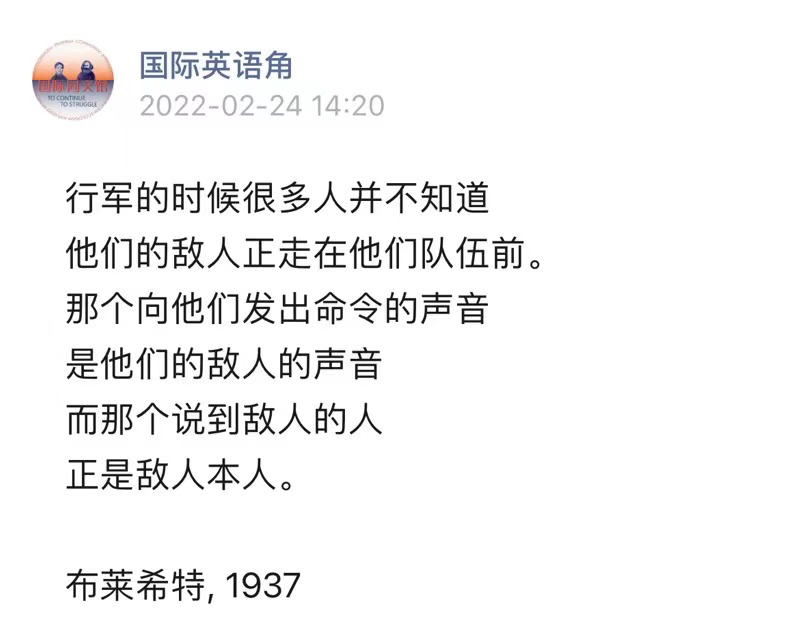
往期评论:
头戴锁铐的娜拉:徐州八孩女子与农村父权叙事(2022-2-22)
东方主义,多重“边缘”与审美解放:回顾陈漫事件及其争议 (2021-12-22)
欢迎订阅Matters账号与微信公众号「蜉蝣型幽灵」
ID:gh_ff416309254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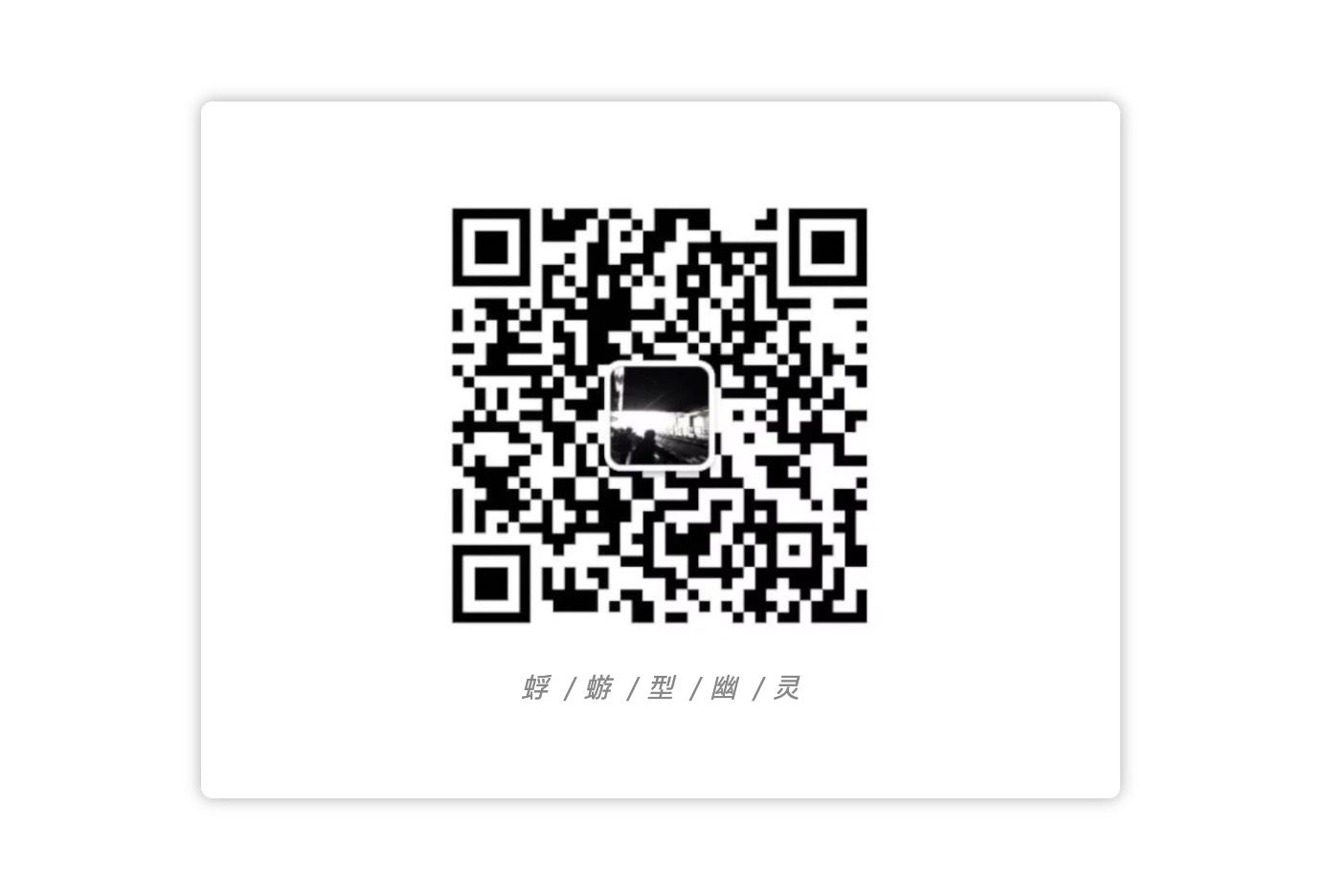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