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子作爲身體的隱喻——韓麗珠《回家》的空間意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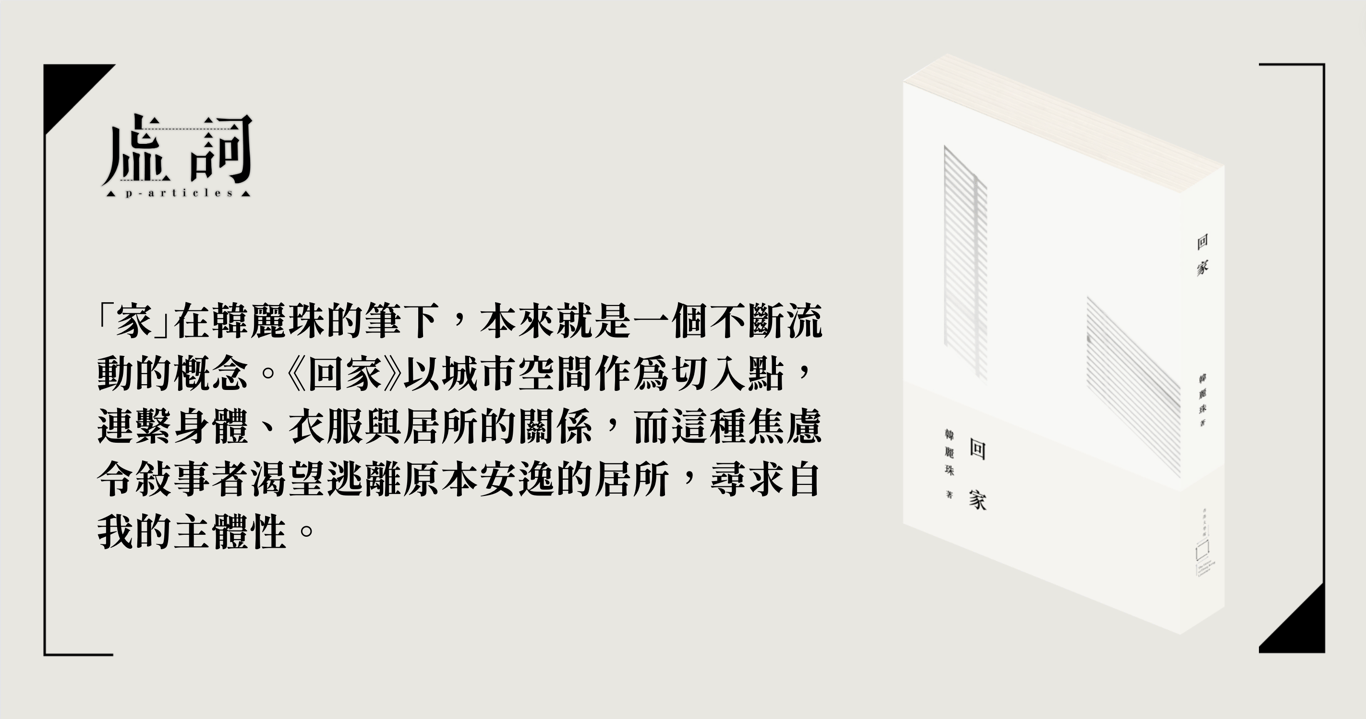
文|陳嘉歡
韓麗珠小説裏的空間可以是實踐規訓與權力的場所,同時也可以是個體尋求自主的所在,要分析當中的關係,必須要先解答小説中的身體意象如何隱喻個體的主體性。
林怡伶在分析韓麗珠的小説時,提出「身體即是空間」一説,認爲身體這個空間令角色得以在扮演「社會身份」的同時,能夠有空間存放「真正的自己」。(1)她指出小説的敘事者試圖想象一個能夠安放真實自我的空間,不受外在的威脅與傷害,變形為一個「介殼」(Coquilles)相似的空間,以此成爲「逃逸」的方式。(2)因爲失去自主的身體只是一個可以扮演的「社會化定型身份」,這個身份並不是「真實的自己」,只是一個可供躲藏的身體空間。韓麗珠在《回家》以散文語言重新釐定「身體即是空間」的意涵,將身體、物件與居所的意象連結起來,大概可以分成三個部分。
身體、衣服與居所
〈逃離安居的處所〉裏敘事者指出「房子」、「衣服」和「身體」都是安放自身的所在,同時處於終將消失的焦慮之中,因此敘事者嘗試自我安慰:「其實沒有屬於自己的居所也不要緊,反正,靈魂其實被安放在軀殼裏,而身體其實被盛載在不同剪裁的衣服之間」。敘事者帶出「房子—衣服—身體」的遞進關係,空間逐漸收窄而最終指向身體本身。身體作為個體主體性最後一道防線,卻也是人處於社會之中最難以掌握的部分。因此城市裏面的人終生勞役身體,把身體安放到居所裡面,試圖換取「家」的想像,彌補自身無法掌控身體的焦慮:
「他們繞過了所有令人忐忑的思慮,而把注意力投放在購買一棟可以容納自己的屋子之上,即使花費了一生的光陰,把皮囊虛耗得筋歇力疲,甚至油盡燈枯也不介意,並不是因為他們對自身的反省不足夠,或對於外界的入侵思考得不夠透徹,而是,她們早已認清了一個實相——購買一座房子,得到一個安居的想像,遠遠比尋回身體或個人的自主更容易達成,也更具體可得。」
由於「居所」、「衣服」和「軀體」三者有完全一致的功能:作爲安放自身的空間,因此它們之間的差異得到被消解的可能。敘事者嘗試藉助衣服掩蓋身體,城市的人們勞役身體以換取自己的居所,都無法掩飾主體性的失落。一層套一層的意象,包括用軀殼包裹靈魂,以衣服收藏身體,或者以居所安放身軀,最終都指向內在的虛空。
身體與主體性
個人自主的失落,是敘事者從居所裏出走的原因。而這種身體或個人的自主之所以難以達成,源於現代化社會對身體的監管與操控:
「人們一旦出生而且成長於群體,他的身體就注定被某種完善的標準制度——離開母體時的正常體重、注射防疫針的正確時機、各種年齡的應有高度、發育時期開始和終結的年紀、脂肪的比例、膚色的深淺、容貌的端正、應有或不應有的氣味、開始戀愛的年齡、伴侶的數目、生育的時候、治療疾病的方法、應該死去的時間、作息的規律⋯⋯凡此種種,都是我們介入別人的身體或被別人介入自己的身體,過於理所當然以至習以為常的干預。」
敘事者因爲無法掌控身體的焦慮,因而離開原本安居的處所:「我買不起一間屋子,也無法掌管自己的身子,便只能逃走,而且無法清楚地解釋逃走的理由」。這裏的「逃走」代表個體暫時放棄社會角色或倫理關係的制約,也是尋求自我的出口。原本在家的空間裏面,敘事者需要「勉强扮演他人分派的角色,仿佛只是爲了使旁觀者感到安心」。而這場出走令敘事者走到一個「偏僻的、靠海的小島,把自己收藏在一個租借而來的、暫時的空間裏」,在那裏她能夠將自己收藏起來。因此離開固有的居室,來到新的空間,便是要忘記社會身份的羈絆,試圖解放自身。
在篇章的最後,敘事者在流浪貓身上看見安然面對一切改變的可能,並認爲只有軀體的消亡,靈魂才可以達到真正的自主。因此真正的主體性,似乎必須在離開社會對身體的制約,才有可能有完整的呈現。
「身體即是空間」
〈踐踏皮膚〉裏敘事者將房子作爲身體的隱喻,透過擴張身體的空間,探索身體的界限。「在我還沒有屬於自己的居所時,基於一種本能的需要,開始練習瑜伽。身體是與生俱來的一所血肉房子,透過延伸和呼吸,嘗試探索和擴張它已有的空間。」 敘事者再次將身體和空間並置,這篇文章藉助身體與房子的共通點,帶出個體如何試探並劃分與外界的界線:「我總是不會先説明要求,關於訪客如何接觸我的地板。有時是忘記了,有時是找不到那種機會,但更多的時候,我想試探他們隱藏著的那一個面向。」
在這個身體意象之下,身體和居所的共通點是同樣能夠劃分自我與外界,同時他人也有介入自我的身體或居所的可能:
「他(敘事者的親密關係對象)一再走進我的家,把鞋子放在門外,但把腳印帶進屋内各處,包括我的皮膚、腦袋和心臟。當他離開了以後,我以許多不同的方法拖地,然後洗澡,但那些瘀傷似的印痕仍然在,而且是無處不在。這些痕跡讓我知道,我還沒有懂得訂立自己和外面一道明確而安全的界限。」
居所作爲身體的延伸,敘事者觀察來訪者對待自己居所的方式,以此試探對方與自己的關係。而身體不斷延伸的過程,隱喻個體不斷打破、又重構與外界的界限,亦即在私密關係中打破、又再建構自我的主體意識。
「家」在韓麗珠的筆下,本來就是一個不斷流動的概念。《回家》以城市空間作爲切入點,連繫身體、衣服與居所的關係,而這種焦慮令敘事者渴望逃離原本安逸的居所,尋求自我的主體性。而人的一生勞役身體以換取居所,這件事本身也如同囚禁,敘事者以比身體更小的空間,突顯城市内人面對的困迫。身體與空間的共通性,令人在扮演身份和在群體中生存的同時,仍然希望軀體作爲一種空間,能夠保護「真實的自我」不受傷害。
韓麗珠在《回家》以散文語言重新釐定「身體即是空間」的意涵,將「居所、衣服與身體」的意象連結起來,層層遞進,指向個體無法掌控自主的事實,亦即主體性的失落。人們身體習慣被規訓,導致靈魂被軀殼所拘禁,無法獲得自由,因此空間對人的壓迫,亦寓意人們「從未走出自己的身體」。
(1)作者引述巴舍拉在家屋的概念下「介殼」一詞,其以貝類化石中的神秘幾何構作指陳身體的部位,或是建構家屋的想象,説到軟體動物生活在介殼内是一種源於内部的生命狀態,並將此是爲進化的本源。加斯東·巴舍拉(Gaston Bachelard)著,龔卓軍、王靜慧譯:《空間詩學》,臺北:張老師出版社,2003年。頁197。
(2)林怡伶:〈轉變是希望的開始?——論韓麗珠《風箏家族》身體與空間的變異意涵〉,《東華中國文學研究》第11期(2012年),頁2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