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持通話,得閒飲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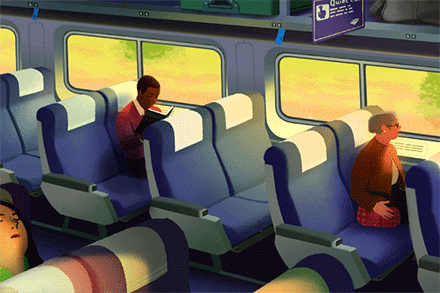
「保持通話,得閑飲茶。」
十一月初與L別送栗子到機場,這是她臨登機前說的最後一句。語調與平時毫無二致,仿若是與日常裏從酒館喝到三更半夜後的「明天見哦」相類似的東西。但這一次終究與以往不同,她即將飛往大洋彼岸,下一次再會的日期,尚未出現在我們的人生行程當中。
我與L十分明白,這只不過是栗子式的客套話,但話語一旦說出口,便能夠擁有安撫人心的力量,對於這一點,我們同樣從不懷疑。
那時我與栗子四目對視,一時間腦海沒能浮現出話語,與相識十年的好友道別,本來想好好說一番話留作回憶,但到頭來又發現不知從何說起為好,唯有默默點頭。
我們在不實的世界裏,很多的離別,可能就是永久的離別,在應說之時沒有說出口的話,就等同輸給了時間與壓力,往後再如何掙紮也沒法到目的地。即使到現在,一回想起當時機場裏的場景,我依然為自己的沈默感到遺憾。
從機場的停車場出來,清晨的天空陰沈沈的一片。初冬的寒風見縫插針地往車內襲來,我下意識拉緊外套,升上車窗,幹凈的車窗玻璃隱約倒影出L有條不絮握著方向盤的動作。為了給栗子送行,L前一天專門到車行清洗了汽車,還翻新了副駕駛座的坐墊。如今副駕駛座已經完成使命,在初冬的道別日裏坐上去顯得格外冰涼。老實說,我不大了解自己的心情,好像道路拐彎錯了,在同一個地方轉來轉去的心情,或是時間的接續有什麽失常,無法順利前進的樣子。
從副駕駛座前的手套箱裏,我找到栗子早上買給我們的水煮蛋。
三只雞蛋裝在白色塑料袋中,隨著車的顛簸發出咯咯咯的聲響。我將其中一顆雞蛋遞給L,隨即拿起第二顆雞蛋,敲開底部,輕輕剝開殼來。我一口咬掉雞蛋的一半,嘴巴被雞蛋從側邊撐開,我只得保持眼前可笑的樣子,反復咀嚼。待手中的雞蛋吃完,我又拿起最後一粒雞蛋,重復方才的動作,敲碎、剝開、咬掉、咀嚼。
兩個男人在汽車裏拼命地吃著雞蛋,吞落友人留給我們的最後禮物。
「若果人與人之間的交往終究面臨分別,那交往的意義又是什麽。」我自言自語般發問。
「正如你我終會死去,但並不能以死亡這一結局來否認生存的過程。」L回應道。

汽車不緊不慢地前進,棕櫚樹在冷清的公路兩側緩緩往後倒退。雞蛋已經吃完,殼碎零零散散地裝在白色塑料袋之中,隨著汽車的震動不時輕輕彈起。L按開音樂,我用力地貼著靠背,想好好聽聽音樂,但眼下做什麽都沒有心情。
「正如你我終會死去,但並不能以死亡這一結局來否認我們生存的過程。」
L的話使我想起高中時代的政治老師,他四十歲,身材十分瘦削,總是穿著一件單薄的白色襯衫。每當他用粉筆在黑板上寫講義時,我們便看到他那件單薄的襯衫在瘦巴巴的身材支撐下輕輕擺蕩。這位老師為人甚是幽默,課堂也並不沈悶,對於書本中的政治內容也總是教導我們如何取舍,所以在我們學生當中頗受歡迎。
高中畢業後,我與這位老師便斷了聯系。直至有一天從舊同學口中聽到他在家中自縊而死的消息,據說是因為家庭的糾紛煩惱而想不開,留下簡短遺書後便自絕生命。我一度為此感到難過,但除了難過,我說不出其他感受。對於死亡與別離,我不願多想。
我坐在座位上望著車窗外面的風景,對L說起那位政治老師的事。但對於他在世時回憶,現在已經所剩無幾。我能清晰記得的只有他那件單薄的襯衫,以及襯衫在他舉高右手在黑板書寫講義時輕輕擺蕩的場景。
飛機如同一只巨大的鐵鳥,從我們上空飛行而過。時而駛過柏油路的汽車輪胎聲傳入我耳膜,仿佛用手指摩擦質地細致的布料發出的絲絲聲。
「上一次能與人好好道別是什麽時候?」我問L。
L聽完以認真的眼神沈思良久。
「大約四五年前,算是酒館一個熟客。」,L緩緩說道,「她常常在傍晚時分沒什麽客人時光臨酒館,年齡莫約三十歲左右。每次都是單獨前來,點一杯威士忌,然後詢問能否播放她中意的音樂,享受完音樂與酒精後便靜靜離去。如此往來半年左右,我便漸漸與她相熟,知道她已婚,沒有小孩,自己是自由撰稿人,而丈夫在一間知名教育機構上班。」
「直到一日,她告訴我不久之後,她便要隨丈夫搬遷到其他城市,但家中有一兩箱由日本山崎威士忌,若連同搬家一起帶走實在麻煩,於是希望臨走前能將其贈送給酒館。我一口答應,相約第二天中午前往她的家中。」
公路上的車輛漸漸多了起來,他們大多數往機場急速駛去,如同端流裏的魚,被一一沖往的河流的分支點。
L繼續說道:「她住的公寓在植物公園附近,從酒館開車前往,大約二十分鐘左右。公寓幹凈利落, 家具與裝修都給人十分舒服的感覺。她招呼我坐下,桌上擺著甜品,提議先嘗試一下威士忌的味道,說罷便將威士忌從房間裏搬出。 我們就像沒有趕上最後一班列車的乘客,一起喝她家中的威士忌,品嘗著她親手烘焙的糕點。」
「那天天氣極好,公寓陽臺晾著被褥和床單,滿是陽光的味道。那味道我至今也還記得。」
「喝罷威士忌,我們開始交談關於自己的事。不過,我沒有什麽好講,幾乎都是她講。但我現在才明白過來,原來她當時只是想向誰說些什麽,百無聊賴的事情也好,歡欣雀躍的事情也罷,她只是想找個人一一傾訴。這種心情我多少能夠理解,於是我靜靜地聽她說話,一直到傍晚時分。」
「我們漫談到傍晚五點,我說時間不早,是時候要走了。她默默看了一會墻上的掛鐘,頓了頓,說謝謝我一直以來的威士忌與音樂,讓她在那段時間裏非常愉快。我也起身表示謝意,謝謝她的威士忌與糕點。送別我上車時,她說了句再見,我也點頭示意,祝她往後生活愉快。」
「即使四五年後的今天,每次酒館裏有單獨前來的點威士忌的客人,我都會想起她,想起那箱山崎威士忌。她可能已經不喝威士忌,若仍然在喝,我倒希望仍然有酒館可以播著她喜歡的音樂,然後讓她慢慢喝完後靜靜離去。」
「我並不清楚這是否稱得上好好道別,但那句『再見』已然具備道別的力量。縱使往後如何懷念,也已然算不上有什麽遺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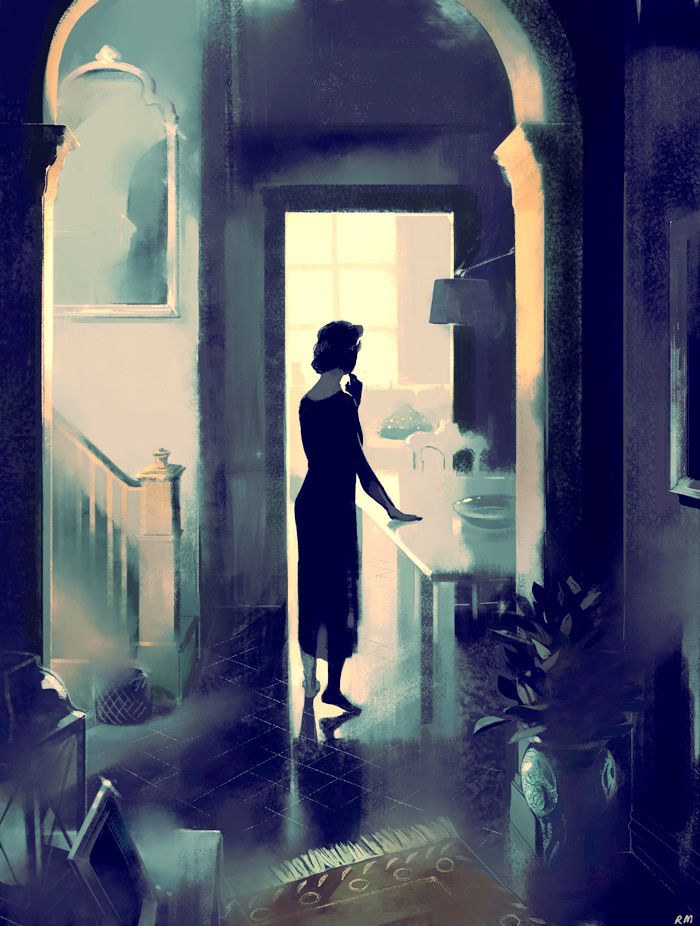
送別栗子的三個禮拜後,我接到栗子的電話。那是分別之後我們第一次通電話,在淩晨四點的冬夜。電話如同震動了整個世界般響起,我睡眼惺忪地接起電話,電話那頭傳來栗子的聲音。
「喂喂!」
「哪位?」
「哪位?這算什麽呀!我剛剛下班拼死拼活給你打電話,就換來這麽一句話?眼淚都要出來了,你已經成了一個冷酷無情的人了嗎?那些溫暖人心妙趣橫生的對白全丟在浩瀚無垠的宇宙了嗎!」
「我這邊淩晨四點,丟失在枕頭裏了吧。」
栗子咯咯咯地笑了起來,聲音讓我想起道別那天車裏的水煮蛋。
「怎麽了嗎?」我輕聲問道,「在那邊是被驅逐出境還是鋃鐺入獄了?」
「沒什麽,就是突然想聽聽你說話。」
我一時語塞,妄想尋回丟失在枕頭裏的話語。
「我要去打給L了,就這樣吧,拜!」
「嘿!」我喝住準備掛斷電話的栗子,「有什麽事隨時給我打電話。」
「即使是在淩晨四點的冬夜裏?」
「即使是在淩晨四點的冬夜裏。」
「好的」,栗子如雞蛋的笑聲再一次響起,「那就這樣吧,再見。」
「再見。」
掛了電話,我腦海突然浮現出栗子拼命吃水煮蛋的模樣,幻想著她嘴巴的一側被雞蛋碎撐開的樣子,不由自主地發出笑聲。隨後我關起電話,再一次鉆入被窩,趕在冬夜奪走腦海裏栗子吃水煮蛋的幻想之前,我需要盡快重新入睡。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