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表面張力:讀Marianne Lien《成為鮭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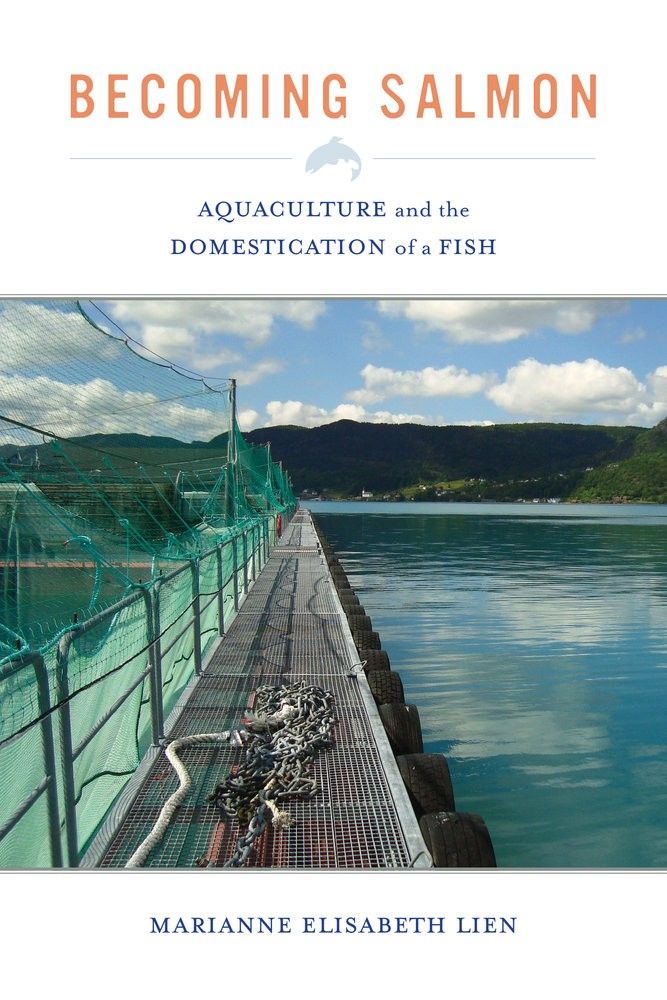
Marianne Elisabeth Lien, 2015, Becoming Salmon: Aquaculture and the Domestication of a Fish.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我們需要一些鹽,一些鐵/一堆熊熊的火/我們抵達,然後停頓/然後被時間釋放。」──洛夫《漂木》〈鮭,垂死的逼視〉
難得溫暖的北歐清晨,陸地上的一天才剛要開始,海面下,另一座城市早已生機蓬勃。十九歲的Aanund登上了Vidarøy養殖浮島,這是他在這個峽灣打工的第四個夏天,與另外兩位同事掌握著60萬隻北大西洋鮭魚的命運。他們一人身兼多職:農場工、殯葬員、行政文書,有時甚至是實驗室助理,唯一的目標是確保這座龐大的鮭魚之城運行不墜。
Aanund熟練地把大塑膠管的一端綁在塑膠容器上,另一端則沈入箱網底部。幾秒之後,已經死去的鮭魚(daufisk)從水管裡一隻接著一隻噴出。清除死魚是每天固定的任務。事實上,死魚是養殖鮭魚產業裡的人們少數可以親眼「看見」鮭魚的幾個場合之一。除了鮭魚,被稱為leppefisk、色彩繽紛的底棲性小魚也被抽了出來。活著的leppefisk被丟回水中,牠們是城市裡的次等公民,因為被認為能減少魚虱而獲得了居住權。
除了清除死魚,餵食是另一個人類有機會與鮭魚建立關係的時刻。機械投食之外,百分之二的飼料會由員工手拋,這讓比較虛弱的鮭魚不致於挨餓,同時也藉由觀察鮭魚進食的速度來評估箱網的健康。在Vidarøy養殖場,人與動物的相互性並不是一對一的關係,飼養員面對的是以箱網為單位的集體魚群,透過日復一日的餵食過程,他們將逐漸認識每個箱網不同的性格。

這一天,11號箱網的死魚數量總共有58尾。即便這座箱網裡生活著將近18萬隻鮭魚,這個數字仍然偏高。麻煩的是,這可能是胰臟疾病的癥兆,有必要請獸醫進一步診斷。Aanund從箱網回到浮動的辦公室裡,把寫在防水表格上的daufisk數字輸入電腦。這些數字會立刻被傳送到陸地上兩層樓高的總部,和其他統計資訊一起決定公司接下來的業務程序、出口策略與預期獲利。換句話說,Aanund和同事們不僅要生產高品質的鮭魚,還要生產好看的數字,把濕答答的漁獲轉化成一疊疊乾燥的紙本報表。
Aanund的每日例行任務只是Marianne Lien《成為鮭魚:水產養殖與魚的馴化》書中的一小塊拼圖。出身挪威的Lien自稱這本書是「在家的人類學」,她把民族誌技藝運用在養殖鮭魚身上,邀請讀者反思「自然」、「工業」與「福利」這些我們習以為常的概念。穿梭在海上的鮭魚之城、決策總部與稚魚養殖場之間,就像Aanund一樣,Lien追溯鮭魚的雙面性:作為非人物種、具有生命的鮭魚,以及作為全球商品、被捲入工業化生產擴張過程的鮭魚,當然還有兩股張力之間的轉譯與摩擦。《成為鮭魚》想要勾勒的便是「鮭魚」如何在這張異質網絡裡誕生。
挪威不僅是全世界最大的鮭魚出口國,也是北大西洋鮭魚的馴化地。如今,牠們被豢養在智利、加拿大、蘇格蘭、塔斯馬尼亞的水域裡,全年無休地供給著規模龐大的全球消費市場。舉例來說,星期日在Vidarøy被宰殺的鮭魚會在星期一的凌晨被開腸剖肚、分裝進保麗龍箱,統一由貨運司機載送到挪威城市Stavanger,從Stavanger搭船到丹麥,再由陸路貨運前往阿姆斯特丹附近的Schiphol,整趟路程大約三十個小時。在Schiphol的機場,其中一些鮭魚將會搭乘國際客貨機前往杜拜、曼谷、東京、台北等亞洲城市。同時,貨車會把內銷歐盟的漁獲載往巴黎、布魯塞爾或柏林。到了星期四,來自鮭魚之城的鮭魚已經游進了全世界饕客的肚子裡。

期待看到Lien跟鮭魚面對面「溝通」的讀者可能會失望,因為她清楚地告訴我們,鮭魚和人類存在於不同的介質中,彼此之間雖然有「部分的親近性」,但沒有什麼浪漫的可能:「我們的世界環繞著牠們的世界。」在感官和儀器都難以穿透的漆黑海面下,鮭魚只不過是冰冷的概數。
對我來說,除了從馴化的歷史視野切入水產養殖現場,《成為鮭魚》最精采的章節,大概還是Lien對鮭魚之城不厭精細的描述:「這些住宅比肉眼可見的部份還要多,有許多未被計數與命名的生物。邊界在字面上和比喻上都是液態的,它們不穩定而且持續變動。」隨著藻類生長,箱網本身也成為其他有機體依附的對象,魚虱和其他病原體在網內網外來去自如。鮭魚之城是一個生成中的、由死物與活物、人與非人構成的多物種組裝體。
鮭魚之城的不穩定性,讓我們認識到全球養殖產業鏈裡無所不在的風險因子。Lien一再指出,鮭魚加入馴化動物的行列不過半個世紀左右,任何環節都有可能出差錯。即便是在陸地上的稚魚養殖場,一位員工也要照顧16個水箱裡的80萬隻稚魚。和箱網一樣,水箱不是一個封閉的系統,而更像是一格格被仔細監測、有著定時出入口的小池塘。水面高度、氧氣或水質的變化都可能觸發警鈴,有時甚至需要走進森林裡排除障礙。
水始終難以捉摸。透過反覆的試誤,人類在熟悉卻又陌生的介質裡琢磨著文明的表面張力。漂浮在挪威峽灣裡的鮭魚之城是一個脆弱的奇蹟。
Marianne Elisabeth Lien是挪威奧斯陸大學(University of Oslo)的社會人類學系教授,她的研究領域包括食物、營養與消費的人類學,近年來則從經濟人類學與水產養殖的角度探索全球化、自然/文化與馴化的議題,並深受科技與社會研究(STS)的重要學者John Law的影響。Lien的第一本英文書是Marketing and Modernity: An Ethnography of Marketing Practice。
關鍵字:馴化、養殖漁業、人與非人、食物與食品、北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