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閉小孩給我的課: 識別拒絕和冷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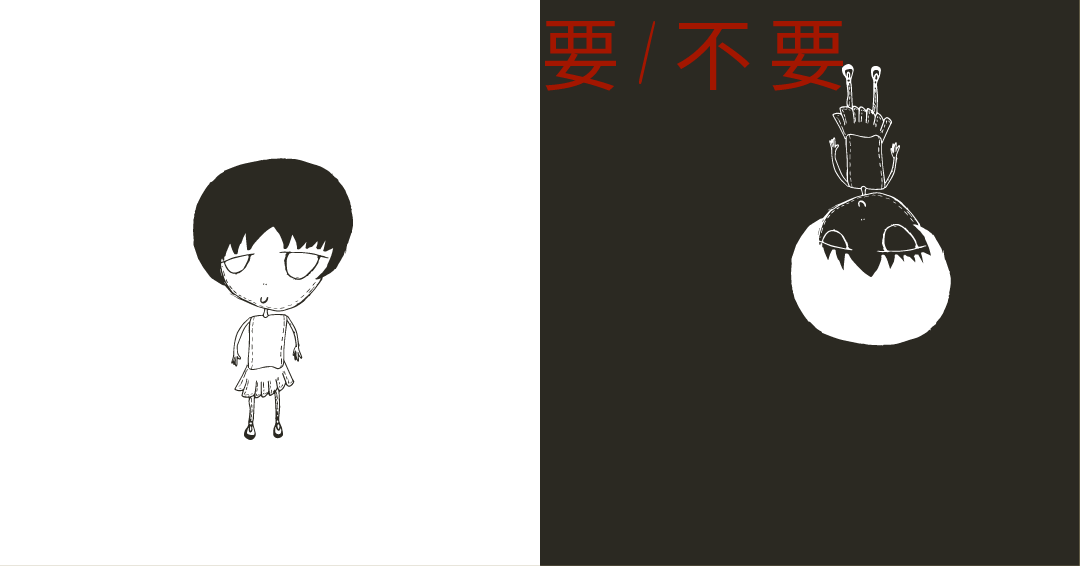
機緣巧合,自七月十六日開始,一連二周,每周三天當上由C&G Artpartment (http://www.candg-artpartment.com/ )主理的summer art cadets 2019創作工作坊《動物合作社》的其中一位導師,跟十一位不同程度自閉小朋友,約七歲至十二歲,以及其他三位藝術家及義工,以視覺藝術及身體感觀為工作坊的軸,再加三次外訪不同藝術館,一起玩樂,一起學習。
工作坊之前,我對自閉小朋友的認識幾近零,只看了一些資料,知道美國可能每六十個小朋友有一個被診為自閉,自閉症本身有很多不同狀態(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 ,的碓,只是傻傻憑著對小朋友的好奇及耐性,以及對藝術可以啟動自由的信念,去接近他們。
第一天破冰的確不太易,十一位小朋友不論年紀、情緒狀態、聚焦能力、願意溝通的時間都有很大的落差。我們準備好的遊戲,不是每個都有效,他們半數樂在自己的世界,經常說不經常拒絕,另有幾個根本嫌你低能幼稚不願玩,反是一些身體遊戲,如搭肩扮一串火車 (當中有兩位小朋友是超級火車迷,熟唸新幹線火車型號及JR 所有車站) ,或簡單遊戲如「狐狸先生幾多點」,他們反而有些些興頭參與,建立短暫的集體意識。
經過好幾天的密集相處(每天四至九小時不等),被孩子拒絕是常態,但每對眼睛並不空洞,拒絕之前,他們定眼、不言、背離、搖頭,流淚、重覆火星短語、身體忽然狂擺,都在思考,都在細想。我慢慢識辨冷漠及拒絕的分別。真的很想理解他們的世界,進入他們的故事,到底為何拒絕邀請? 是沒有安全感,是討厭別人的秩序,是只想留在自己的世界,是害怕面對自己的不能? 但有時又為何接納? 當中是什麼在起作用?
老生常談,時間才是真正的老師,沒有耐性,沒有(可能)回響。而且,漸漸地,從他們身上,我看見自己童年的身影: 閉咀,獨坐,令自己無感,遇上挑戰即離隊,在一個人的世界,安全,寫寫、呆呆。
真的,如何跟他者相處,如何尊重和你很不一樣的同伴的空間及自由,如何閱讀拒絕及接受,如何堅守自己的原則,都是我從小朋友之間的相處看到的,
見過小孩被另一位小孩「突襲」,被紅色印章大刺刺地蓋在面的正中央,他呆了三秒,沒有發脾氣,看清對方只是一時興奮,沒有惡意,長唉了一聲,走開,慌亂的,也不知道如何處理臉上的印痕。也有另一位小朋友,給另一小朋友從頭淋皂水,他一樣沒有發火,只是哎呀一聲,走開,沒有哭。小朋友到底如何判斷? 他們相互不認識,全都是陌生人,但能力不一樣,是很明顯的,這些能力較好的小朋友,知道要用不同的方法去和他們相處,知所進退。
聽過兩位九月後才升上四年級九歲大的較「醒目」的小朋友對話:
A: 你知道我地同呢班小朋友有咩特別嗎?
B: 咩呢?
A: 我地都係患上自閉嫁?
B: 你肯定?
A: 係媽咪話嫁!!
B: 我唔信,我唔係。
A: 媽咪話我地自己唔知架,係醫生判斷嫁。
B: 我唔信。咁你知唔知咩係情緒病?
A: 唔知。
B: 我都唔知。
兩位小朋友完全沒想過要問坐在身旁的我,自顧自繼續畫畫。信任到底如何在小朋友之間建立? 他們心底裡,未必完全相信老師和醫生,甚至家長。但,其實,小朋友是有知得更多及更仔細的權利。所謂保護他們,跟讓他們自行思考及獨立選擇是大人要好好分辨及細想的事。我忍不住硬生地延伸思考,想及最近的銀髮出來保護青年人的說法,真的要很小心,青年人已經用血肉做了很多,加了很多大油,不用長者來保護,長者要行動就用自已的身份去聚焦反抗,不需要以家長身份來出師,要共同成為抗爭的主體,要真正互相尊重,談何容易。
工作坊有好幾位小朋友都有自己的火星語言,一時三刻很難理解,是想「要」還是「不要」? 喜歡繼續還是討厭? 推開你的手是否真的想你離開? 他們真的知道要什麼嗎? 真要很小心的,就算他們說好,原來也未必是好。有機會跟一位照顧小朋友的印尼姐姐姐細談,知道原來由她看大的小朋友,因不懂發「唔」這個音,所以如她說「好」,其實是「不好」,那什麼才是真正的好? 原來是她重覆你的話才是好,如你問她「XX , 飲水好嗎? 」如她答:「飲水」才是直正的好,答: 「好」其實是不想要,天呀,真佩服眼前姐姐的解碼能力和耐性。語言指向的意義,從來不是固定不變的,在有差異的建碼及解碼情況下,意義可以完全相反,必需要明白發放者建碼的脈絡,才有機會有效溝通。想起,最近跟不同政見的人的溝通,其實當下有沒有構成有效對話的條件? 我有沒有明白對方的信念是如何建成的,如對方根本沒有聆聽的空間,自己也沒有足夠的時間辨識的話,真要硬碰嗎? 我又是否只想壓倒對方? 是否以為自己就站在(道德) 優勝的高地?
聽罷印尼姐姐的話後,我開始更多去理解及觀察小朋友之間非語言的溝通。第四堂左右的侯間,當中一位非常自我的女孩子,主動上前拉起一位正想背棄世界把自己屈縮卷曲如小蟲的朋友仔時,他接受她的邀請,然後女孩帶笑拖著他轉圈,陌生的二個孩子就短暫地起舞,轉呀轉呀,二人都笑得很快樂,很忘我,真的好美,好美。共舞時間也許不長,但空間被完全打破了。我不知道當中是如何成立的。可能只是很純粹的善。他們互有感應。
當然比較難處理的是完全的沉默。小朋友為了表示某種不能發洩的憤怒或不滿,會把自己變成冷漠的石頭。一切甜言和挑釁都起不了作用。我想我明白的,小時候也曾這樣的。連表態,連回應都不想給大人,不會哭,不會笑,把自己冰封在小小的世界裡,其實就是徹底地跟世界切割,不要跟世界發生任何關係。這比起大哭大笑可怕太多,冷漠比拒絕更決絕,拒絕仍是一個回應,給你一個否定的姿勢,仍然在關係框架內,但如果小朋友,呆臉一張,冷冷地自顧玩樂或呆站,這才難處理,因為他已否定關係。
自然想及當下時勢,林鄭對民意不問不聞,冷對年輕人以血以前途對抗惡警,就是跟香港市民割裂,甘心成為中共政權的拉線公仔。同時間,前線的朋友,對所謂大人的懷疑及不相任,也非一日之寒,又是誰先對誰冷漠呢?
當下香港,如何連結跟自己不同意見的人,如何聽得見或讓別人聽得見呼應? 找到共存的扶持及壯大? 是純粹的善? 是更大的義? 在不同的社區都見到短暫的美。我會記得自閉小朋友忽然拉著我的手的溫暖及可愛的笑容。總會有間中陽光的日子,不要自己先冷漠,得一步一步去做及看。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