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徵:「要工作,似乎真只有離婚不可」—— 沈從文大師素描之六

【一】
沈先生要求把妻子調回北京。
事情辦得不順利。到情況有點鬆動時,沈先生又擔心,家裡只有一間小房,夫婦倆人擠在一起,可能會發生衝突。
他寫信給孩子說:「媽媽回到東堂子一同住下,將不免會迎面摩擦,矛盾突出。因為我除了工作無可為。......在工作時,自然是房中亂糟糟統無所謂,總經常會忘了洗臉、吃喝、理髮......忘了爐子和煮什麼。忘了離開桌子。有人來商談工作,又照例說個不休。那麼一間房子中,已經使她無個轉身處,若二三客人不斷前來‘古為今用’,她哪受得了?」
從1949年起,沈先生和太太的觀念一直不大相同。一位老跟不上形勢,另一位特別積極。在幹校,沈太太提醒丈夫少講話,說他一開口就錯。她又說沈先生思想落後,拖她的後腿。沈先生講:「話說得我極痛苦」。沈太太已經年過六十,還參加幹校的文藝演出。光是1972年6月,她就上台表演了三次。沈先生拿這事開過玩笑。
沈先生要求領導多給一兩個房間,以免太太回來住得太擠。但博物館一毛不拔。沈太太工作的作家協會在小羊宜賓衚衕給了兩間房,總共十九平方多一點。那裡原來叫小羊尾巴衚衕,離沈先生住的東堂子衚衕兩里地。
8月,沈太太辦了退休手續,以照顧沈先生為理由,從幹校回到北京。為了工作,沈先生一個人留在東堂子衚衕。小屋的地板堆起一摞一摞研究資料,桌上和床上經常攤滿書刊和圖片,牆上也層層疊疊掛著古代服裝的畫像。老人家晚睡早起,不停地讀書寫作。
沈太太帶著一個孫女住在小羊宜賓衚衕。沈先生每天中午過來吃飯,然後用小竹籃把晚餐和第二天的早飯帶回去。
那時中國的百姓沒有冰箱,夏天飯菜放久了會變味。沈先生對別人說:「我有辦法。」
人家望著他,想知道有什麼高招。
他正兒八經地說:「先吃兩顆消炎片。」
【二】
沈先生幹了一年多,到1973年5月,把《中國古代服飾資料選輯》補充修改了一遍,交給博物館領導。
他估計很快就能出版,心裡挺興奮。這本書是先秦到清代服飾史的大綱。原來計劃接著分階段或者分不同人群再編九本或十一本,全套十到十二冊。沈先生很快就動手收集和整理第二冊的資料。他覺得「至少還可望親眼看見三五本由我手中完成」。
但他的希望落空了。直到年底,博物館領導一點反應都沒有,書稿被丟到一邊。三個同事在一個月內去世。沈先生覺得自己時間不多了,在12月寫信給館長,要求退回書稿,自己抄一份留底。
就在這時,毛主席說林彪尊孔,推崇儒家。於是全國掀起「批林批孔運動」,把古代史翻出來,胡亂解釋,責罵林彪。這樣,沈先生研究古代服飾的書就更別指望出版了。
多年研究古代史,沈先生比當官的更了解儒家。他覺得把孔子和林彪綁在一塊是胡鬧,非常鄙視原來讚揚儒家、這時跟著叫罵的教授。他認為最可惡的是統治者不誠實,公開口號是一套,實際目的是另一套。沈先生給親友的信寫道:「從批孔到教改,知[識]分[子]大多不明白究竟要達到什麼目的。」「反孔批林運動進展,也許還是在造輿論階段。將來到一定時候,便將一轉而為......明日事,實難預知。」這段話裡的省略號是沈先生寫的,意思是公開的宣傳靠不住,以後不知會變成怎麼樣。
【三】
北京飯店蓋了新樓。
周恩來總理指示調一批畫家給它搞裝飾。為了跟周總理爭權,江青一伙硬說那些畫家的作品是「毒草」。1974年春,他們在人民大會堂和中國美術館擺「黑畫展覽」,從各地拉了三十萬人去看。被批得最狠的,是黃永玉一隻眼開一隻眼閉的貓頭鷹。這幅畫被說成是「仇恨社會主義革命現實,仇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沈先生看到報紙對表侄越罵越凶,冷冷地說,批「黑畫」不過是藉口:「這些哪會是真正矛盾重點?......卻儼然是大不可言之事!」
這時兒媳婦和親戚從江蘇來北京,在小羊宜賓衚衕落腳。沈太太帶著小孫女到東堂子住。於是沈先生的毛病暴露無遺。他沉迷工作,經常忘了洗臉,忘了理髮,忘了吃飯。沈太太很生氣,罵他「懶到一生少見!」
更要命的是沈先生不斷接待上門請教瓷器生產和紡織圖案的人。那邊只有一個房,客人來了,沈太太只好退到外邊屋檐下搭建的廚房,寒冷難耐。看著破舊的小房,她氣呼呼地對丈夫說:「在這種情形下,究竟還有什麼責任要你去盡?」
那時大批判鬧得亂哄哄。沈先生在科學院的朋友天天搞政治學習,不做研究。一位在博物館當中層領導的鄰居也勸沈先生別那麼認真搞文物:「不急於看書、做事......有些事還不知明天怎麼樣!」
沈先生不那麼看。他脾氣好,一方面做點解釋,另一方面哄太太去南方旅遊,散散心,自己留在小屋子里繼續幹。同時,他寫信給博物館領導,要求解決住房問題:「我上次曾告[訴]你說,就因為趕工作,家中六十五歲了的老伴,為此鬧得不和,發展下去,(可不是笑話)要工作,似乎真只有離婚不可。」
博物館根本沒把沈先生看在眼裡,巍然不動。
這時沈先生的血壓升到二百二十,左眼失明,只能靠一隻眼睛讀書寫字和看圖片,有時連自己寫的字都看不清。可他還在堅持。沈先生叫太太在南方放心休息,說自己一個人生活沒有問題,原來以為洗不了衣服,「試試也成了,不大髒,因之也易乾淨。但徐大娘還是帶去重洗了。」他覺得很容易把衣服洗乾淨,但別人把他洗過的東西拿去返工。沈先生顯然缺乏自知之明。
他一個人在北京幹了兩個半月,然後請假去上海治眼,但沒有明顯療效。沈先生回北京後,又恢復太太在小羊宜賓,他住東堂子的牛郎織女生活。
沈先生的視力仍然很糟糕,看遠處還湊合,看近處不行,不閉上左眼,就看不清書上的字。他說自己讀書的時候,「只能閉左眼,開右眼,如[黃]永玉所畫的貓頭鷹情形」。
他一個人日夜苦幹。有時他的屋子半夜還亮著燈,鄰居大娘擔心出了事,會敲敲門,探頭進來看一看。
沈先生的精神令人感動,一些年輕人自願幫助他工作。在1975年8月寫給孩子的信裡,沈先生說:「近半年得了兩個得力助手,先後已完成了八個專題,都還像個樣子。內有玻璃進展史、獅子在中國、馬的應用與裝備」。
【四】
1976年10月,「四人幫」被軍隊抓捕。
沈先生的反應相當冷靜。他在這個月寫的一封信裡說,聽到那個消息,他有點憂慮。如果滿足於把江青一伙抓起來,不從根本上解決中國政治的問題,那麼,同樣的災難還會出現:「若不能從這種現實的形成,取得一點教育,十分謹慎認真,對於‘城狐社鼠’可作隱蔽保護的根本原因,有所認識,而作出更大的努力,加以合理的制約,則到另一時,還難免出現這種歷史性的重復。」
過了幾個月,他又在信裡寫道:「不宜妄想,認為‘四人幫’一打倒,凡事好辦。」「要比較正確的認識封建意識在上中下各層已泛濫成災,並不是這十年四人幫混入政治最上層的結果,事實上卻由封建意識的廣泛抬頭,才會出現四人幫。」只是抓了四人幫,不真正鏟除專制主義的基礎,只要出點小事,知識分子又會遭殃:「情況小有變化,所謂‘右派復辟’可能又會在另一種形式下,成一部分老老實實的知[識]分[子]受過災難,亦意中事!」
沈先生估計自己能幹到八十歲,覺得必須抓緊最後幾年。他校改《服飾資料》,同時研究相關的專題。博物館對他還是很冷淡,老人家心情不好,打不起精神。這多少影響了他的身體。1977年中,沈先生的血壓升到二百三十,右邊手臂有時失去控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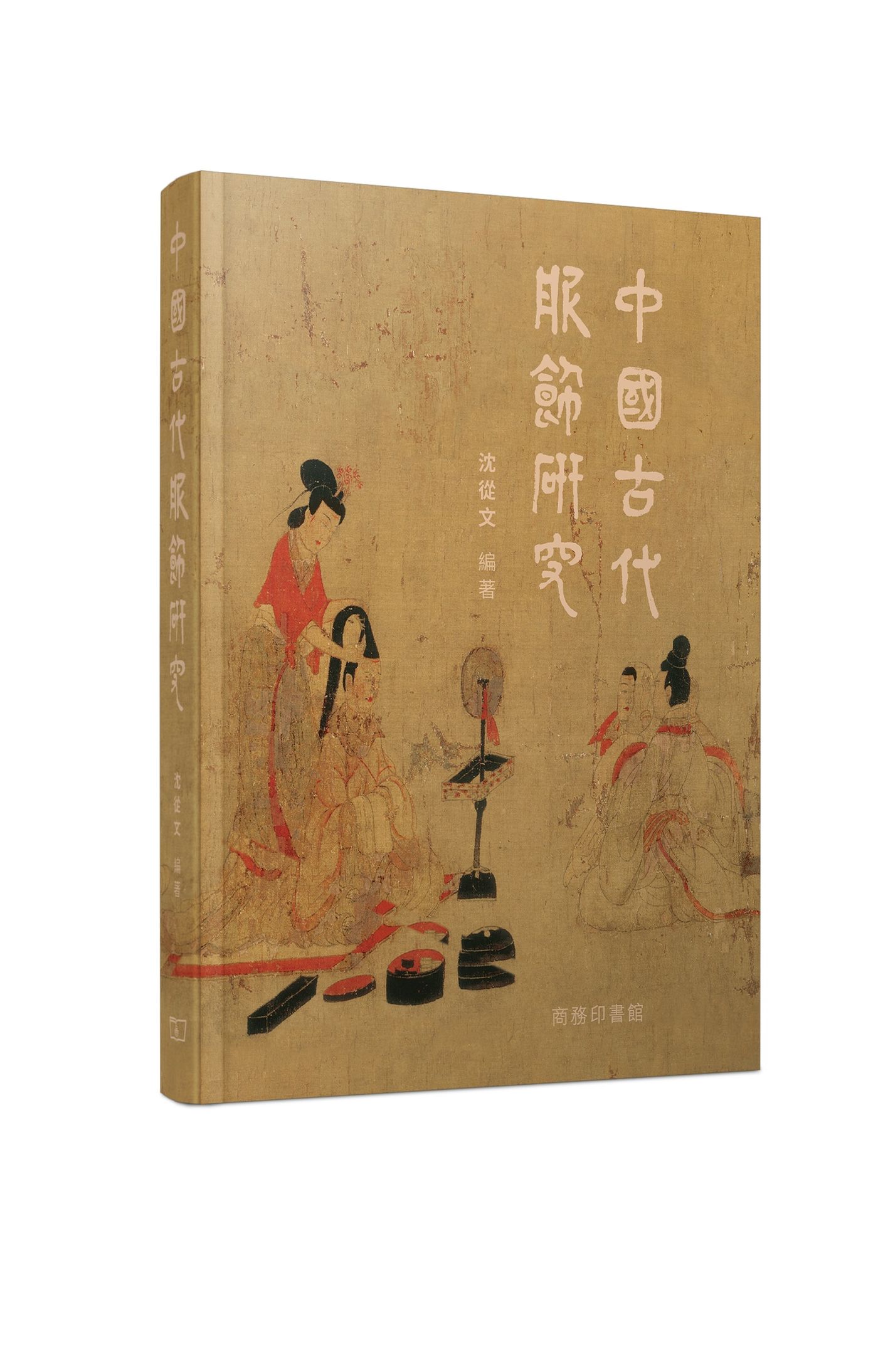
他寫信跟老朋友說:「看到經過小龍整理過一堆堆、一疊疊,以圖像為主的專題性待收尾、待完成或待進行的百十件材料封套,稍稍翻看翻看,頭就亂了。理會到可用精力已來不及一一完成了。試把已經過朋友為重新抄錄好那廿萬字《服裝資料》說明,校對清理一下,不到廿頁,一個上午就過了。一個多月還不曾校完七十頁,近三個月還只到百十頁。精力衰退比預料還糟。......困難處是絕不宜向家中老伴正式提出,而且任何方式提,變相提提,也不成。因此雖每天仍照常裝成去工作處,其實經常什麼事也作不下,不知不覺即過了一天。」
即使如此,沈先生還在咬緊牙關一點一點地幹。1978年春,探討古代扇子變化發展的論文完成。沈先生計劃年內再搞出四五個專題。但博物館既不解決他的住房問題,又不提供繪圖美工。沈先生全靠外面自願幫忙的助手。他還聽說,博物館想把他擠走,把《服飾資料》算作某個領導的功勞。
【五】
沈先生不想在博物館呆下去了。
剛好胡喬木當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沈先生跟他比較熟,於是想調到那邊。社科院可以給他調整住房,安排助手,而在博物館根本沒有希望。沈先生給兒子的信說:「若當真還能做幾年工作,或許還是換個地方好一些。」沈先生的住房實在不像話。他要改善住房,一方面是為了工作,另一方面也是為了沈太太。沈先生七十六歲,已經實實在在地考慮自己的死亡。他跟兒子講:「應考慮我故去後,為媽媽如何安排得好一些」。
1978年3月,沈先生調到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領導很快就給他配了助手,還把他從副研究員提為研究員。其實沈先生抗戰時就是西南聯大的正教授,當研究員只是恢復原有的地位。
得到領導支持,沈先生的勁頭又來了。他早上五點左右就開始幹,天亮搬張小桌子在院子里做事。沈太太的月季花種得很好。沈先生在兩百多朵月季旁寫作校對,陽光轉過來,就挪挪桌子,上午十點移到門廊底下,十一點以後退回屋裡。
他似乎年輕了五十歲。1933年秋,巴金到北平,住在沈家。每天早上,沈先生搬張小桌在院子的老槐樹下寫《邊城》,巴金在屋裡創作他的《雷》。
10月,社科院在友誼賓館租了兩個大套間,讓沈先生和幾個助手在那裡為《服飾資料》定稿。沈太太和他們的養女也參加了。沈家軍沒日沒夜苦戰三個月,到第二年1月中旬交稿。全書從1964年的二十萬字增加到二十五萬字,圖片從二百多張增加到七百多。
沈先生終於完成了十多年來「擱在桌上,壓在心上」的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