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可:研究动物交配,教我重新“做”“人”
以下文章来源于BIE别的 ,作者BIE别的

Randy
▼
“倘若把人类认为自己可以永生的信念加以摧毁,那么,不仅人类身上的爱会枯竭,而且人类赖以维持尘世生活的一切生命力都将枯竭。”
——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
当我读到这句话时,还来不及思考爱与永生之间的关联,手机便收到了一条新书推介提醒,《它们的性》,一本讲 “动物的性” 的书。
这本书的宣传语里写:忠诚与出轨,诚实与作弊,温柔与残暴;美丑、阶层、江湖、宫斗、无私、同理心……动物的世界,与人类世界无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立马下单了,收到书后,我带着普通读者的趣味,用人类的视角来观察动物。看雄性里的弱者为了求偶作弊,鸡舍里的老鸡联合起来教训不懂事的年轻鸡,千奇百怪的丁丁形状和雄性对雌性的强迫性行为,求欢前被母老虎撕咬虐待的公老虎……
忍俊不禁的同时,却渐渐生出一点疑惑:难道生存和繁衍,打斗和交配,活得长和生得多,真的足够解释人之所以为人,又足够解释动物之所以不为人吗?而人作为动物的一种,人性里除了动物性,就没有一点超越性吗?
直到我在作者后记里读到这样的句子,“倘若我背离了中心主义,便如无根之浮萍,无从质疑人类中心主义理性的正当性,倘若接受中心主义,则非人类中心主义一直是悬挂着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我想知道这本书背后的故事,而和作者王大可聊完后,我发现,与其说这本书是她对现代性的一次失败的攻击,不如说是她用自己的肉身,回到动物性,逃离人类社会种种规训(纲常伦理、丛林法则、优绩主义 etc. )的思想结晶。
这是一个通过 “不再做人”,而真切领悟 “我”,以及 “我” 要怎么做人的故事。
以下是大可的自述:
“应该做” 还是 “想做”?
我从小就笼罩在一种自我感受、本能和天性被深深压抑的阴影里,干什么事情想的都是应不应该,而不是想不想要。
比如我想要一个玩具,别的小孩也想要,我如果去争去抢,大人就会斥责我,不要这样,要学会谦让;比如我刚加入一个新集体,内心里其实不喜欢社交,人多的场合我肠胃会有反应,吞咽困难,但我会逼着自己去,因为我要融入新集体,我要合群;再比如我大学那会儿,想着要出国,绩点要高,就放着自己喜欢的课不选,专门选一些给分高的课,就连正常的吃饭睡觉需求都不能满足,想吃肉,不行,我应该吃蔬菜,想睡觉,不行,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
规训感是一点一点加重的,内心的反抗却早有迹象。小学五年级我写命题作文 “给我一点时间”,写了一只在地面生活了很多年的蝉,它这一生的梦想就是有朝一日能够蛹化,站在树枝上放声歌唱,然后我写了一个小男孩,他很调皮,很不道德,在蝉梦想快要实现的那一刻,眼睛也不眨地把它摁死了。
道德的写法应该是小男孩觉得蝉好可爱,要保护它,可是我没有那么写;唱歌也是一件特别释放的事情,可以看出那时候,我的内心还保留着对天性的渴望,和对道德压抑的抗拒。
越长大,约束自己的论述就越多。小时候大人教的是一套,课本上的知识又是另一套,不同书本教得还不一样,文学作品基本上是不道德的,比如茶花女、安娜卡列尼娜,跟随内心的指引,激情放肆地活,哲理性的作品又是非常道德的,为了大爱、为了全局、为了某一种更宏大的东西去规范自己。我禁锢在两者之间,内心冲突特别激烈,能感受到身体里有两股力量,一股在哭泣,在嚎叫,想要表达,想被看见,一股在往回撤,自我消除,自我磨灭,照本宣科,照着模版活。
以至于我读大一的时候,严歌苓来我们学校做讲座,我举起手就提问,“文学是情感的表达还是道德的规训?” 她回答说,“是情感的表达”。这句话真的救了我,我想冲出去,冲破社会加诸于我的种种规训,为什么孔融要让梨?人为什么要合群?为什么要社交?我是谁?我应该如何行事?什么才是好的,正确的,良善的生活?
“回到动物性”
我本科读的是生物,四年下来实在是厌倦了做一个实验室里重复旋转的小齿轮,收着一管管 DNA,养着一瓶瓶细胞。课余时间,我做自己感兴趣的研究,写过关于 “鸟类出轨” 的论文,大四申请季,我犹豫着转行,从一篇婚外情综述的参考文献中挖出了我在牛津的导师,一拍即合。
在牛津,我专门研究野鸡的性行为,是一个实验狂魔,过着非常争分夺秒的生活,因为我要就着鸡的节律,早上 5 点多钟过去,做到晚上 11 点,连着做 30 天,休息两天,再做 30 天,再休息两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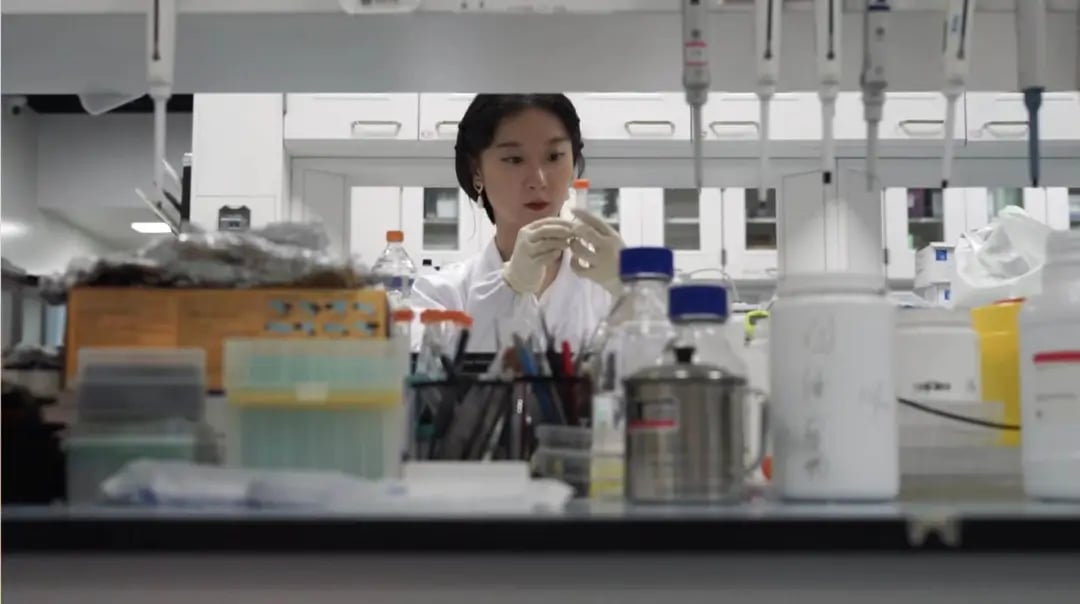

回到动物性,是一个重新审视人类社会种种规训的过程,我拆掉了一些墙,又长出了一层壳。
一开始,我总是从人类的角度去思考动物。主流人类社会很长一段时间内是父权制的,我就会推论动物界可能也是这样,但其实别说父权制了,连社会性的动物都很少。像果蝇这样的昆虫都是自己觅食,大部分哺乳动物也都是独居,繁殖季才会出来找配偶,爬行类动物诸如蛇和蜥蜴也是独来独往的时候多。
这一点特别冲击我,原来人作为一种动物,天性不喜社交,是无比正常的一件事,反过来想,所谓的 “人是一种社会性动物”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会不会是建构出来的?
研究原鸡之前,我假定动物界里的雄性和人类男性一样,无性不欢,但做了两年实验我才发现,每次屁颠屁颠跑来交配的总是那几只,其他的大部分公鸡,要么在漫步,要么在教训别的公鸡,而且鸡的交配时间又特别短,从开始到结束可能就 5 秒钟。
性在鸡的生活里只是一个很小的部分,反观人类社会,是不是对性的重要性过分夸大了?没有性生活就是可耻的吗?男人真的满脑子想的都是性吗?这些都是要打问号的。

以前我认为,强者建立秩序,弱者被淘汰,后来发现这种视角太狭隘了,弱者不甘于被淘汰,它们有很多法子可以活下去。
流苏鹬是一种特殊的水禽,雄性有三种形态,黑色的是地主阶级,白色的是流浪汉,另外还有长得和雌性差不多的伪装者。
因为外形酷似雌性,它们闯入地主阶级的领地时并不会被驱逐,甚至会引起地主的怜爱,它们会在露馅之前找准时机,以最快的速度交配,再全身而退,这被称为 “替代繁殖策略”。

寄生行为广泛存在于体外受精的鱼类中,睛斑扁隆头鱼,它们有的天生高大威猛、颜色艳丽,它们往往优先占据了最好的繁殖位点,那些体形小的鱼没有办法占领到巢穴,也找不到对象,所以它们会在大鱼交配的时候,冲进去排出精子,再立马跑掉。
而且,规则从来不是单一的,“被操纵” 的下位者也可以创造规则,来操纵上位者。一个简单的理论框架是,不论什么性别,什么等级,能量终究是有限的,如果雄性把能量分给了发育肌肉,打斗能力强,赢得了更高的社会地位,就少了一些发育精子的能量。社会地位高的雄性精子质量低,这就给了拥有大睾丸的 “下位者” 翻盘的机会。
雌性也是如此,雄性鸭子拥有巨大的生殖器,这样的生殖器有助于强迫性行为,但雌性鸭子的生殖道已经在旷日持久的保卫战中进化成了复杂的迷宫,而且和雄性生殖器的螺旋方向相反,母鸭子生殖道入口处135度的大转折足以掰断丁丁,如果得不到雌性的辅助,雄性鸭子不仅无法实现交配,还很有可能连丁丁都保不住。
明白这一点之后,我仿佛一下子解脱了。我讨厌丛林法则,讨厌弱肉强食的价值观,但又无法抵抗地被这种价值观收编,甚至矮化自己。
2018 年的时候,严歌苓来牛津讲座,结束后我和几个同学围上去和她聊天,她说自己年轻那会儿也不懂得表达自己的需求,特别在意别人的想法,年纪大了就放开了,想说什么说什么,我当时在心里暗想:你是大作家你可以,但是我不可以。
我从小压抑自己的需求,是潜意识里认为,只有足够强大了,有话语权了,才可以表达自己的需求,才可以说我是谁,我想要什么,否则没有人会在乎,也没有人会尊重。
但回到动物性,让我看到,强弱是动态的,变化的,一个标准下的弱者,在另一个标准下可以是强者,所以弱并不是问题,单一的社会,单一的审美,单一的价值取向才是问题。
“进化论解释力很强,但问题在于你满不满足”
越往深处走,我越发现人类社会塞满了无处不在的文化建构。
人们歌颂无私和爱的高尚,但这些 “品德” 动物身上也有。比如,刚性成熟的后代不去繁殖,而是帮助父母养育后代;斑胸草雀在配偶孵蛋的时候,会站在巢周围的树梢上放哨,有蛇出没的时候通知配偶逃跑。
在人类看来,这或许是爱的献身,但演化生物学的解释是,这是为了种群的利益和基因的传递,为了活得长和生得多,那么人类的无私和爱又有什么高尚呢?进一步说,哪里来的无私和爱呢?
回到动物世界,我褪去了一层壳,又长出了一层新的壳,演化生物学消解了爱,把崇高的价值也祛魅了,2017 年底,我回国拜访武大哲学院的陈晓旭老师,老师问了我一个问题:“进化论解释力很强,但问题在于你满不满足。” 那时我还不懂这个问题的含义,于是说:“满足。” 时隔一年,我再见到老师的时候,我说:“完了,我现在不满足了。”
做动物实验赋予了我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我不仅知道这只野鸡的过去,还可以规划它的未来。有一段时间,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也是一个缸中脑,肉身在一个水缸里,大脑接上了各种管子,所有的脑活动都可以被第三方读取,我是没有自己的心灵和自主权的。
个体就像一个基因容器,我既不能决定我的出身、样貌和肤色,也无法改变自己的性格和思维方式,周遭的环境、人事物也不受我控制,所有东西都不来自于我,那么我是不存在的吗?如果孔融让梨和合群只是人类为了种族繁衍而建构出来的谎言,那么我到底是谁,个体的存在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一直有焦虑症,在牛津做心理咨询的时候,我问了咨询师一件我要去做的事,她问我:“你想做这件事吗?” 我说“我应该做。” 她又问:“你怎么连你想什么都不知道呢? ”
后来我上了一门哲学课,哲学老师是一个游离在体制之外的野鹤般的人物,可以想象这个人和我的生活状态多么不一样,那半年我几乎都在和他吵架。
当时班上同学大部分是夜猫子,而我习惯早睡,有一次上课上到凌晨两点,我又困又倦,强忍着愤怒问他,“你怎么可以上到两点钟?” 他当即反问我,“你想早睡为什么不说?” 我说我没机会说,他告诉我,你要学会表达自己的需求。下一次他又上到两点钟,我这次火了,质问他 “你都知道我要早睡了怎么还上到两点钟?” 他理直气壮地回,“这次你还是没说啊,我以为你不困。”
过去我感受不到自己,感受不到现在,永远在用上帝视角规划我的生活,什么节点 “应该” 做什么,用各种训诫和教条来指导自己的生活,以使未来的我有什么样的成就,就连去听音乐会和歌舞剧,脑子里想的都是我 “应该” 去接受艺术的熏陶。
而现在,我终于感受到自己了。我不再依附于一个宏大的理论或者千百年来的社会规训,我此刻的感受和意志就是我的锚点,我想吃肉就吃肉,我想早睡就早睡,我看自己喜欢看的书,我和喜欢的人交朋友。我发现,遵循自己的内心,诚实地活着,用真心换真心,也并不违背道德啊。

这种内心的转变也体现在了日常生活里。前年我来了中国科学院,同事都觉得我是个直肠子,需要什么帮助直接说,不想去的社交我就不去,相处起来又舒服又轻松。这本书的编辑也说我文字的风格都变了,2017 年刚写 “它们的性” 专栏的时候,内心有一股要冲破一切的愤怒,文字是有劲儿的,而越往后写,我越娓娓道来,开始呼唤爱与和平了。
我不再像一只无头苍蝇般地,撞上哪只壳,就将自我寄居在厚厚的壳内了,如今这些曾保护我也钳制我的壳都已经褪去,只剩下一个剔透柔软的躯体,而这就是我本来的样子。
// 作者:Randy
// 编辑:zqq
// 设计:板砖兮
// 排版:sojulee,赵四
BIE别的女孩致力于呈现一切女性视角的探索,支持女性/酷儿艺术家创作,为所有女性主义创作者搭建自由展示的平台,一起书写 HERstory。
我们相信智识,推崇创造,鼓励质疑,以独立的思考、先锋的态度与多元的性别观点,为每一位别的女孩带来灵感、智慧与勇气
公众号/微博/小红书:BIE别的女孩
BIE GIRLS is a sub-community of BIE Biede that covers gender-related content, aiming to explore thing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females. Topics in this community range from self-growth, intimate relationships and gender cognition, all the way to technology, knowledge and art. We believe in wisdom, advocate creativity and encourage people to question reality. We work to bring inspiration, wisdom and courage to every BIE girl via independent thinking, a pioneering attitude and diversified views on gend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