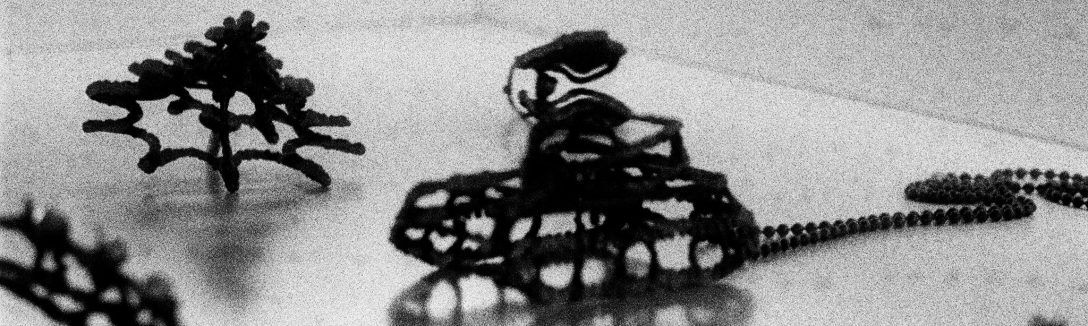小説//法律無法禁止的東西
寫給香江兩岸英雄的人民。
那一天阿城像往日一樣,在街上閒逛 ——至少逛街還是不犯法的事。逛街之不犯法,就好比秋雁乘空不賴噴氣引擎的動力:飛翔是秋雁的天性,而蜿蜒的街巷則是「法」在大地上的勒銘。人多欲求便捷,但再泥濘盤曲的通道,也沒有人能夠化曲為直,不由道路的導向,而直愣愣徑向終點衝去的。除非是能穿牆鑿洞,飛簷走壁,或有特異功能之徒。故而街道本質上是一種規馴的工具,首先規馴了我們的雙腿,使其不再邁向野嶺荒山。規馴了的雙腿又進階規馴了我們對空間的想像,「酒肆」由此擴充為「三岔路口的酒肆」,「家」由此只存在於「某街某巷的家」。而正因此,逛街本質上是此種規馴的反覆演練,是「法的精神」由以深化貫徹的制度手段。那自然,逛街,還是不能違法的。
阿城的腦袋瓜子沒有想這麼多,他還徜徉在昨夜殘燭照影里的女人,女人的雙股之間,汗毛和肌膚的摩挲 —— 這是他沿街挑賣了半年的冬菜換來的。冬菜不是生活必需,閒來解饞或下飯卻是極好。所以無論貧富,多少會買點。賣得的錢,扣去了平日的酒食,還有餘的,阿城就攢著。攢夠一年半載,在那末流的妓館,阿城就也能搬演一齣「賣油郎佔花魁女」的戲碼。阿城的逛街,這樣說來就也不那麼閒了。就好比「守法」是因為法有使人徒善遠罪的好處,阿城的「逛街」也是因為街上來往的時常有要買冬菜的主顧。反之就都不然。
冬菜裝在甏裏,甏用麻綫懸在竹扁擔的兩頭,幾乎沉到地上。扁擔支在阿城的肩上,阿城每向前邁一步,冬菜甏就顛一顛,扁擔也隨之吱吱嘎嘎地響。過眼的都不禁暗忖,若是下一秒這扁擔再也經不住分量,啪嗒斷裂,那兩個瓦甏可要在這青磚路面上砸出多大的響聲來!阿城就這麽一步,一顛,一響地挑著,並不時沿街吆喝。還未至街口,不提防一陣腹痛,逼出一額頭的冷汗。兩股戰戰,愣是無從發力。阿城只得卸下擔子,手一撒,那壓彎了的扁擔就順著肩滑落了下去,噹一下敲在甏沿上。阿城捂著肚子蹲在甏旁,心想定是早前啃的半個饢餅在作怪。饢餅是從前街老婆子家的雞欄裏撿出來的,阿城想:雞吃餅無事還長肉,而人吃鷄又無事,那這餅人也是吃得的。與其偷鷄落得一頓打,不如撿了飼雞的饢餅,既能果腹,四捨五入,還算是吃了雞。可這腹痛也不分時機,若是未進城,儘是野地,哪裏不是方便的去處。現已至城中,再沿街脫褲子,若是來了警衛糾察,行不成方便,還要弄個人菜兩空。
正焦急間,阿城一拍腦袋,想到大帥府前的那座「義厠」,正在街口轉角處。本縣大帥向來跋扈成性,藉勢作威作福,縣民都叫苦不迭。大帥也知道人心向背,便滿口仁義禮智,説要修齊治平,但盡是空頭支票,唬不了縣民多久。有一參謀便進言,說要綏靖民憤,收攏民心,大可不必談什麽仁義,只要解決一件事,那便是「厠」。別看這字聞起來有味,談談確是大道理。衣食住行,哪樣不歸結到一個「厠」字上?無「厠」則衣物儘溲,七尺男兒也要穿著尿布上街;無「厠」則飲食皆坏,剛出鍋的麻球要與糞球在一塊擺放;住房無「厠」則床頭桌腳滿佈污穢,行旅無「厠」則舉國街巷便是屎溺。所以「厠」才是民生之重,大帥只消在帥府門前立一「義厠」予縣民方便,縣民便知大帥愛民之深,衣食住行都受惠顧。甚至可以撤去糧農,住房,交通等等各繁冗的中央政府部門,只消一「如厠部」便能一勞永逸。大帥若再兼任「如厠部」部長一職,那原先三府六院各種政府經費,不都全進大帥囊中。大帥聞言大喜,立馬在帥府前砌起一座「義厠」——黃金鋪面,琉璃瓦儅,丹墀接地,好一似全縣城的最高機關。
阿城是下等人,平時豈敢奢望在琉璃瓦下拉屎。然而當下情急,別無他法,撂下膽子,便捂著後庭飛速向轉角的「義厠」飛奔去,蹬蹬蹬幾下功夫踩上了丹墀臺階。大帥這時正好也在佝僂著背,坐在馬桶上「打持久戰」。一邊用力,一邊手裏還在把玩著那天早上剛搜刮得來的一把新式手槍。那手槍是泰西製造,小巧玲瓏,又蘩飾精雕,賽過工藝品,大帥十分喜愛。帥府的馬桶間的窗子剛巧正對府外的「義厠」,當然「義厠」裏的阿城是看不到另一邊的大帥的。那時間,阿城倏地拽下了褲子,撅高屁股,正要享受那一瀉千里的快感的時候——砰地一聲洋槍在大帥手裏走了火,流星子彈穿透帥府的窗戶,徑直飛向「義厠」。「義厠」縱有金粉貼面,也不過是一座木板隔間,哪裏經得住洋槍的子彈。阿城便倒在了他的泄物,和血水裏。
阿城的死并未引起什麽轟動。「義厠」被打穿了的墻板,也迅速被換新,又粉上金,好像無事發生一樣。要是説大帥殺人,也不是稀奇事,殺在「義厠」裏,倒開一先河。但一賣冬菜的貨郎的死,往往又是無人關心的。大帥本也不在意阿城的死,還是照舊橫徵暴斂,驕奢淫逸,順帶派人游説中央,盼著早日坐上「如厠部」部長的肥缺。可阿城畢竟是死了,「義厠」畢竟是沾了血,總歸是蟠首的豐碑上落的一坨鳥糞,或是白羅衫上的一個燙洞,他人或許不曉,進了風則皮肉自知。大帥自此總是不由自己地多望一眼「義厠」,好像生怕會出什麽鬼魅。他越是多望,便越是生疑。往日少人光顧,現在每分每秒都有來往的脚步聲,厠門的開闔聲,和便溺的墜水聲。大帥幾乎都能聽出如厠者是在拉稀還是便秘,前晚的吃食有幾分油水,入厠前又喝了幾碗薄粥。
也不知同阿城的死有無干係,在「義厠」解手的人倒真的越來越多。「義厠」前更排起了隊,先是兩三人,一個個縮首顰蹙,急慾方便的樣子。興許是冬菜咸膩,不利腸胃,如今死了賣冬菜的,往日的食客倒都潤腸通便,糞量大增了。爾後便不然,排隊的人一天比一天多,隊伍一天比一天長,從清晨排到晌午,從晌午排到日暮。排隊的人也不像是尿急便急得樣子,往往都交頭接耳,閑談致興。大帥更是越看越疑,越疑越怒,暗自估摸一定是縣民知道阿城橫死於流彈,爲其鳴不平,就在「義厠」前貫以人龍,以示憤懣。修「義厠」收買民心不成,反成了縣民用以陳情的鳴冤鼓。「反了反了!用公共厠所來反帥府,真是他娘的一大發明!」大帥咆哮道,「敬酒不吃吃罰酒,給個金馬桶真他娘當福氣了,非得老子給點顔色看看」。嚷嚷著抄起了那把雕花的洋槍,噌噌噌地就往外奔。帥府那兩扇黑漆漆的烏頭大門嘎嘎吱吱地對開,大帥跨出門來朝著「義厠」周遭的人群便是幾槍,乒呤乓啷,哐哐郎當,直打得人群抱頭四竄。「從今天起立一新法,誰都不准用這「義厠」,也不准在老子的地盤裏拉屎撒尿,給老子看見,他娘來一個斃一個!」
從此封了「義厠」,帥府門前也清净了幾許。大帥洋洋得意,雖然修此「義厠」沒能籠絡人心,靠那不長眼的槍子,一樣治的服服帖帖。舊日還未修「義厠」的時候,往來縣城的人大多還能尋個隱蔽之處出恭入敬,如今封了「義厠」,又立了新法,城中大凡不是私人宅院的範圍内,皆不得隨地便溺。大帥又遣了一隊「防厠警」,日夜在「義厠」周匝和大小街巷搜捕犯拉野屎者,繩之以法。家住城内的人,要有厠意,回轉家門便可一泄了之。不然的話,生計勞作多少受點影響。街上的商販漸漸地都移到城外不受新法管束的地方經營,縣城内就也凋敝不少。
大帥新近物色了一個花魁小姐,紅唇蜜嘴,豐乳肥臀,十分歡喜。這天便偕同乘著新式的敞篷轎車,要甩甩派頭,耍耍威風。大帥抱著小姐,小姐抱著熱水袋——衣襟單薄,高開叉的旗袍裙,經不得寒風。車行到半路,那小姐忽覺前庭緊脹,大概是清早飲了太多的茶的緣故。可車中無處方便,又怕觸了新法丟了腦袋,慌亂之中縱生一計:那熱水袋只灌到一半,尚有餘裕,靠此解決,豈不是偷天換日不爲人知。「大帥您看那下花叢有人在拉野屎哩。」那小姐尖著嗓子說,大帥立馬從車裏探出頭張望,小姐順勢撥開熱水袋的橡皮塞,伸進裙下,口中又作鳥叫聲噓噓然。「哪呢哪呢,哪兒他娘有不要腦袋的人呐」大帥扭回頭問小姐,見她依舊懷抱著那隻熱水袋,喃喃道「呀,大概是看差了,大帥如此的威嚴,哪有人敢觸犯新法的呀」。大帥不知什麽緣故,一時口焦,出門卻不曾帶得飲料,一眼便看到了小姐懷中的熱水袋。河水也是水,井水也是水,這熱水袋裏的水不也是水。「媽的小娘們眼睛長歪了吧」駡駡咧咧地就奪過那隻熱水袋,也撥開橡皮塞,咕咕嚕嚕地往口中灌。獅子老虎狗,黃漿入帥口,大帥倏地就噴薄而出,惹得一車的騷臭。他一巴掌扇在小姐的粉嫩嫩的臉頰上,即刻喊停車,著車夫沿街邊的人家商鋪去取净水來。不多時,車夫竟空手而返,結結巴巴地答說,四下的人家都閉門不出,不是在拉屎不便啓門,就是在急著要趕去城外拉屎的關頭。大帥聞言雷霆大怒,「反了反了,用拉屎撒尿來反本帥,真是他娘的一大發明!」
次日帥府門前貼出了一大張紅榜告示:「本帥即日頒佈新法,無論城内城外,本縣人一律不許拉屎撒尿。私家厠所一律拆毀封禁。如有違者,槍斃示衆。本縣人若勾結外縣,偷赴便溺,同罪論處。」大帥揚言這是天下第一法,治國之良策。因爲焚書坑儒,禁言噤聲,全是下計,禮不下庶人,庶人更不識字,唯有拉屎撒尿是其謀逆造反的窮途末技,故而只有「禁厠」這一條才能根絕後患,永固金甌。大帥更要獻言中央,做不成「如厠部」部長,不如當個「禁厠部」部長罷。
新法一出,縣民譁然。耆老鄉紳們也有聯名抗議的,但終敵不過大帥的槍械彈藥。試法的成了新鬼,或轉之地下陣綫,有外縣關係的都移了民去,抗法的也疲於無成,時間一長,倒也習慣過上這種不用拉屎撒尿的日子。但人終究不是貔貅,只進不出,貔貅吃的是金銀珠寶,人吃的是五穀雜糧,五穀雜糧從塵土中生,最終也是要零落成泥,化歸塵土的。吃下的不能不被消化,被消化的殘餘不能不被排泄。可穢物一落了地,便要歸入「拉屎撒尿」的門類,觸了新法,罪該槍斃。那怎麽辦呢,有人説要麽就兜著吧,於是就兜著了。於是這一縣城的人,不分時間場合,糞意降臨,只管讓它順流而出,兜在底褲裏。底褲衲得寬且大,襯了油紙隔水,外加長衫罩袍,縱是兜了一日的屎尿,旁人也不易察覺,自然不會被大帥的警衛糾察發現了。
日子這麽過著,穢物也天天這麽兜著,可是有一個人是不用害怕觸法的,那便是大帥自己。大帥大概不曾想過人非貔貅這種道理,以爲槍在手,權在手,以槍治法,以法治人,沒有什麽不成的事。大帥依舊每天在帥府的馬桶上解手,解手時照舊把玩那雕花洋槍或其他新繳來的玩意。縣内的空氣儘彌漫著溲溺的氣味,漫城皆似腐蠹,惡臭雲天。縣人倒是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了。大帥先是掩鼻,又只能居帥府不出。可帥府中的上下士官佣仆,為不觸法,也只能把屎尿兜著。大帥躲到東,躲到西,閣樓地窖,前庭後院,也覓不到一處芬芳。抓耳撓腮間,一拍腦袋,想到了之前封禁的那處「義厠」。自封禁以來,數月不曾有人駐足,方圓之内,皆是禁區,鳥都飛不過一隻。「義厠」有丹墀引地,筑在高臺之上,有風颯然,倒成了最後的净土。
説話間,大帥徑直衝出帥府,翻過警戒的圍欄,手脚并作地就爬上了「義厠」的臺階。隨著就是砰的一聲,大帥噗倏跪倒在「義厠」門前的最後一級石階,大帥的身子定格了,僵直的臂膀剛巧夠到厠門的門閂。
大帥被飛來的流彈擊中。有人説是義士舉槍。有人説那是大帥自己的軍士,不過在執行「入義厠則槍決」的新法罷了。
但有一件事是確定的:有些東西是法律無法禁止的,比如拉屎撒尿,比如自由,又比如捍衛自由的自由。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