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要如何在俗世中行走、戀愛、老去:記黃燦然《詩合集》新書台北發佈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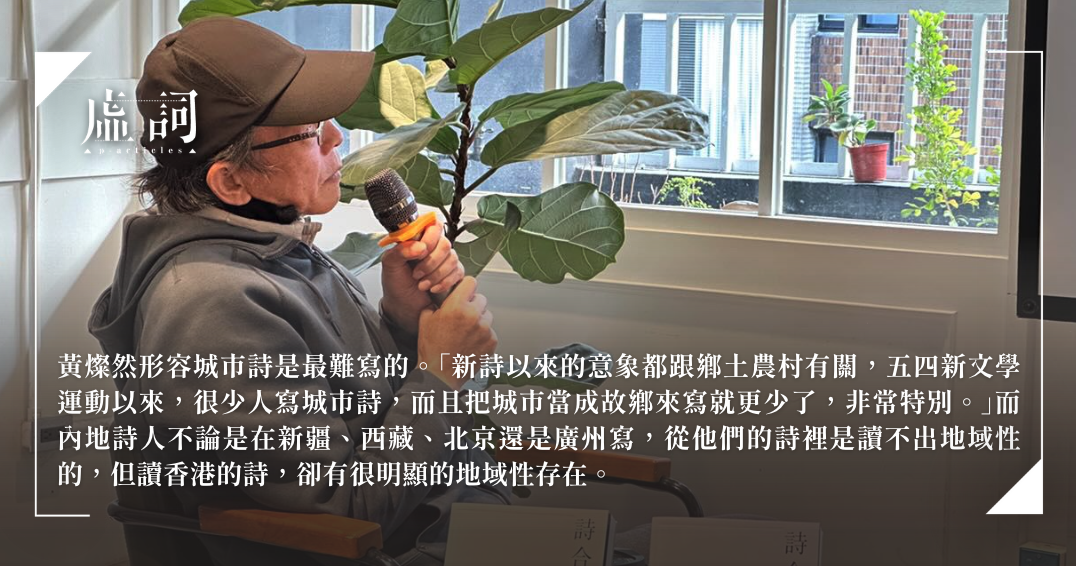
文|陳諾霖(現就讀於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文學跨域創作研究所)
「我們對這個世界一無所知,除了在詩裡。哪怕詩人是半神的存在,有能懸浮在半空中的眼睛,那不是為了讓詩人成仙成神,而是為了能夠更寛廣地俯視這個世界。如果沒有世俗,也就不可能有詩歌了。」——詩人黃燦然
日前,黃燦然的新書《詩合集》發佈會在台北春秋書店舉行,詩人親臨主講,本書責任編輯鄧小樺主持。黃燦然抵台便先後出席金馬影展及讀詩會,行程雖奔波,抵達老宅書店迎見滿屋讀者時,還是雀躍地笑說要與大家一起好好讀詩。
由冥想至苟活 如圓的詩旅
《詩合集》收錄了黃燦然由1985年至2021年所寫的六本詩集,由卷一《冥想集》、《靈魂集》、《奇跡集》,到卷二《發現集》、《洞背集》、《苟活集》,他的詩旅一如詩集名字般,奧妙地相互對照,於世俗散步又再歸返。
黃燦然從《冥想集》說起,《冥想集》不論在形式上,還是精神的跨度上都極具實驗性:「酸甜苦辣都在裡面,很多人可能一輩子就寫這麼一本詩集了。」到他三十來歲寫《靈魂集》,轉而追求語言及意象的精練,風格趨近超現實主義,「很多超現實主義的詩人經不起精神的內耗,靈魂崩潰,都很早死。」黃燦然笑言年少詩人總以為自己有用不盡的力量,消耗精神、身體去餵養詩,靈魂困在頭腦裡面,並沒有堅固的外在世界,因此也容易患上抑鬱症,他曾經也如詩史中的詩人,崩潰過,幸好沒死罷了。
幸運的是,黃燦然剛好被身處的香港喚醒,他形容當時「簡直像戀愛一樣」,有種睜眼才突然發現世界新如初見,眼睛所觸及的一切皆觸動他。《奇跡集》正是從黃燦然生病寫到健康,洋溢着他觀看生活的深情。他與世界相互打開擁抱的同時,所喜歡的詩人也起了變化,開始關注歐洲的詩人,如希臘的卡瓦菲斯。寫的詩也受信仰、音樂影響,他每天會沉浸在馬勒的音樂裡兩三個小時,才開始寫詩,完成《奇跡集》時,他便把其獻給馬勒。
馬勒慢版音樂對黃燦然的吸引力一直延伸到《發現集》,他已經不滿足於詩一般的音樂感,他嘗試在詩行裡複製馬勒那種非常緩慢、低沉的節奏,也對長句、詩調比較慢的詩人感興趣,於是黃燦然的詩又回到各種實驗裡。在黃燦然差不多五十歲時,從香港搬回內地,重回童年陪他成長的山水之間。他的前四本詩集一直以來也在寫城市,寫出城市既是天堂,也是地獄,但寫《洞背集》時從城市回歸自然,農村的風貌也染上了他的詩,寫成了現代的山水詩。
「你看到樹葉一動,立馬就有感覺了,回家你就開始寫一首詩,這是一種幸福。」詩旅彷彿不由黃燦然主宰的,有時更是詩撞上詩人,他只是一名捕捉靈光一閃的人,他唸出〈車過葵潭〉時便興奮地說,這是詩自來的一刻。
〈車過葵潭〉
一個、兩個和更多
更像是山中湖的池塘,池塘邊
幾十、幾百、幾千只白鴨子
彎著脖子在休息。一個
戴斗笠的農婦,用扁擔挑著糞土
走在田埂上。一座、兩座
和更多墳墓……
2019年,黃燦然曾一度跟世界的關係斷裂開了,眼睛雖睜着看,卻失去詩靈的感知,看一切也毫無感覺,超過幾年的時間沒法寫詩。不能寫詩的詩人與一般人無異,回歸生活的本質,「還俗」的黃燦然卻被斷了七情六慾,無法體驗世界回饋他的喜怒哀樂,他形容自己是再次被封鎖起來,日子過得宛如行屍走肉。
直到編輯這套《詩合集》時,才又被打開,可以寫詩了,而且寫的詩又再次趨近抽象跟超現實主義。黃燦然的六本詩集有如一個圓,被某種玄妙的力量或拘禁或釋放他的詩靈,讓他從抽象的內在世界,走到現世,又回到抽象的風格。
*
黃燦然坦言早已斷了在香港出版詩集的念頭,覺得沒有機會。在香港出版詩集無利可圖,出版社僅印幾百冊,往往落個送也不是、賣也不是的下場。但他其實一直心懷把所有單行本詩集完整出版的願望,因他的詩集大多已絕版,包括第一本詩集《游泳池畔的冥想》及《我的靈魂》在市面上是買不到的,只有在舊書網上被高價拍賣。黃燦然寫下六本詩集,合共過千首詩,讀者卻讀不到他的詩,實感可惜,才有了出版詩合集的想法,讓讀者可以一鍋端地把他的詩完整帶走。恰好在本年四月回港時,與鄧小樺聊起這想法,重燃起黃燦然的希望,並迅速地行動起來。
黃燦然既是詩人,是翻譯家,也是位成了精的讀者,他閱詩無數,家裡更收藏各式各樣的詩集,但凡是他所愛的外國詩集,即使只是紙張或字體的版本不同,他也會收藏。「詩集的不同排版是會直接影響閱讀的。」與鄧小樺討論《詩合集》的制作時,黃燦然便一一翻閱他的珍藏,一本本細說,有來有往。「詩合集」一詞更是黃燦然由Collected Poems翻譯過來,不同於讀者較為熟悉的Complete Poems(全集)或Selected Poems(選集),Collected Poems是把詩人的單行本詩集,收集在一起,也會按照原本單行本的次序來排列。
黃燦然非常堅持,要用最簡單的美學去結集他的詩:「詩是不應該有任何裝飾的,因為詩是不允許被任何東西去分散注意力的。好的排版是要讓讀者無法察覺有排版的痕跡,也許花俏的裝飾會讓讀者因感有趣而買詩集,可不會真正讀進詩裡去。」《詩合集》採用了讀者很少見到的「順排」,即詩與詩之間不會相隔一頁,順連排下去。看似簡樸的詩集,可細緻至行數、字號也是經過一番對比研究過的,小樺笑說:「本來已經決定好是每一頁二十九行,後來校對好給黃燦然看,他說,還是二十八行吧。要知道,只減一行也需要非常耗工夫地重新排版,可就是看到黃燦然對細節很講究。」
香港詩人以城市當作故鄉的本土詩
香港作為黃燦然寫詩的養份,他談到香港詩人非常獨特之處,在於香港詩人與土地的關係。「與內地和台灣詩人完全不同,香港詩人就在一個小地方寫他們的小語境。」香港詩人有能力翻譯、閱讀大量西方的詩,可就是很聚焦眼前土生土長的土地,寫山寫水,寫填海、變遷、房子清拆與重建,詩人與土地的連結,黃燦然以中國的古典詩比擬,有如杜甫一路從長安寫到成都,詩歌都是由走過的土地而生發出來。
台灣有鄉土詩,可真的是寫農村鄉土,香港的本土詩卻是城市詩,黃燦然形容城市詩是最難寫的。「新詩以來的意象都跟鄉土農村有關,五四新文學運動以來,很少人寫城市詩,而且把城市當成故鄉來寫就更少了,非常特別。」而內地詩人不論是在新疆、西藏、北京還是廣州寫,從他們的詩裡是讀不出地域性的,但讀香港的詩,卻有很明顯的地域性存在,甚或是具體到一個區、一條街道。
黃燦然吸取了香港本土詩的養份,不少詩作也是拔地而起,例如他有好幾首詩以將軍澳的路名及醫院作主題,寫他媽媽及姐妹們生活的地方,寫媽媽住院。黃燦然在發佈會中,選了幾首詩朗讀,其中一首便寫香港電車,他以詩人之眼定格、放慢日常之景,讓人動容。
〈國王電車〉
我希望又不希望好人這麼少。
午夜。
我在紅燈前等過馬路,看見電車剛好駛過,知道趕不上了,便慢吞吞往電車站走去。但電車還停在那裡……司機在等我!
就像他是國王,他的馬車在等我;或者我是國王,我的馬車在等我。或者他是好人,正在等我;或者我是好人,受了神恩。
我坐在上層靠窗的位置,尋找天使的痕跡。窗沿的舊木框微微發光。
我想起幾次看見電車還停在那裡,等某個追上來的乘客。不管他是好人,正在等他們;還是他們是好人,受了神恩。
我希望又不希望他是同一個司機,這個司機。我希望又不希望好人確實這麼少:
有一天他的電車將坐滿他等過的乘客,他們互相不知道彼此是好人,但都知道他是好人,都希望又不希望好人這麼少;
誰也沒意識到車燈漸漸暗淡,因為車裡通明。因為所有眼睛和心靈裡都有個天使在發光。
越過詩浪漫的宿命 黃燦然要寫成熟的詩歌
黃燦然在三十多歲寫詩時,縱觀詩的歷史命流,發現新詩被當成一種浪漫的宿命,像徐志摩、余光中那類浪漫、音階甜蜜的調調。黃燦然指很多詩人在二、三十歲就完成他們作為詩人的生命了,而他也到了承擔宿命的年齡,當時年過三十五,已然成熟,承受着時代的變遷、家庭的壓力、中年孤獨、身體痛苦的各種施壓,他能找哪些詩人去給他安慰和啟發呢?
「詩歌變成青春期的詩歌,沒有成熟的詩歌。」黃燦然談有如台灣詩人瘂弦,也是在三十多歲以後就沒再寫詩了,「年輕的時候讀瘂弦的詩,很喜歡,讀到他最後一本詩集《深淵》,就真的掉到深淵去了。讀者還想知道詩人怎樣面對生小孩、政治動盪,應對無常變幻的外在世界,詩人對生命有什麼新的反省,對詩歌有什麼新的想法。可到了四、五十歲想讀瘂弦的詩,沒了。瘂弦還在,可他再也不跟你發生關係了。」
面對自己的時代,有些解答是前一代的詩人無法提供的,黃燦然會在中國古典詩及外國詩人去尋找榜樣,讀中年詩人、老去的詩,還是讓黃燦然更有信念去寫出成熟的詩歌,他不但要寫一個中年人的生理變化、對生命的思考,他也寫周圍的世界,觀看自己年老的父母、公園裡的老人,老人是什麼,老去是什麼。而他相信成熟的詩歌是可以一路傳承下去,延續詩的生命,如同延續他曾被安慰一樣的安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