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這一代:傷痕的權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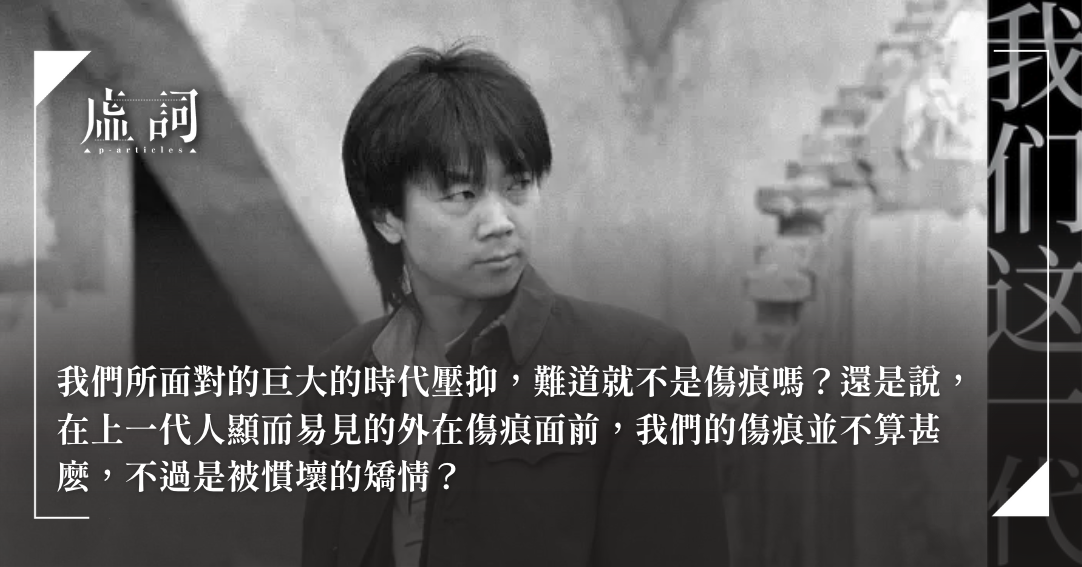
文|王崢
在新加坡的圖書館,偶然讀到了攝影師肖全所作的作品分享及報告。他通過攝影的鏡頭記錄了上一代人(五零後,六零後)的青春群像,並展示了彼時文化界的不同人物在八十到九十年代初的真實狀態——有迷茫,有自信,但更多是某種熱切的希望。對於這代人來說,八十年代中國大陸的基調是「傷痕」,而這個詞匯蘊含著兩層意思:首先,他們看到了傷痕並承認其痛楚;而後,他們需要尋找使傷痕癒合或至少與之共存的方法。肖全所拍攝的大部分人,便是通過藝術的媒介,去尋找這些方式,並獲得了巨大的共鳴和回響。與其說肖全記錄的是一代人的傷痕,不如說他記錄的是癒合的過程。與此同時,這也讓人思考:作為年輕觀眾的「我們這一代」又該被如何記錄和總結?尋找回答的努力往往是復雜的,一方面我們必須確認這一代人的某種共性和特性;而另一方面我們也必須看到「承前啟後」的關係,這種關係不僅僅是時間上的,更是血緣和文化上的。
如果往前看,「傷痕藝術」(包括「傷痕文學」)縱有它們的歷史意義,但它們的缺陷也恰在於傷痕本身。通過上一代人的藝術,這個傷痕實際上並未消失,而是被掩蓋了。雖然掩蓋同樣是一種美學,需要技巧,但這後果是新一代人失去了辨別和分解傷痕的能力。我們到底該如何理解「傷痕」?這種傷痕是否是上一代人獨有,還是在面對痛苦和轉變時,因人性而產生的普遍機制?而處理傷痕的不同方式,是否能給我們,在面對時代時,提供一些可鑒的經驗?
歴史的巨大震蕩是肖全一代的傷痕,那這些傷痕同樣也是機遇。如同細胞的自我修復,新的細胞必須產生來修復舊的孔洞,傷痕同樣是生長的過程,於是有了肖全鏡頭下的璀璨眾人:陳凱歌,余華,芒克等;而對我們來說,如果傷痕被繼續掩蓋,或是「傷」痕變成了「疤」痕,再被覆蓋,那麽傷痕反而成為了一種權力——這讓人質疑:我們所面對的巨大的時代壓抑,難道就不是傷痕嗎?還是說,在上一代人顯而易見的外在傷痕面前,我們的傷痕並不算甚麽,不過是被慣壞的矯情?實際上,我們從沒從上一代真正理解,或聽其說清這個「傷痕」是甚麽,他們好像說了,但甚麽也沒說,便用新的東西覆蓋了。這些東西可以是經濟指數,可以是國際賽事,也可以是故作成熟地成為他們曾經反對的立場。
值得警惕的是,這種壓抑可能是更嚴重的內傷。我們的青春既不是「十八歲出門遠行」,不是「那些憂傷的年輕人」,更不是「小時代」,而是——「大象席地而坐」,是「野馬分鬃」。大象是有力的,而且聰明,但在動物園它只能坐著;野馬是迅猛的,但在旅遊村裏,它只能成為遊客的工具。如果試圖用肖全的鏡頭重新捕捉「我們這一代」的群像,我們這一代的表情該是甚麽呢?也許是疲憊臉孔的集體克制,也是時代縫隙的個體無力。實際上,我們錯過了八零後七零後的巨大商業成功所帶來的,某種程度上的個體解放;也缺少零零後對於二十世紀的懵懂和天真,對於信息時代的自然熟稔。對傷痕無知,對未來茫然,是我們的原罪;但究其原因的巨大壓抑並不能因為無知而緩解,它需要更多的時間,更豐富的娛樂,和更徹底的荷爾蒙——而這些,除了娛樂,或是自娛,同樣是更大的騙局。我們連反思這種壓抑的時間都沒有,就很快成為了下一代人的背景。
但這些也並非意味著我們在面對鏡頭時,只能作為被同情,被觀察,或被質疑的某種符號存在。我們同樣可以把鏡頭轉向自身,或是轉向更多人;我們同樣可以改變鏡頭的角度和寬度。而這一切的前提是,我們必須有意識地從個體的孤獨與掙紮走出,逐漸走向一個集體的反思和總結。這是我們面對和把握鏡頭的方式,也是和過去未來產生關係的必然階段。
正如羅蘭巴特所說:「時間本身就是傷痕。」 作為我們這一代,也許是時候去把傷痕揭開,認清和理解我們所經歴的,並在壓抑中發出最後的吶喊——趁我們還沒沙啞和失聲的時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