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普文章:好奇能殺死一段關係:談的是真理,亦是愛
原文刊於哲學新媒體
《神探夏洛克》(Sherlock) 中有一幕是這樣的:華生的妻子瑪麗,打算向華生交代自己作為殺手的身世,隨即把 U 盤交給華生,任由他處置。華生想了想,問:「你甘心成為我約翰華生的妻子嗎?」瑪麗點頭應允後,華生隨即把那個 U 盤(隨身碟)扔進火堆裡。由相戀至今(華生拿著 U 盤那刻),華生透過與瑪麗日常的相處,建立了瑪麗是何許人家的認知,更愛上以那個認知為基礎的瑪麗。然而,那 U 盤所盛載的正是將他對瑪麗的認知推倒的堆土機。華生知道只要看了,瑪麗已非他熟悉的瑪麗。

秘密作為真相呈現的一種,可互相增進雙方認知的同時,亦伴隨著被拒絕的風險。揭露秘密能將關係昇華,源於愛剛開始並不完整、需要建構。同時,把自己的秘密抖出來,若不被對方接受的話則能摧毀一段關係,源於真相往往具始料不及的特質。巴迪歐認為,愛與真理,一體兩面,兩者均牽涉開創與行動。熟知真理,便明瞭愛,更了解華生面對瑪麗秘密的態度如何演繹出巴迪歐認為面對真理前應當謹慎。
愛,既是開創,亦是斷裂
真理是一種開創;愛亦是。前者開創新的認知,後者開創新的人生軌跡、對對方的新認知。任何的開創皆始於事件。事件往往既是改變現實的驅力,同時它帶來的影響非能用理性預測的特質。我們不能預見這軌跡所引領的終點。巴迪歐因此從愛中看見真理。在愛情降臨前,不知經過多少時間蘊釀,直至當事人心動一刻,推翻了舊有看待雙方的框架,當事人的人生軌跡亦從此改變。它的來臨總是在愛發生後才察覺。換言之,愛非能透過因果關係來捕捉,只能由回溯方式發現。表達形式如下:非因為找到理由才愛你,而是因為對你有了愛意才找愛你的理由。若能用因果關係預測到,那是理性能把握的,也就失去了事件性。
愛與真理亦是與過去的斷裂,這點則從行動上體現。一個人的行動、抉擇,受事情、自我的認知框架左右,認知框架亦構成「我」的元素。我認為事情是 xyz,所以我會作出相應的行動。真理即事件。真理的出現推翻舊秩序、認知,換來的是行動上的改變。接受了真理的人摒棄了舊的認知框架,意味不再受舊框架的指導行事。在愛情中,察覺自己心動的剎那,正是當事人走出舊有的認知脈絡(包括了對自己,或是看待對方的關係)。因為心動,我也不再視對方為陌生人,相處的方式亦會隨即調整。
我永遠愛你的潛台詞
對一個人心動,就是真理出現的方式。有了心動這一刻,才有後來對一個陌生人的全新認知,視對方為自己的一半。愛的真理莫過於對融貫的愛 (integral love) 的追求,藉著開啟一段關係來獲取與另一人的連貫,擺脫孤獨。沒有真理的開創力,追求與另一人融貫的後話也無從說起。真理蘊含新元素,將現實那牢牢的既有結構鬆綁,製造出具備另類可能的空間。那個創造出的空間並非從一開始便是完整,而是靠行動來築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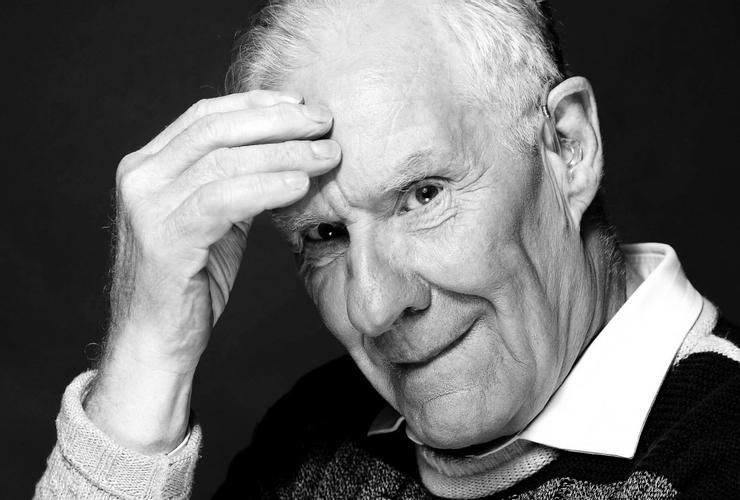
真理瞬間乍現,彷如一個學生問了對的問題那樣,喚起了其他人用全新角度來看待事物,但提問不足以轉化成有秩序的思想與人交流,頂多只構成新命題的契機。真理有一半不可預測地出現,另一半需按著真理的潛在軌跡,以探問的方式把剩下的部份建構出來,彷如作者把故事寫到一半便死了,往後需由其他人接力,按故事的設定續寫下去。
巴迪歐稱之為預期性假設 (anticipatory hypothesis)1。先假設真理的預期模樣,一步步將真理的輪廓勾勒、打磨細節,再將其完整 (totalize)2,如計算不規則形狀的周界時,以劃虛線的方式把沒有呈現出的範圍勾勒出來。建構真理就是個先預設、再建構的過程。
若放在愛情的脈絡理解,融貫的愛只是願景,如何達至則需要持續建構、維繫。僅有愛意不保證戀情會理所當然發生,邂逅完了,當事人沒有把心動轉化為戀情,甚麼事情都沒有發生。愛的例子點出了自主性的問題:當事人能將心動轉化成現實,關鍵在於做還是不做。巴迪歐認為,真理的出現,不是人人能接受,正等如不是人人有勇氣投入一段戀情的膽量。接受了真理形同對舊現實告別。
問題是,捨棄舊的認知框架,就需要新的行事準則作為著落點。一旦接受真理,就是一種向前的跳躍。凡是跳躍皆需要著落點,若是向前的話,就先得跳出舊的認知,以及箇中主導的行事準則,將它們一并捨棄。行動,便是藉著坐落到新的認知框架當中,受之主導,以身在其中來證明其存在之必要。只有這樣,向前跳躍的動作才算完成,否則只是上下跳動,原地踏步。因此,接受真理便必須行動,只有行動上改變,才算徹底從舊有認知的包袱中掙脫。否則,一切只淪為空談。
這裡所說的行動,包括了自我調整、對現實的質問、探究。在關係中,自我揭露來拉近與對方的距離就是典型的行動例子。假如只有你談自己的秘密,對方卻沒有回饋的意思,那只會增進對方對你自己的認知,大概你也會覺得好像自言自語,甚至被出賣。關係是動態的,需以雙方互動來達到融貫的愛。若沒採取行動,真理沒有對當事人產生任何衝擊,假如你沒有表現想進一步拉近關係的意欲,那麼邂逅的衝擊對你來說亦是有限。
而在愛中,預期性假設多半大帶著對愛侶的一些要求。說「我永遠愛你」,看似因情到濃時而隨便說出的一句話,但實際上亦可在透過這句說話索求更親密的關係,其潛台詞是這樣的:我希望你在我說完後也會用同樣的方式對待我。這句話的意義不在於每天愛你多一些,而是透過這假設令愛侶的距離拉近,踏出通往融貫的愛的第一步。因此,結婚是將說出「我永遠愛你」的儀式化。婚姻中的誓言有預期性假設的特質,因為有了這個願景,當事人必須要自我調整,甚至約束自己來達成,這往往是邁向融貫的愛的重要一步。這樣便能理解催婚是怎麼一回事!
融貫的愛的界限
新對象或新命題之所以吸引人,多半來自好奇,好奇則源自一知半解。 因為好奇,才有動力尋根究底。愛情與真理因先天不完整的緣故,造成了探索的吸引力。問題是,到底該用何種力道逼出真理的完整性呢?巴迪歐沿襲拉康的精神分析框架,認為真理乃屬真實界 (the real) 的產物。在真實界裡頭,事情非語言能捕捉,它們總是超出理性預期、理解,一般以創傷、事件的形式出現。真理與理性落入了前者給多少,後者便知多少的關係。兩者之間,主次關係明顯,是動不得的。
欲從真理那處竊取更多,猶如從上帝那處打聽秘密,窺覬「天機」。過份好奇令真理過份暴露,令理性能承受的超出負荷。華生在真相面前選擇自我約束,欲保護與瑪麗的關係,某程度上已點出了過度挖掘的風險,稍有不慎,分分能為自己開啟一個揮之不去,後悔一生的新命題:「瑪麗到底是個甚麼人?我如何百分百肯定她真的會安份守己,而不是對我繼續說謊?」但華生的克制非理所當然的事,若不懂得適可而止就會招致反彈,《安眠書店》的男主角 Joe 正是這樣的例子。

控制慾極強的 Joe,每愛上一名女生,便透過跟蹤心儀對象的去向、追蹤她的社交媒體等途徑,收集對方的戀愛狀態、與甚麼人交往、其生活習慣,來了解這個陌生人的一切。這連串的舉動就是為了避免再受情傷。最後 Joe 亦把女生追到手,但交往期間,不斷去查證對方所說的每句話是否屬實。女生最後發現了 Joe 對自己監控的痕跡,作出強烈反彈,逼使 Joe 非把她滅口不可。
以為知道愈多情人的秘密,便愈能與情人融貫,真理便愈完整。哲學點說,Joe 的變態,便是過度開拓真理的完整性,真理打從開始的不完整,予人極大的誘因去發掘其完整性,但從來沒有人知道界限何在。真理本就毫不妥協地存在,沒有甚麼理由可言。若能將知識的界線預先勾勒,便表示理性能把握的,不再具過度、事件性。
若要回答「真理的完整性的界限」,巴迪歐恐怕會說:不知道!大概當你認為進一步探問將引發無窮後患,那刻便該停止,那些正是不可命名的知識,亦說明對真理的承受力 (potency of truth) 已見底,到時只能見好就收!不可命名的知識便是無法敘述、超出現時能力所理解的知識。換言之,建構真理的過程也有相應倫理:知道該在何時停止。明知有雷的情況下卻偏要繼續挖掘,便是邪惡的開端。邪惡就是不惜代價,欲要言明一切不可命名的知識 (Evil is the will to name the unnameable at any price)3。借用韓裔德國哲學家韓炳哲在《透明社會》一書中用到透明的概念說明,邪惡就是致力追求完全透明。
邪惡就是追求完全透明
韓炳哲在書中道出了現今世代對透明的執著。透明可解作肯定、沒有阻力、去陌生(否定)的意思。不管是情人,或人本就有種不可縫合的距離,不可知、不透明的一面,這種阻力正是來自人的他性(多半以隱私、自主的方式呈現)。每一個人在關係中都是另一人的真理,能隨時對另一半投出一枚震撼彈,每人都可以像瑪麗華生及 Joe 一樣,表內不一。融貫的愛所要克服的正是這種表內不一。但「克服」是甚麼意思?這樣說的話,追求真理豈不就是鼓勵消除隱蔽嗎?

無可否認,追求真理某程度上就是克服新命題的阻力,沒有對真理解碼,就不會有往後延伸出來的知識、新現實。但追求真理的先決條件,得建立在阻力出現,令舊現實運行中斷,轉變方能開始。箇中當然伴隨風險,從風險中做選擇來體驗個人轉變,克服阻力的同時,也是對其肯定。融貫的愛旨在追求兩人的調和,互相為對方調節自己的慾望,達至和諧狀態。調和亦是控制,但管理的是自己的慾望,而非風險:我有(讓你)知道與不(讓你)知道真相的權利。因為雙方自我約束的緣故,雙方的改變才被視為愛的表現。
消除隱蔽不志在從阻力中尋求轉變,恰好與追求真理相反,後者追求絕對確定性,忍受不了轉變、風險存在。Joe 從一開始便不打算與情人原本的心理界線妥協,才會裝作自我約束,以便對情人絕對掌控。消除隱蔽就是消除他者的界線 (人與人之間的界線、可知與不可知的界線),不斷將他者解碼,直至所有事情一目了然為止。
另一方面,追求真理本有時間的因素在內。真理永遠比理性走得前。面對真理的衝擊,人需要一段緩衝期,將箇中的意涵消化、內化。理性本身亦需要時間建立理論框架,從紛陳的現象中,梳理世界,好讓理性掌握。譬如說,基因改造的問題之所以引發道德爭議,因為這項技術雖能夠造福人群,但同時也開啟了打造優越種族的可能。討論這話題,就是從對話中找緩衝。瑪麗與華生之間的對話亦是在找緩衝的空間。尋找緩衝空間就是停下來,讓時間發揮作用,令前者得以與真理保持距離。
肯定時間的作用就是阻止理性在最初接受真理便對後者一目了然,免去真理在理性面前過份暴露,亦免去真實界過分入侵,令理性癱瘓。懂得停下腳步就是肯定時間的否定作用,拒絕一目了然、透明的表現。反之亦然,若把時間壓縮,就如拆除了車上的煞車,允許理性不加節制地發問,失去了與真理的應有距離,打開一個又一個的命題,把理性壓垮。對真理不假思索,照單全收,甚至進一步挖掘,就如讓基因改造這項技術在理性尚未準備的情況下普及一樣,失去了消化的機會。逼理性追上真理的步伐,後果不堪想像。
邪惡就是讓真理把認知框架拆走,不給予理性時間重新建立框架的機會,剝奪理性消化的時間。過渡開拓真理的完整性,猶如強逼烏龜追趕白兔,甚至要求比兔子跑得更前更快,務求令理性主導真理。Joe 就是透過監控,壓縮了時間的蘊釀,一邊剷除女主角身邊的人,一邊製造一場又一場的邂逅,操控著融貫之愛的過程,確保對方愛上自己的目標達成。這個理解下,過份的好奇、迫不及待發掘真理,就是否定時間的作用;壓縮了時間就是透明的表現。
哲學的作用
邪惡就是展現過份好奇,追求完全透明。若不理時機是否適當也要對他者解碼至一目了然為止,箇中需犧牲他者的他性達成。他者的他性就如道阻力,抗拒被直接把握,等同情侶間也有條心理界線,只有在感到安全的情況下才會讓對方跨越,不會輕易自我暴露,讓對方直視自己最隱私的一面。情人的意願就是阻力的表現,亦即他性的體現。只有在其首肯下才獲知有關對方的隱私,如同在適當時機下才接受真理的彰顯一樣,是急不來的。因此,致力追求肯定、無阻力的過程中,就要藉著消弭他性的阻力來直接將他者把握,猶如將崎嶇不平的道路磨平一樣。消弭他性亦即消弭個體性,在這節骨眼上,恐怖情人及獨裁者可謂一體兩面。
反烏托邦故事如《一九八四》、《美麗新世界》,看似處理體制與自由的問題,其實在點明追求透明的問題。建制獲得自我肯定(排除管治上的阻力)的途徑就是將個體性抹去馴化,然後將一切的隱私牢牢掌握。說服民眾本是費時的事,只有將民眾的個體性消除,當權者才有介入的機會,要求眾人尾隨當權者的管治意志。當我們以為自己有權知悉對方一切時,即是跳過與人的心理界線周旋的步驟,否定了時間的作用,遂步邁向獨裁之路,成為一名恐怖情人。透明的關係就是一種死掉的關係4。
華生的自我約束說明了一件事:若要知道對方的秘密也要看自己能承受的程度。巴迪歐認為,這種克制便是哲學的用處:區分哪些是可知哪些不可知,在不斷發問的高速中,慢慢煞停。哲學就是學會適時停止發問,不要過度開拓真理的完整性,判斷在何時停下腳步的思考,認清有些真理非我們這時代所具備的知識能應付,這份自覺正是對透明的否定5。

中庸之道方為面對真理的上策:沒有任何好奇就沒有行動,真理無法引發轉變;然而過分好奇,否定了時間在追求真理的作用,將真理過分暴露,引致不堪想像的後果。
結語
開創與行動,成為了愛與真理的交匯。兩者剛發生時,為現實打開了缺口,能否成為現實則依靠行動將事件轉化。兩者均毫不妥協地存在、非完整的、有待建構。要使其完整,就要預設真理的潛在影響,甚至把它逼出來。問題是,開拓真理的完整性,若少了點克制,就會變成追求完全透明,亦即是巴迪歐所謂的邪惡。這點正好在揭露秘密上體現。它的危險在於,它既可是增進親密感的催化劑,同時少了點分寸便將一段關係摧毀。
如何拿捏開拓真理的力度,決定了你是個模範情人,抑或恐怖情人。究竟是見好就收,還是挖個沒有?假如 Joe 能從哲學角度思考,認清情人就像真理,亦有其界限,也許他能夠像華生一樣約束著自己的好奇。他表現出的善解人意,不會只是一副流於表面的面具,而是一種自我克制、尊重無法完全消除的他性的內涵6。
對一個人好奇,也許是愛的徵兆,若不加節制, 便能殺死一段關係。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