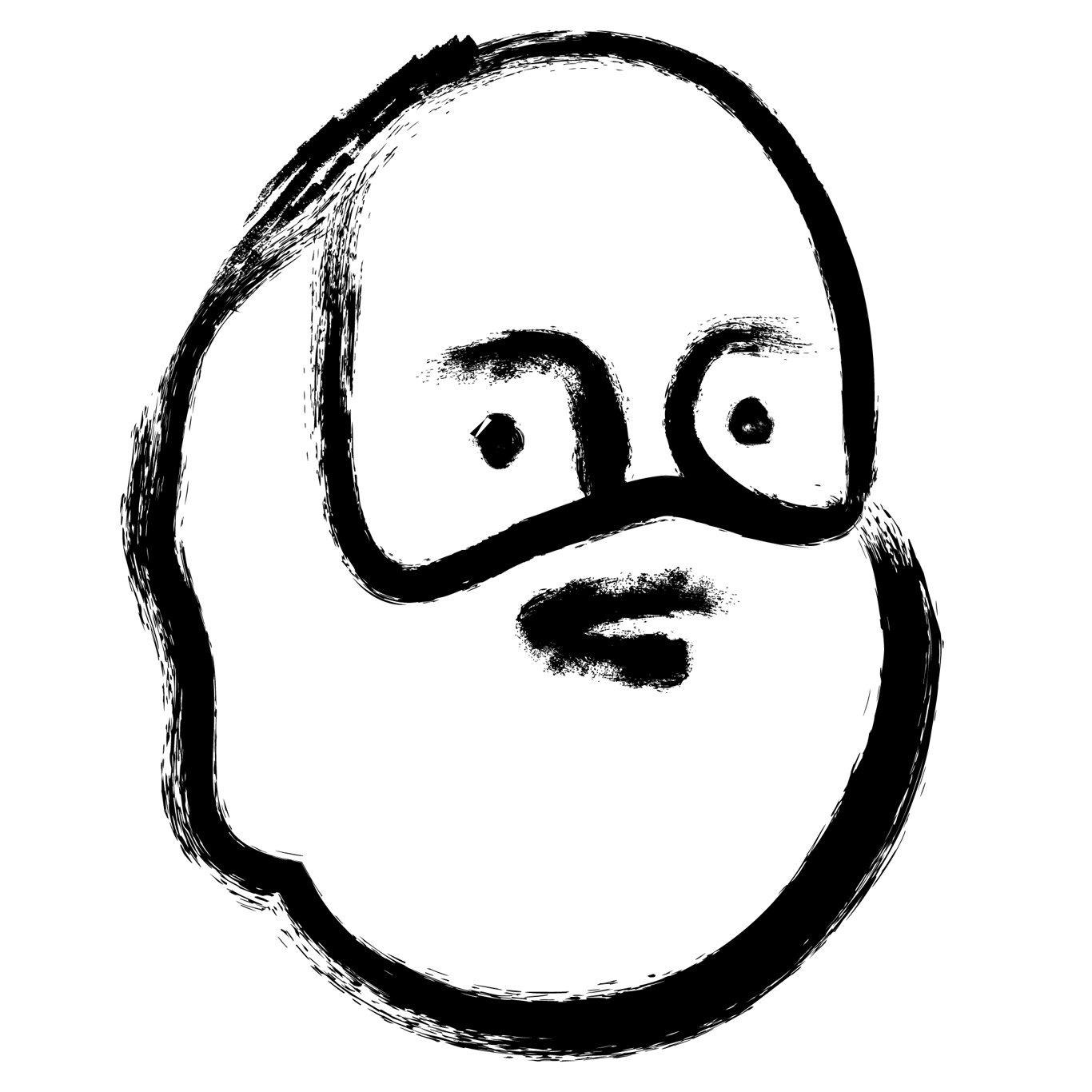不如承諾來得艱難

作者:Yu Hui 難度:★★★☆☆
I.
我們動輒就可以許下數十個諾言——承諾母親會早點回家、承諾伴侶會愛對方一生一世、承諾朋友會應邀赴約。我們的生命中、生活中,都離不開承諾。我們都承諾別人甚麼,又要求別人承諾自己甚麼。承諾很多,多到我們平常都不覺得這是一回事。承諾愈多,就愈顯得它空洞,愈顯得它不過跟聲音一樣輕。
但承諾這行為,表現了人的甚麼特性?承諾,在人與人之間創造了一種怎樣的關係?
承諾,何以來得艱難?
II.
「承諾」這行為得以可能,最起碼需要兩個人或兩個群體。姑且叫他們做「承諾者」及「被承諾者」。在許下承諾的時候,承諾者及被承諾者都超越當下的環境,對未來有所投射。只有因為我們的目光可以離開現在、放到未來,承諾者才能許下諾言,承諾他(們)將來一定會如此這般。另一方面,亦只有當被承諾者對未來有所投射,他(們)才能理解「諾言」所指向的,是未來的事態或行為。承諾這行為,反映了人這種存在者的時間性(temporality),展示了人從來不是只活在當下,而是同時向着未來而活的。
III.
承諾,亦需要語言。沒有語言,我們很難設想任何物種能夠許下諾言。首先,語言當然是一種工具。在我許下諾言的時候,我要能夠言說或者能夠寫字,才能表達自己,才能向他人許下諾言。但另一方面,比較容易被我們忽略的,是語言的公共性。在許下承諾的時候,語言可以說是扮演了公證一般的角色。本來,這個世界沒有我的承諾存在。就算我在心中默默想着要做某件事,甚至立定決心,必定要完成這件事,只要一日我未把它通過語言說出來,未讓它進入公共的領域,這個承諾就不存在。
雖然承諾需要語言,但同時,承諾亦可能是人類對語言濫用的極致。在這裡,我們不妨先區分開「承諾」和「契約」。契約可以有粗疏和嚴格的理解。在粗疏的理解下,契約的制定雙方(或者多方)通過共同承認的契約作條件交換。假如 A 君和 B 君定下契約,而 A 君不能履行契約中訂明的條件,那麼 B 君便有權按契約訂明的內容和方式制裁 A 君。而嚴格理解下的契約,則是具法律約束力,往往會由第三方 —— 執法者 —— 確保契約的執行。
然而,承諾卻和契約不同。承諾並不能作為依據,賦予權力給任何一方制裁或懲罰另一方。當我們說 A 承諾了 B 某件事,那麼就算 A 違背了他的承諾,無論是 B 或是任何人都不能因此懲罰 A。
IV.
由於承諾沒有上述契約的強制權力(coercive power) ,一般人都會覺得契約更可靠。承諾的語言彷彿沒有任何重量,聲音劃過耳邊,甚麼也不會留低。
然而,儘管承諾沒能像契約般予人放心,我們都應該留意一點:從承諾到契約的轉變,不單單是從沒有 coercive power 的話語轉為有 coercive power 的話語;承諾和契約,是兩種截然不同的人際關係。
借用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暴力批判〉(Zur Kritik der Gewalt)中的分析,我們可以說,平等的對話和溝通是一種非暴力地解決人與人之間的衝突的方式。在這狀態下,我們會透過承諾達到共識,化解衝突。然而,由於承諾——以至單純的溝通和對話——本身沒有 coercive power (本雅明甚至指出,在單純的溝通和對話之中,就算是謊言也是不可懲罰的),人們就會希望訂立契約,引入一種「暴力」——一種能確保契約受尊重,仍然行之有效的暴力。
然而,契約成立和暴力介入的一刻,「承諾」就被摧毀。原先由對話建立的人際關係,在引入契約的一刻,就變成了以暴力作為中介的關係。契約之所以能解決紛爭,是因為契約容許被違約的一方行使「暴力」,懲罰違約的一方。因此,維繫眾人的,不是信任和承諾,而是默許的暴力。
V.
本雅明〈暴力批判〉的目的是論證任何(法律)制度和權威都是一種暴力的體現,並非分析承諾和信任,我們對這篇文章的討論可點到即止。
回到承諾的問題。鄂蘭(Hannah Arendt)在《人的條件》(The Human Condition)中就說,承諾是政治行動 [註1] 的其中一個重要條件。鄂蘭哲學的其中一個核心想法,是政治行動注定是「不可預計」(unpredictable)的。她認為,政治行動發生在「眾人」(plurality)之中,人與人的語言和行動互相交錯,編織成一個人際網絡,而在這個網絡中發生的每一個行動,都與其他人和他們的行動互相影響。由於我的行動必然影響到他人的行動,而他們的行動又或許會進而引發其他的行動,我這個原初的行動的影響,根本不可能由我一人預計。當一個行動在人際網絡中出現,它就已經獲得自己的意義和生命,不能被原初的行動者控制。
於是,鄂蘭指出,所有政治行動者都會遇上一個困局:既然每個行動的結果、影響和意義都不能完全由我控制,那麼我們憑甚麼要求他人和我們一起行動?在這個問題上,鄂蘭認為,承諾是政治行動的一個重要條件。要眾人一起行動(act in concert),我們需要行動者的共同承諾,儘管世界不一定像你我預期,儘管行動一旦誕生,它的意義就會脫離你我,我們亦無法預期它會引伸甚麼結果,但我們仍可以共同承諾,會繼續行動,直至我們看到世界變得貼近我們的理想一點點。在這意義下,我們似乎可以說,透過承諾,人才能與他人站在一起,形成一個由平等和獨立的個體構成的群體,進而創造政治的力量。
VI.
承諾本質上就沒有契約的 coercive power,只由語言作媒介,迴盪於人與人之間。只要人能把目光投向未來,能運用語言,他就能許下諾言。所以,承諾看似簡單。
然而,承諾的重量,並不是來自像契約般「被容許的懲罰」或「被承認的暴力」,而是來自它所創造的關係。由於沒有 coercive power,承諾看似十分脆弱,但承諾的這種脆弱,反而是它沉重的來源。換個角度講,承諾之所以是承諾,就是因為我們每時每刻都有摧毀它的可能。沙特(Jean-Paul Sartre)說,人是注定自由的。這句話常常被理解作人永遠有否定某物,作另一個選擇的能力。但,從另一個角度講,倘若縱使我有無限的自由,但我仍然執着選擇某事某物,那麼,這某事某物,就擁有我賦予它的無限價值。若然有那麼一個承諾,是我們沒有自由不遵守的,那麼它亦失卻了作為承諾的價值。正因承諾隨時隨地隨意都可以被我摧毀,保守一個承諾,就變成一個無比高貴的行為。人是絕對自由的,所以我所許下的諾言——不論是愛情、婚姻,以至堅持在頹垣敗瓦中保護住一點殘光——根本沒有任何外在的力量把我和它綑綁。但如果明明人是絕對自由,但我卻仍然無法斬斷某個羈絆,仍然覺得好像有些甚麼,把我和它緊緊地綑綁着,那麼,這羈絆只可能來自我自己的選擇,來自一個由諾言牽引起來的關係,來自我所肯定的價值——儘管堅持這個價值往往伴隨無比的痛苦。
因為承諾,人與人才能產生一種非由暴力、懲罰維繫的關係。因為承諾,眾人才能共同行動。透過審視承諾的脆弱,我們看到我們所珍而重之的價值。
不如承諾來得簡單?不如承諾來得艱難。
[註1]:這裡我選擇用較為冗長的「政治行動」來翻譯 action,原因是我沒有恰當地解釋「行動」在鄂蘭哲學中的意思,為免引起誤解,就加上「政治」來區分一般意義的行動和鄂蘭心目中的行動。但讀者必需注意,在鄂蘭的想法中,行動幾乎必然是政治的,所以「政治行動」一詞或多或少有點類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