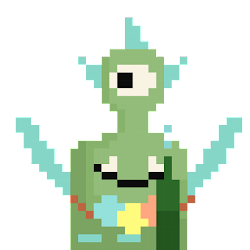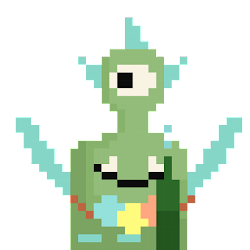意指工具的再創造:我讀《時間也許從不站在我們這邊》
梅洛龐蒂:「所有偉大的散文也是一種對於意指工具的再創造,接著我們便能據此來運用新的句法。平庸的散文,則只是侷限於使用既受文化中的既定符號。偉大的散文是,捕捉到人們至今還未客觀化的意義,因而提供給使用同一種語言的人們來接近的,一種藝術」*[1]

鍾耀華的《時間也許從不站在我們這邊》作為一本近乎時間序的日記感、含有各雜文體、貫穿2016年至2021年的文章選輯,在我看來,即是那種「意指工具的再創造」工作。
他生於1992年,經歷傘運被告,第一口氣嘎然而止於香港命運的轉捩時刻,他的命運也隨之鉅變,如眾多我們所熟知的香港青年。
「五年一瞬,今天講什麼抗命不抗命都已過時了。人人都在抗命了。我也肯定再也寫不出這樣的文章了。…讓我們的生命成為機器運作的阻力。」
這幾句話在書中2019年6月30日〈在香港,雨一直下〉寫下。
我想起在那十五日前,我作為社運份子,急欲「在場」而衝到香港,見到極端的「抗命」。然後我問了每一個受訪者「你覺得抗爭有用嗎?」那聲聲回答,至今擾動了我的感知頻率。事實上,那之後的日子,不知所措。
快要過去兩年了,時間站在你們這邊嗎?時間站在我們這邊嗎?或是書中所說「時間是光的產物,在陷落的世界沒有日照,不存在時間。」
讀這樣一本漫長跨越五年的文章合集,腦補著各種,從此岸同步見證的種種情節,也腦補著貌似的個人化的生命歷程如抗爭、被告、公開發言、找工作、書寫、自我質疑、再書寫、虛構與非虛構、讀書與實踐。
我們能做什麼?
此書,從2016年傘運後的筆觸憂愁,時而虛空,彷彿看破;至2017、2018年的寫實日常感嘆,做出篤定控訴之勢;看2019年的抗爭青年繼續碎念,才在夢境中穿透自然與物種的閃影,清醒,面向無光之前途,邁步行進,述及我們讀者最懼痛也最熟悉的反送中抗爭;並最後,煞地收攏在一篇,可以說是風格上急轉直落的,關於「否想國家」的政治理論與民族誌的嚴肅筆記。
作為台灣讀者,觀看「你城」香港,受提醒而意識須活出真誠,已是相較門檻極低的義務之事。我們能夠過分舒適地「否想國家」,更多時候僅僅需要在共創共同體的過程中「反思(我們的)國家」,直視併吞意圖的「另一個國家」,並觸目驚心地意識到,港人如何否想的複數國家。
若如書中引述,球場上在陣勢變動的幾秒鐘做出應變的「感知」能力:有感知,才有預判,才有突破。那麼,感知訓練的道場裡,我作為受惠於其意指工具的同一種語言的人們,或能是書中所指「接應感知的同伴」。
此書,有幾段寫於今年初的作者介,摘錄如下:
「當所有人包括自己都以為我們必定下獄,我卻被判緩刑。又在我審訊剛完一個多月後,經歷反送中運動——痛苦、絕望、希望、力量、人性光芒與邪惡交織糾纏,如果有神聖,為什麼她對暴行默不作聲?如果沒有神聖,又何以人們孜孜不倦堅持負隅頑抗?
文學呈現的是一個世界,但其必須借助於人們對現世的理解、某些人類交往運作的法則,不然我們無法鉅細靡遺地把世界每個錯綜複雜的糾纏寫進文字裡頭,讀者也無法由零理解一個全然虛構的世界。問題是,要借助於現世到哪個程度?…
我想知道文字在殺戮的世界前,是如何的貧乏或者豐富,他的界限在哪裡,寫作在痛苦面前,還可以是什麼。我想知道,如果換各種不同的方法重新觀察、寫作,現世或者是否能變成另一種現世。」
再摘錄此句,脈絡於香港知識份子們的對話:
攬炒?然後呢?「也不就是踏踏實實過日子。」*[2]
上一次想到「攬炒」這個詞,是看完一個與反送中不必然有什麼關係的港片,虛構與非虛構,聯想與腦補詮釋,又接著在讀完一本香港作家於反送中時間段裡寫成的日記之後,見這個詞彙的理解及衍生。因而我也想逼近其意。「攬炒」在抗爭中引爆,其運用總在「生/死」之間,不過,如果詞彙能夠在論述中不斷生成演化,還能從「踏實過日子」這層去推進。
書中最後〈否想國家〉所引用的,是或許所有社會科學的學徒們,多少聽過的《弱者的武器:農民反抗的日常形式》跟《支配與抗衡的藝術:隱藏文本》。我記得初讀這兩本經典文本片段,腦裡想像的畫面,是揣摩著那時候的農民的行為;時隔多年在此書讀到,已自然浮現港人的行動。
因此,那「踏實過日子」的意義,如果帶有「Effort-Luck Distinction」的命運意識感,意識到我們「處於」尚能跟時間接近這邊的片刻切面,在奢侈行使相對安全且公開的政治反抗同時,應是共同「理解生命的幽微複雜及創造多元的土壤社群」。而文學確實地提供了這片土壤。
「文學中的交流,並不只是作者對意義的簡單訴求。…作家的思想無法不受制語言,作家本人就是一種新的習語,建構其身,發明表述,據其身意義來使自己多元化。」*[3]
所謂生命幽微複雜,我又想到在個體經驗上,書中有一段使我莞爾。作者在2017年8月20日寫到,反對新界東北官商鄉黑勾結一案的審判前,他與運動夥伴們於法院外抗議聲援。
他說「只要接近開庭時間,這些舉動就必須要做,不管人到齊了沒有。有些受審者總是遲到,總在這些聲援發言之事剛處理完後就出現。」
受審者的遲到意味什麼呢?其實我腦補了好多可能。我曾是受審者(於苗栗苑裡風機一案)也曾是聲援者,能想像其中意涵或不意涵什麼。又想到傘運後的香港運動青年來台,好幾次對談彼此的社運場域內部關係,或團結與分歧。雖然台港之間或案件之間難以對等比較,人的處境又會奇妙共想。
我對時間的體悟,並不深刻。但經常(或許是過於草率地)帶入「時間點」。同樣生於1992年,參與並書寫過台灣抗爭的我,得運用此書作為句法去接近意義。在「香港228大檢控」時,便寫下這篇讀書筆記。
同一個世界,不同的夢。時間流逝,河水奔流。他問河流失落的愛與奉獻,河流報以沈默的波浪,而風吹不止息。滿天的星屑有如破碎的夢,粉碎的承諾,在流動的淚裡閃閃發光,刺破視野。——《時間也許從來不站在我們這邊》
- [1],[3]:Merleau-Ponty, M. (1973). The prose of the world.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Editor’s Preface xiii.
上開中文引用,是我自行從英譯再翻譯。引用構想來自鄧小樺撰寫的〈眾數的邊緣:《浮雲與剃刀:字花十年選散文卷》序〉,其中頁19有部分句子的翻譯,但我仍選擇重譯。望無誤解原本,若有錯漏誤讀,敬請斧正。 註1,英文如下: All great prose is also a re-creation of the signifying instrument, henceforth manipulated according to a new syntax. Prosaic writing, on the other hand, limits itself to using, through accepted signs, the meanings already accepted in a given culture. Great prose is the art of capturing a meaning which until then had never been objectified and of rendering it accessible to everyone who speaks the same language. 註3,英文如下: Communication in literature is not the simple appeal on the part of the writer to meanings which would be part of an a priori of the mind;The writer’s thought does not control his language from without; the writer is himself a kind of new idiom, constructing itself, inventing ways of expression, and diversifying itself according to its own meaning. Perhaps poetry is only that part of literature where this autonomy is ostentatiously displayed.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