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清醒的厌女者吗?团结、身份与责任(二)
2. 受益者悖论
暂时不管上述两位女性主义者的观点极端与否,背后的论证合理与否,面对清醒的厌女者,她们的观点和策略正好点出一个更深层的悖论式的问题:当社会上出现系统性不正义或者压迫时,不正义或压迫的受益者如何能够加入旨在改变社会中这些问题的运动呢?又或者说,他们应不应该被允许加入?比如男性,普遍作为当下性别不平等状态的受益者,如何加入女性主义者行列,或者能否允许并信任他们加入呢?
在她的《政治团结》(Political Solidarity)一书中,Hypatia前主编Sally Scholz称这个问题为“受益者悖论”(the paradox of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privileged)。一般来说,当一个个体获益于某种社会的不正义或者曾经是某种压迫者,他要加入旨在终结此种不正义或压迫的运动时,他的加入似乎就具有了悖论式的难题。根据Scholz的说法,社会运动旨在终结的压迫和不正义,可能牵涉到整个社会体系非常深入的方方面面,而未曾受过压迫并且从中受益的个体,可能无从知晓这种系统性不正义的种种利害。他们可能会在运动中带入这种获益,通过这些来自压迫的优势或特权(privilege),去反对其他方面的不正义。在受压迫者看来,受益者身上享有的优势和特权正好是受压迫者害怕和反对的,甚至,受益者加入改变社会现状的运动反而会使得他们本身的特权增多。
男性要加入女性主义运动之中,如李麦子所说,他们不会了解性别不正义在整个社会体系中的深远影响。更加有可能的是,男性在女性主义者群体中,会依仗他们在性别不平等体系中获得的优势,比如性别话语力量、性别社会机会等等,去反对其他性别不平等而已,甚至会在运动中引入不平等和更多来自性别的受害者。所以男性女权者不可能形成女性主义团结,不可能真正懂得姐妹情谊(Sisterhood)的意义。既然如此,那么上文提到的两位女性主义者在面对清醒的厌女者时的策略,限制甚至排除受益者加入到运动之中的策略,是有道理的。
3. 悖论的三个问题
不过,受益者悖论虽然看似悖论,实质上并非如此。根据受益者悖论来限制甚至排除受益者或者前受益者加入到运动之中的结论需要面对三个问题。
3.1 立场理论
根据上文的描述,受益者悖论形成的一个前提是,受益者不可能知道系统性压迫和不正义的全部实质,因而结论才是他们不可能真正参与到消除这些压迫和不正义的运动中。正如李麦子文章认为,女性才能真正知道女性主义要终结的性别不平等,因为女性受到的歧视最多。然而,我们可以追问一下,为什么女性受到的歧视最多,蕴含了女性才能真正知道性别不平等,而男性不可能真正知道呢?可能不太恰当的类比,被骗钱最多的人,才能真正懂得骗子的手法?
立场理论(standpoint theory)或许是回答这一追问的答案,并且是受益者悖论背后预设的知识论(认识论)。作为一套知识论理论,立场理论主要关心知识在社会中的状态和地位。(刘满新,《女性主义应当反思》)立场理论的主要观点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马克思提出的认识论观点:
1)不同的社会物质条件(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会带来关于世界的不同经验和理论(知识/认知)。
2)根据社会物质条件的差异,人在社会中被分成不同的群体。
3)所以,不同群体对世界的经验以及形成的信念和理论(知识/认知)也是不同的。换言之,不同的群体具有不同的知识立场。
不少论者认为以上就是立场理论的全部,认为不同的群体具有不同的知识立场。这可能是一个在方法论上十分有效的观点,认为不同的群体具有不同的知识立场。然而,这并不是立场理论的全部。认为不同的群体具有不同的知识论立场,与一般关于知识的相对主义没有区别,知识没有客观上的正确性。女性主义的立场理论关注社会性别关系,如果只是接受不同群体具有不同的知识论立场,那么结论只能是,女性有女性的立场,男性有男性的立场,两者没有对错只有权力的制衡。显然,这不是女性主义的立场。立场理论还有一个关于知识立场地位的判断:
4)被压迫的群体的立场具有知识上的优势。
在立场理论看来,并非所有知识立场都具有同样的知识论地位:受压迫的群体的立场上获得的(关于社会压迫)的知识更具客观上的正确性,所以,用李麦子的话说,“最有发言权”。因此,女性主义的立场理论认为,女性作为被压迫群体,其立场更具知识上的优势,能够更真实地反映社会状况,而男性,自当然不可能完全了解性别不平等的全部实质。
不过,作为一种知识论,女性主义立场理论是有缺陷的。
首先,立场理论无法找到非循环的辩护基础。按照立场理论,因为女性处于社会性别关系上的被压迫位置,所以女性对社会的认识要比作为压迫者的男性的认识要更正确。然而,如何确定女性处于被压迫位置呢?男性至上主义者/直男癌患者也许并不会承认,女性被压迫是事实。这时我们又要确定,直男癌患者的认识是错误的。如何确定?因为他们处于压迫者的位置,对社会的认识没有受压迫者女性的认识准确。这样一来,女性主义立场理论在辩护上就陷入了循环论证,我们无法非循环地确定哪一种立场是更具有知识上优势的立场。
再者,立场理论会出现自我矛盾。立场理论要么承认,所有女性的经验都是铁板一块这个错误前提,要么承认,不同的女性在社会中所承受的压迫各有差异。如果后者,不同的女性群体对应的不同立场,哪一个才正确呢?女工群体除了性别还需承受来自资本的压迫;外来务工者中的女工,还承受者社会上对外来务工者的歧视;外来务工者中的女地盘工人呢?社会上存在着不同身份不同社会位置的女性,根据立场理论,她们各自可能都有不同的知识论立场,哪一个立场才是关于性别不平等的社会状态最有权威的立场。立场理论无法回答这一问题,反过来只能认定,没有知识立场。这是一种自我矛盾:谁才是真正的女性主义者?(刘满新,《女性主义应当反思》)
如果受益者悖论成立的前提是预设里知识论上的立场理论,那么,既然立场理论有问题,自然受益者悖论未必成立。
3.2 经验与行动
如果承认受益者悖论的结论是,受益者因为没有经验过压迫,他们也无法真正投身运动去终结这种压迫和不正义,这似乎预设了经验压迫和实际行动的紧密相关。不过,经验过压迫与行动本身的关系,既不充分也不必要。
首先,或许对压迫和不正义的亲身经历对于理解压迫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经验过压迫本身并不能够必然意味着被压迫者会真正参与到行动中去改变此种压迫,甚至,并不必然意味着被压迫者承认这是一种不正义压迫。参与到运动与经验压迫尽管关系密切,但是它们是不同的两种社会关系。我们日常处处是这样的例子,很多女性尽管经历着性别不平等带来的压迫,但是这并不能够驱使她们去行动起来反对这种压迫,甚至,不少认为这并非不平等,而是女性必须经过的人生历练。
相反,尽管本身未必经验过压迫,但目睹并认识到他人所承受的不正义,许多人会因此站起来反抗。Frederick Douglass或许没有经历过女性所受的压迫,但不妨碍他同时为妇女运动提供支持。我们常常误解,只有通过亲身经历或者亲近的人受到伤害,个人才会真正投身于(commit to)行动或者运动之中。只有个人受过来自性别体系带来的不平等才会真正关注女性主义和投身妇女运动,或者仅当亲近的人受到枪支伤害,个人才会积极参与控枪运动。这种预设在我们的流行影视作品比比皆是,也是我们阅读到的许多好文章的常用方法。这种预设忽略了个人理性和意志的力量。正如电影“斯隆女士”(Miss Sloane)中Miss Sloane斯隆女士所说,这个预设认定,好像仅当她有亲身经历或她的某位谁谁死伤于枪下她方能认识到论证的力量(the merits of an argument)而投身到控枪法案的游说。(“As if I can only see the merits of an argument when I feel the effects personally.”)这个预设并不恰当。甚至,这种仅仅因为亲身经历而马上改变立场或者采取行动的做法,才是值得怀疑的,因为这未必是谨慎思考得出深思熟虑的意见和决定的理想例子。
所以,受益者悖论中预设经验过压迫和行动本身的密切关系,实际上未必如想象中那样紧密。
3.3 女性的受害者化
如果受益者悖论成立,因而结论是运动需要限制甚至排除受益者的参与,那么这可能导致第三个问题,即著名女性主义者bell hooks所说的“女性的受害者化”(victimization of women),尤其当排除受益者参与行动的基础是参与者的共同压迫(common oppression)。(bell hooks, “Sisterhood: Political Solidarity between Women” in Feminist Theory: from Margin to Center)
的确,在长久的性别不平等和男性中心之下,女性受到各方各面的不正义与压迫。性别主义和男性至上主义为了继续剥削和统治女性,会通过制度的每个面向阻碍女性,而其中一个有效的方法是分散女性,让每个女性相信,女人之间互相都是潜在的敌人,女人之间没有真正的友谊。女人怎么可以团结呢,如果除了找到男人,依靠男人之外,女人没有价值的话?女人和女人就是争夺男人的潜在对手。所以,要终结性别不平等,女性需要团结,形成姐妹情谊(Sisterhood)。
可是,hooks质疑,如果姐妹情谊的基础是女性的共同受难经历,这种姐妹情谊是不可靠和不恰当的。首先,如果女性以共同受难经历为基础而联合,这很可能不过是继续顺从于男性至上主义对女性的想象和塑造:真正的女性就是柔弱的受害者。如果女性主义运动只能容纳自我认定为受害者的女性,如果女性只有通过设想自己为受害者才能代入女性主义运动,运动很可能不过是不断重复性别主义对性别的建构。在哪里,到什么时候,女性才可以不是受害者?这才应该是姐妹情谊需要让女性看到的关键。
另外,如果姐妹情谊的基础是女性的受害者化,这会导致在女性主义运动中排除某些女性,特别是那些自我肯定的、强势的女性,她们将无法加入和认可女性主义运动。bell hooks认为,每天饱受压迫的女性,有时极需要的一个顽强的信念,相信自己对生活保持控制,才能继续生活下去。她们不可能放弃这种信念而只设想自己是受害者。
最后,如果姐妹情谊的基础只是共同受难经历,这会导致女性主义运动不断地推卸责任。bell hooks认为,如果女性主义者们只设想自己是受害者,这等同于漠视女性也可能参与构建和维持性别主义、种族主义和阶级主义等等的压迫的事实。男人才是唯一的敌人。(通过共同敌人而联合的运动,很可能只是一个报复行动。)除了推卸责任,这种做法还将遮盖女性之间,女性主义者之间的差异与分歧:只要我们有共同受难经历,我们就是一致。
既然受益者悖论蕴含这么多问题和困难,那么我们就大可不必接受受益者悖论。既然不必接受受益者悖论,我们似乎也没有必要相信,在运动之中,我们必须限定甚至排除受益者的参与,就算我们有可能在女性主义者中遇到清醒的厌女者。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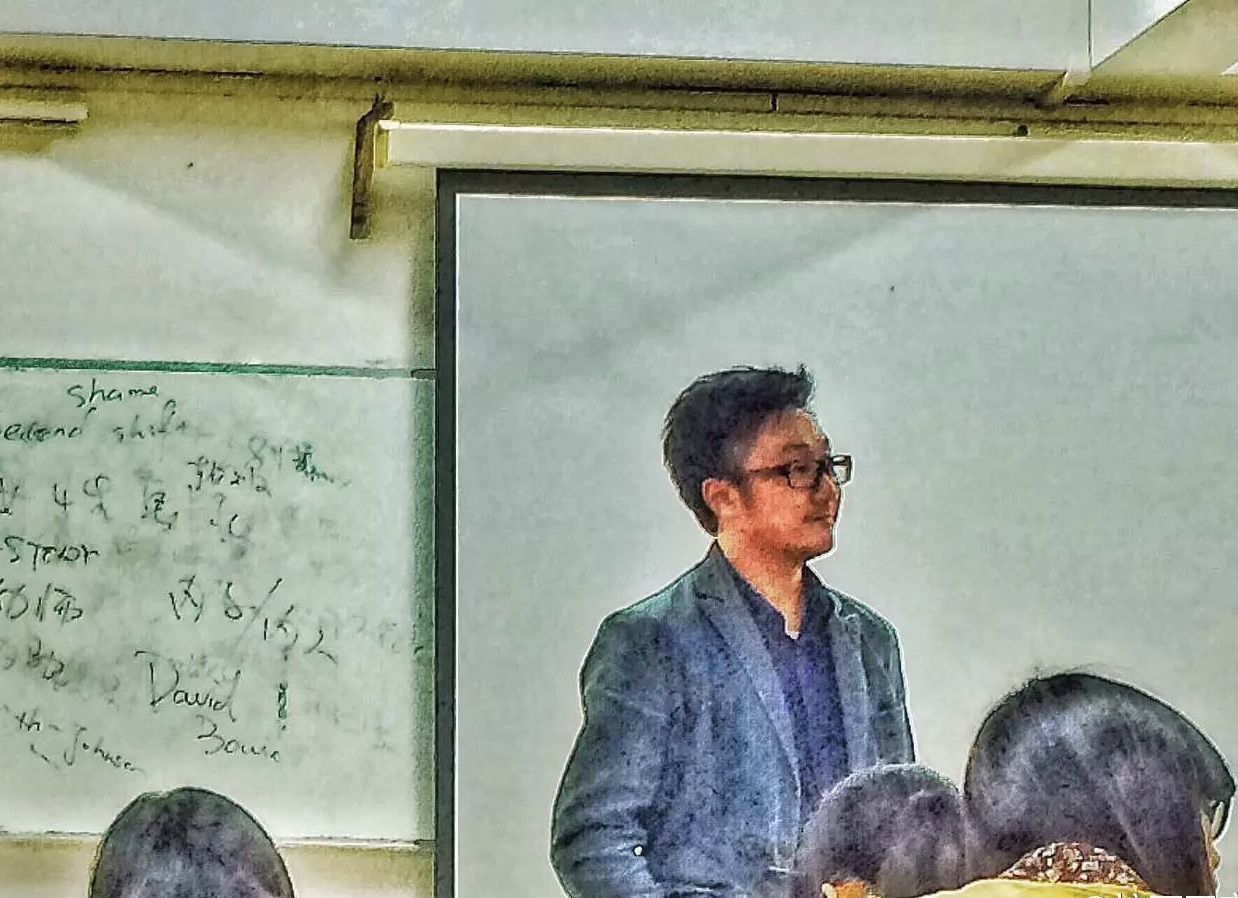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