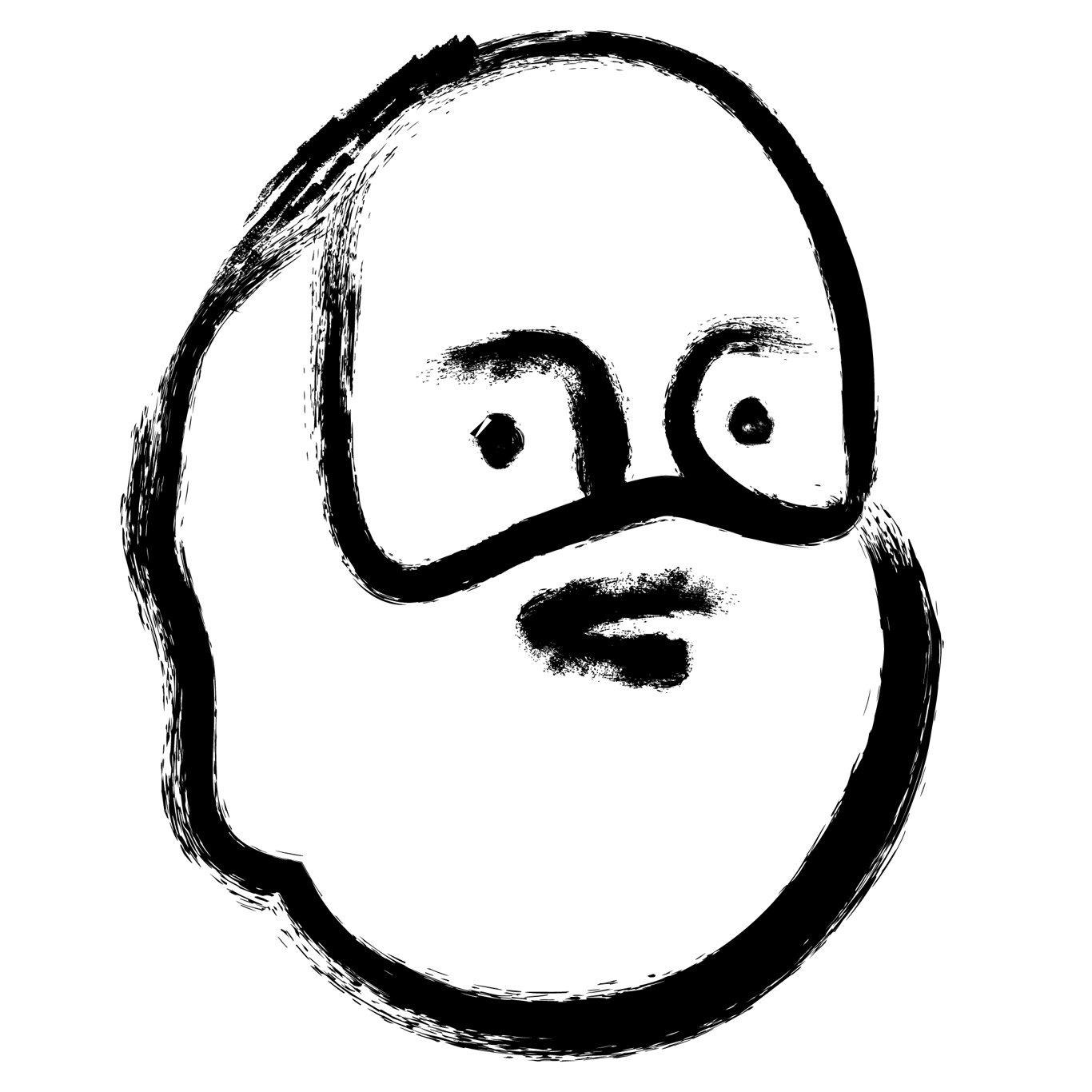《格雷的五十道陰影》── 必然崩潰的性虐待

作者:Kum Long Yin 難度:★★★★☆
《格雷》當然不是一部新戲,而劇情其實並不複雜,這部戲是講述男主角格雷是一位年輕有為的企業家,亦愛玩性虐待遊戲,因為接受訪問的,巧合地遇上一位唸英國文學的女大學生。這位名叫安娜的女大學生清澀且帶點天然呆的性格,讓格雷對她感到興趣,她不經意的咬唇咬筆的舉動,更撩起了年輕總裁的收服她衝動。
安娜亦被總裁霸氣與才氣所迷倒,經過男主角的幾輪攻勢,他們開始以合約的方式,建立一段虐戀關係。可能是男主角兒時的經歷,令成長後的他一直想成為主導者,所以需要一位異性對他服從。傻呼呼的女主角恰好出現時,便挑起了他透過性虐的方式來「調教」異性的渴望。

劇中有幾句對白令我感覺十分深刻,如安娜曾訪問格雷,他的商業成功之道是什麼,他回答他的長處就是使別人發揮其長處,並且駕馭別人。從直覺看來,這句話已經夠「虐待」味了,但為什麼這是施行性虐一方的性格特質?換句話講,究竟什麼是性虐待?
性虐待語源
性虐待的外文為「Sadism」,這字其實源於法國大革命前後的一位名為薩德侯爵(Marquis de Sade)的貴族。若果我們直譯Sadism的話,便是「薩德主義」。
薩德侯爵究竟有什麼特別,讓後世的人把性虐待與他的名字連上關係呢?他本來是波旁王室的遠親,而薩德侯爵所做所為的荒唐遠遠超過當時法國放盪貴族所能容忍。據聞他喜歡虐待雛妓與家中的男女傭人,後來他的妻子更加入,與他一起虐待下人。他曾迷姦妓女,並強迫她們肛交與群交,其後東窗事發,被判死刑,所以他便出逃。往後經過一大輪轉折,回到巴黎,又被人監禁到巴士底監獄。薩德侯爵寫了不少著作,最著名的是《索多瑪一百二十天或放縱學校(Les 120 Journées de Sodome ou l’Ecole du Libertinage)》這本書,描寫了一些年輕男女的性虐待與綁架之類故事。
這些性虐待的情節,其實看來已經遠遠與純粹生理上的性高潮無關,例如強逼一些男女群交,且自身沒有參與其中已經是個簡單的例子。我們可再問深入一點思考:性慾是否等同於追求性高潮?要回答何謂性虐待,這答案可是關鍵要點。
性慾與精神面貌
性慾其實不完全等同於追求某些生理反應,至少沙特(Jean-Paul Sartre)亦會這樣看。他在《存在與虛無》這本書中,曾對愛情、被虐與虐待等以現象學描述分析。他認為,性慾並不單純為了性高潮等生理反應。當然,性高潮可以包含在性慾當中,但絕對不代表性慾僅僅是為了性高潮。要不然有慾望的時候,自慰就能滿足性慾,再有的話則來多幾次,以增加數量的方式去解決。可是情況並非如此,自慰不能滿足人的需要,否則人便不會找性伴侶來解決問題。
另外,對於沙特來說,一般人對他人身體的慾求是「整體性」的,人根本不可能僅僅對他人身體的某一個部分產生慾望。例如,某些人認為胸或腿十分性感,這是因為這些身體部分,落在這個人的身體整體之上,能夠表現出性感的特質,而不是我們僅僅對某個部位有性慾。若非如此,一般人便會對人體殘肢產生性慾了。
在日常經驗當中,他人身體呈現於我,乃介乎一顯一隱之間,從而構成整體。衣服正正能夠能夠扮演了決定身體顯隱的功能,它不可能把全身都覆蓋的,只能把身體的某部分遮蔽起來,而同時把身體的某部分顯露出來,就如某些回教國家的女性把「全身」都遮蔽起來,亦不能把眼睛藏着。這使得衣服決定了身體哪部分顯,哪部分隱的佈局。
感覺某個人很性感,是因為我們對這個人有顯有隱的整體產生慾望。我們的欲望對象不是任何個別顯或隱的部分,而是整個身體。就算我們覺得身體某一部分特別性感,也在於這一部分坐落於整個有顯有隱的身體整體之中。
我們之所以會為欲望對象產生欲望,正因為這對象本身存在於一個更大的意義網絡之中。這個意義網絡的整體,賦予了某一部分特殊意義。例如整個有顯有隱身體作為意義網絡,使身體的其中一部分特別性感。按此說法,我們甚至可以追問,身體作為我們的欲望對象,究竟是以座落於世界,如何在一個更大的意義網絡的環境下使我們產生慾望。為何格雷要把安娜帶到遊戲室,並把她吊起來?就是這個原因。
愛撫和塑造
性慾亦不等於性愛過程的追求,因為風土人情與個人喜好各有差異,難以普遍地一概而論。唯一普遍的,是性慾必然與他者產生關係。對待他者的態度,也是一種精神面向。故此,對他者或自身整體意義的關係,關連到人的精神面貌層面,甚至是與他者之間的意義交流的問題。
愛撫他人,已經是人我關係的具體表現方式,按照沙特的講法,我與他者永遠都在主體與客體的對立關係之中。
當我作為主體的時候,他人便以客體而存在。他人的存在性質,透過我對他的理解,任由我自由地定義;反之,我在他人的的眼中便是一個客體,一旦進入他人的世界,我便儼如他人世界的物件般,任由他者自由地定義。理解自我,必然與其他人對我的理解有落差,故此關於自己是誰的問題,便分成了兩個不同的部分:作為第一身的自己,與第三身的自己,用他的話來說,就是為己存有(Being-for-itself)與為他存有(Being-for-others)的分別。
可能一般人會認為愛撫流於純粹觸覺感官層面,兩者純粹透過雙方互動,加上觸覺的刺激而性滿足。但其實愛撫這種活動不此如此,這是關於意義層面的東西,透過愛撫他者來定義他者的一種活動。愛撫對方,就如同跟對方細說:「我要依據我的想法來塑造你。」我把他者拉入自己的意義網絡,同時他的身體不僅僅是生理軀殼,他的身體因愛撫的過程,成為性慾意義的肉身。要注意的是,愛撫並不一定限於觸覺層面,人亦可以透過視覺塑造他人的身體,使其作為我的性慾對像。或者,有一個更加貼切的講法:愛撫其實有「調教」的功能。
一般而言,愛撫是雙方平等的攻守互動,並不指一個是攻而另一個是守。雙方透過愛撫把對方納入自身的主體所建立的世界,同時自己亦作為他者的客體。那麼,二人便從這個有機的活動,使自己的身體與他人的身體成為性慾意義下的肉身,沙特稱之為交互肉身化(double reciprocal incarnation)。
性虐待的單向特質
講了那麼多,究竟什麼是性虐待?性虐待的一方,往往只希望自己是主體,不想成為他人世界裡的客體,僅想運用自己的自由來定義他者的身體怎樣出現在他的世界裡,絕不希望自身的主體絕對自由,因他人愛撫自己,而被塑造成客體的存在。按沙特的講法,這是不交互(non-reciprocal)的關係,他可以隨便透過他人的身體為工具,來定義他人為何物。或者這樣說,虐待別人的一方,就是幻想自己的身體不會成為對方的慾望對像,從而產生快感。真正的性虐待,要控制的不僅僅是對方的身體,而是在自己能自由定義對方的同時,操制對方如何定義自己﹙或不容許對方定義自己﹚,讓自己只做主體,卻不會淪落為客體。
所以,格雷要把安娜綁起來,就是讓安娜不能愛撫自己,只能任人魚肉;安娜對格雷的目光,能反過來塑造格雷,所以格雷也為她戴上了眼罩。當安娜成為了純粹的物件,她就不能定義格雷是什麼。在遊戲室裡面,格雷控制了安娜如何理解自己,也就是說:格雷控制了安娜該怎樣看自己,所以他才一直不肯講自己兒時經歷過什麼。格雷要求安娜絕對服從,他要成為主人,而對方則是服從者,把安娜變成了自身世界裡的「物」,變成被他隨意任用的客體,以解除對方本身既有的自主性。
故此,他想自己如何看待自己等同於安娜如何看自己,第一身的自己就如同第三身自己,也就是為己存有等同於為他存有,以達致自身在前反思活動狀態下的統一的假像。
透過這種方式來達致自身統一,必然是一個假像。安娜是一個正常人,她不可能完全放失自身的自由,亦不能長期如此。她需要互動,也需要格雷來滿足她世界裡的幻想。她是一個人,並不是物件。故此,安娜渴望撫摸格雷,並反覆質問格雷為什麼不能被她觸摸。兩個世界觀彼此相違,這時他倆便互相指責對方改變自己。

最終,還是離不開衝突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