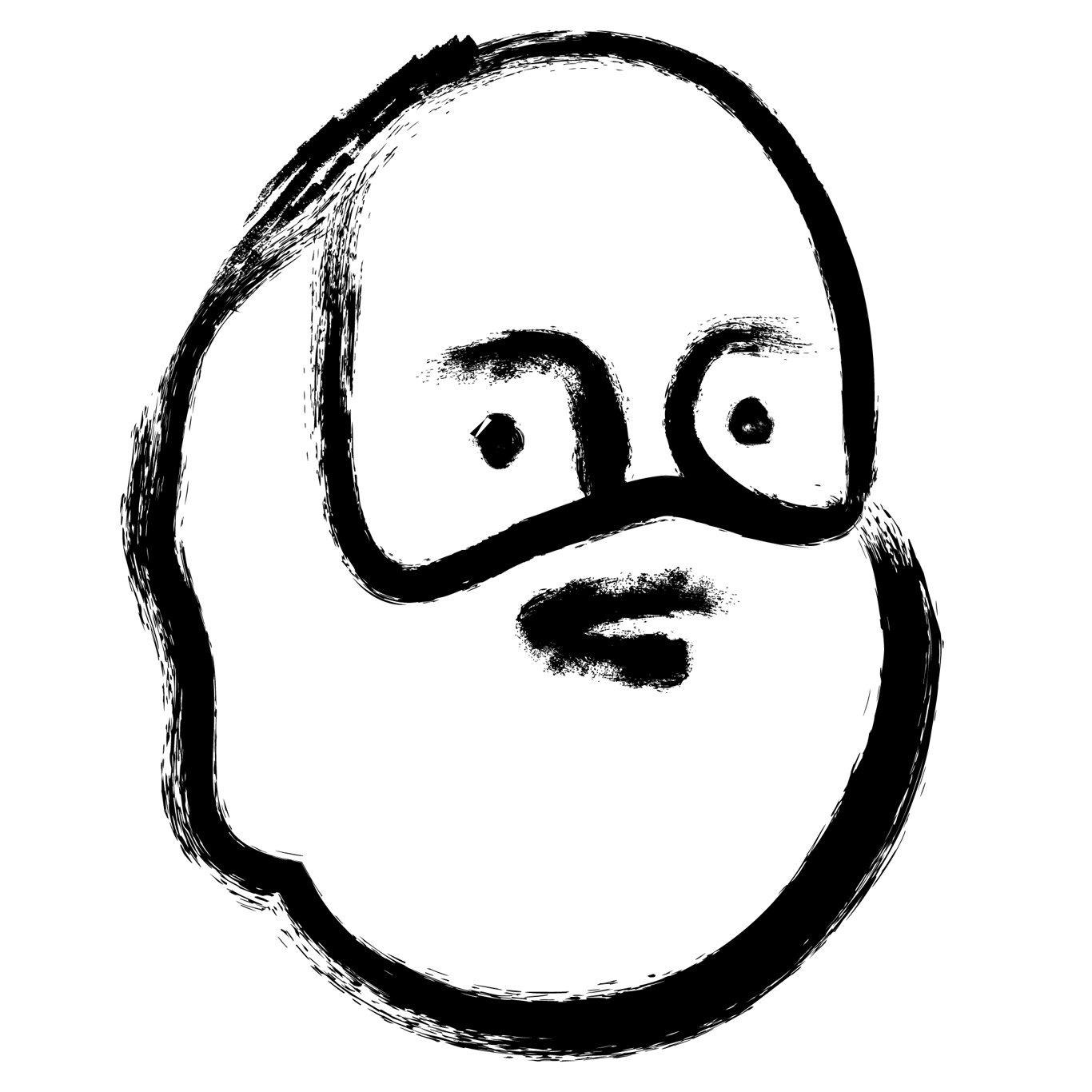後結構主義的無政府主義(二):權力無處不在,所以革命也無處不在

文|豬文
難度:★★★★★
「我的想法不是一切都是壞的,而是一切都是危險的。壞與危險不完全是同一回事。如果一切都是危險的,那麼我們便總有事情要做。所以,我的立場並不導向政治冷感,而是一種悲觀的行動主義。」── 傅柯
上回解釋了後結構主義對社會、權力、人的理解如何與傳統無政府主義有所分別,今回希望說明後結構主義按照這種社會圖像,如何看政治介入與社會變革。
微觀政治(Micropolitics)與宏觀政治(Macropolitics)
搞清楚後結構主義的理解之前,必須說明它如何解釋所謂微觀政治與宏觀政治。
後結構主義其一中心思想,是對各種殊別的行為、關係、現象作系譜學式歷史研究。順之,後結構主義對政治的分析也是一種「微觀政治」 ── 它關心的是各種殊別的政治行為、關係、事件,例如監獄的設計、教會的告解文化 ── 而不只是這些比較能夠安頓在大故事(grand narrative)之中的「宏觀政治」,即那些所謂根本、決定性的政治結構,如經濟生產模式(對馬克思主義而言)或者國家體制(對傳統無政府主義而言)。
換句話說,後結構主義除了關心經濟、國家之外,也關心語言、文化、性、宗教、醫學、心理等各種領域。這些領域互相交疊,亦有其不能還原的內在特性與歷史。因此,它們不會再只是一些被經濟或者國家決定的「上層建築」,反而與經濟和國家一樣,是構成整個社會的部分。
雖然後結構主義特別關心微觀政治,但後結構主義也不可能否定那些所謂宏觀政治的存在。例如,沒有人能夠否定資本主義、主權國家這些「大結構」在當前社會扮演的重要角色。可是,若果資本主義、主權國家這些宏觀政治確實存在的話,後結構主義的政治哲學中,會如何理解微觀政治與宏觀政治之間的關係呢?
一方面,一如後結構主義的理路,後結構主義會強調這些宏觀政治雖然在社會有很重要的角色,但不是一些超然的存在。相反,這些宏觀政治源自於個別的行為、關係、事件。例如資本主義這個宏觀結構,也是從個別、具體的行為而來,像我們稱呼手裡的一張紙作「錢」,拿着它去買東西等。所以,傳柯認為這些看似決定性的宏觀政治都可以追溯至殊別的行為。甚至,我們一定要以那些殊別的行為為基礎,來理解宏觀結構。
然而,另一方面,後結構主義也反對我們將宏觀政治還原成微觀政治,因宏觀政治乃各式各樣的殊別行為所交織而成的結果。例如剛剛提到的資本主義,它當然不只是因為你一個人稱呼手裡的一張紙作「錢」拿去買東西便出現。要研究資本主義,不可能只研究你這個殊別行為。資本主義的出現,還需要千千萬萬個你,以及千千萬萬各種不同領域的不同行為才得以可能。當中或者牽涉到我們逛藝術館的方式,對待父母的態度等等。
經過如此眾多的殊別行為交織之後,那些宏觀政治已是獨特不能還原,甚至有能力創造出新的行為(例如資本主義之後創造出的「陪老闆吃飯」等各種新行為與新關係)。簡言之,雖然宏觀政治因微觀政治而起,但宏觀政治並非只是微觀政治疊加出來的總和(sum),卻是各種微觀政治互動交織之後的整體(whole)。各部分的微觀政治當然有自己的運作方式,但當它們之間又會互動,才再構成更大的宏觀政治。各種微觀政治的研究,並不包括它們之間的互動,所以對整體宏觀政治的研究,並不等同於各種微觀政治研究的總和。關於宏觀政治的研究,微觀政治的研究不能取而代之。
總的來說,後結構主義認為:宏觀政治(大結構)與微觀政治(殊別行為)不能互相化約。殊別行為生出大結構,微觀政治不能還原為宏觀政治;大結構由殊別行為層層交遞而成,宏觀政治也不能還原為微觀政治。德勒茲甚至曾說:「一切都是政治。但一切政治同時都是宏觀政治與微觀政治。」
沒有烏托邦
按這種對社會的理解,後結構主義所談及的政治介入,便與傳統無政府主義的圖像很不一樣。後結構主義基於上述宏觀政治與微觀政治之間關係的理解,認為傳統無政府主義,以至馬克思主義的政治計劃註定失敗。亦即是說,後結構主義認為一勞永逸式的烏托邦實現計劃並不可能。
一來無論巴枯寧主張的人民由下而上的革命,抑或列寧主張的由工人組織帶領的革命,他們都預設了我們眼有一個「大佬」(「老大」)要解決。革命的一切和唯一目標都是要打倒這個「大佬」。巴枯寧眼中的是「國家」與「權力代表」,列寧眼中的是「資本主義」。可是,就後結構主義者而言,他們都漠視了十分重要的一點 :這些「大佬」其實都是微觀政治的產物。單單盯着這些「大佬」,而看不見生成這些「大佬」的殊別行為、關係,顯示了他們以為微觀政治能夠還原成宏觀政治 ── 只要解決了宏觀政治問題,一切微觀政治問題都不復存在。這種認知錯誤下,政治改革計劃註定不能成功。
二來後結構主義並不相信權力與壓迫會有完全消失的一天。正如上回所講,權力與壓迫並不是獨立的關係,無所謂「壓迫 ── 被壓迫」的關係本身,更不可能把這種關係等同於「統治者 ── 被統者」或者「資產階級 ── 無產階級」。權力與壓迫就在我們生活裡的各種關係裡。如是,無論在無政府的世界也好,抑或是社會主義世界也好,都總可能出現壓迫。因為在這些所謂烏托邦世界裡,雖然我們消除了「統治者 ── 被統者」或者「資產階級 ── 無產階級」這些關係,但依然會有「同事 ── 同事」、「父母 ── 子女」、「老公 ── 老婆」這些能夠衍生壓迫的關係。
更何況,在那些「美麗新世界」裡,我們又會有一種新的生活、新的行為、新的文化以至新的關係。這也意味着新的權力與新的壓迫也會隨之而出現。因此,即使我們能夠打倒那些「大佬」,建立起一個全新的世界也好,那個新的世界也不可能是烏托邦:只要有生活,就會有權力與壓迫的可能。
無處不在的抗爭
那麼,真正的改革是怎樣的一回事呢?後結構主義認為,這裡沒有「大佬」,政治改革也不可能有「綱領」。我們就只能從各種殊別行為、關係裡的權力與壓迫中開始解放。
如果社會就如上圖的樣子而不是一棵大樹的話,我們要做的就不是「連根拔起」,來一場「翻天覆地」的革命,而只能夠「逐點擊破」 ── 在生活的每一個層面都抗爭。不只是經濟和國家層面的改變,語言、文化、性、宗教、醫學、心理等各種層面的抗爭,都屬社會變革。後結構主義強調在生活的每一個角落都要抗爭,並不是因為這樣做可以驅趕把手伸進我們生活每一個角落的「大佬」,而是因為各種壓迫本來就具體地出現在這些殊別的行為與關係之中。
既然社會是駁雜而多元的,那麼政治介入與改革也自然是駁雜而多元的。這是後結構主義對政治變革最核心的想法。
故此,後結構主義便不再認為有所謂「質變」/根本改變與「量變」/小修小補的區分。因為一切量變都是質變,一切質變都是量變。以往之所以會出現這個區分,是因為以往的人認為社會是棵有本有末的大樹,所以也以為變革有所謂「根本」的改變與「旁枝末節」的改變。比如有些馬克思主義者會說唯有生產模式的改變才是有意義的結構性改變,而爭取最高工時、最低工資則全都是沒有意義的小修小補。但這在後結構主義眼中是錯誤的,因為社會其實如上圖所示,就是由這些殊別的點與線所構成。任何殊別的改變都是結構性改變,任何結構性改變都是殊別的改變。
不過,後結構主義當然也不會認為任何改變都是同等地重要,正如上圖的交匯點也有大有小。明顯地,「你女朋友強迫你陪她吃日本菜」與「高官強迫你交稅給地產商」之中,後者牽涉的權力與壓迫嚴重得多(如果你認為前者較嚴重的話,那就……加油吧)。後結構主義者在著書立說時,也不可能研究全部殊別行為,他們也總得揀選他們覺得特別值得研究的。
所以後結構主義也會承認某些行為、關係特別重要(這個重要差別仍然只是程度之分,而非如其他立場以為的本質之分),他們想做的便是分析那些他們認為在社會裡特別重要的交匯點,例如傅柯針對懲罰制度、德勒茲着墨國家制度、利奧塔關注語言運用,藉以說明說明這些固有做法如何產生大量壓迫,亦揭示了它們不必然如此 ── 它們全都有改變的可能。
往哪個方向走?
說到這裡,我們似乎只解釋了後結構主義對社會改革的理解,有何形式上的特性(「逐點撃破」),至於改革的內容卻未論及。現在的難題是:我們的改變應該往哪個方向走?一如既往,後結構主義不可能給予我們一個「藍圖」或者「綱領」,頂多只能告訴我們一些很粗疏的指引。但這些指引的根據又是甚麼?他們根據甚麼原則建立這些指引,使得我們應該跟隨?甚至,更根本的是,後結構主義容得下這些關乎評價與規範的問題嗎?這又要留待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