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葭:中国人仇日的“程序设置”——略论四十年来的中日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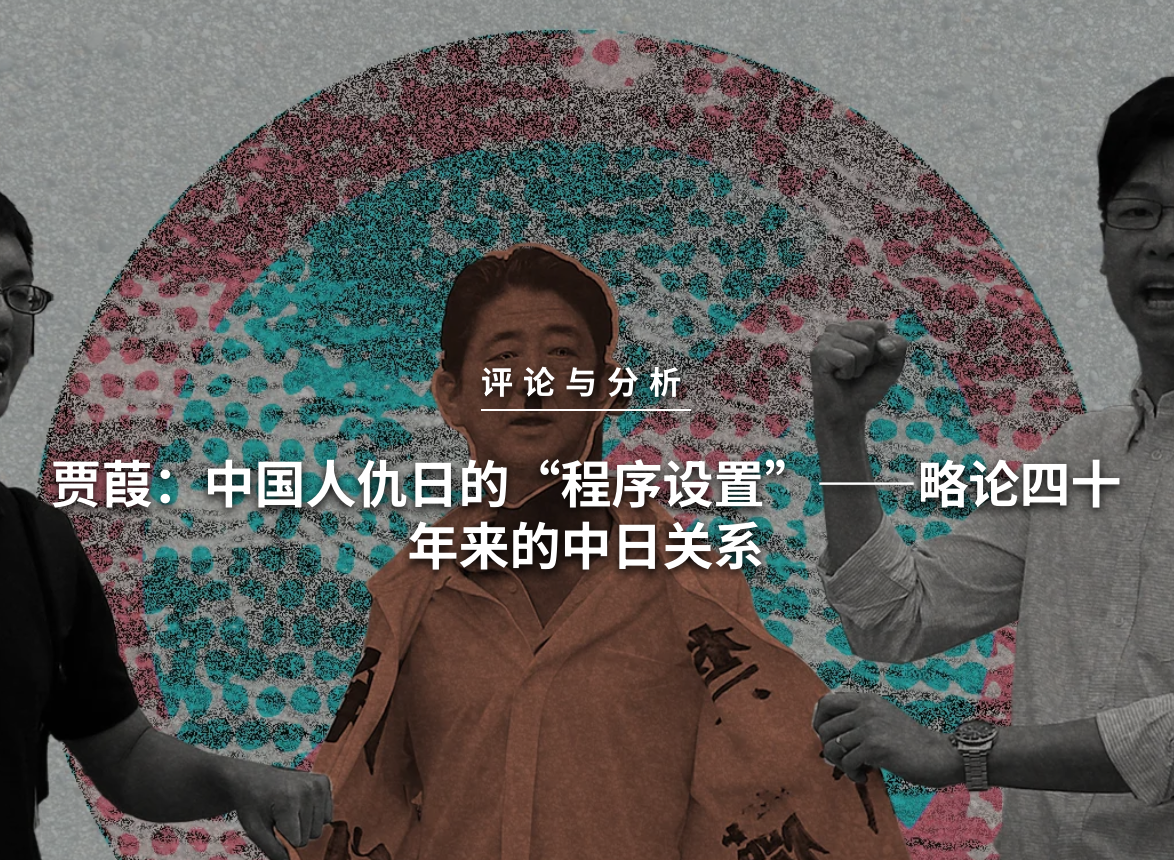
文|贾葭
原文发布时间|07/01/2024
差不多近百年前,《大公报》的张季鸾先生,让编辑王芸生开设了《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的专栏,并在1932年结集成书。该书从1871年《中日修好条约》讲起,直至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直至今天,这套书也是中国人了解日本的必读著作。王氏甚至因此去庐山为蒋中正讲解中日关系。
当然,今天的中国人透过原文翻译去阅读日本学者、作家的著作,可以更直接地了解日本,而不必透过中国人的著作。但当代中国人面临的困境是,了解中国比了解日本更难,尤其在中日关系的重重迷雾之中,一般人无法在自身目睹的历史进程中作出判断。
新闻界有一句老话: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易言之,没有新闻就没有历史。而中国的事实正是如此——我们只有新闻界而并无新闻,只剩下支离破碎的个体记忆。很多年后反刍的时候,才会恍然大悟,原来我们曾经历了那样的历史进程。
当下在日本所目睹的那些熟悉的事物,让我的个体记忆又变得鲜活起来,往事历历在目。过去的四十年,中日关系经历了颇多跌宕起伏,如今却被人评价为“历史上最差的时候”,民间的反日行为也再次甚嚣尘上。那么,什么是历史上最好的时候呢?中日关系又何以至此呢?
山口百惠、碑林、熊猫:蜜月期的八九十年代
1986年春天我六岁,父母带我去西安兴庆宫公园春游。那个公园里有一座汉白玉纪念碑,父亲带着我诵读碑上的两首诗,一首是阿倍仲麻吕的《望乡》:翘首望东天,神驰奈良边。三笠山顶上,想又皎月圆。
一首是李白的《哭晁卿衡》: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这两首诗我至今还能背诵。父亲给我讲了遣唐使的故事,上学时我在历史课本里又读到这个故事。
后来我才知道,我在兴庆宫公园读诗的那个春日上午,许多来自日本的工匠,正在距离兴庆宫南侧五里之遥的乐游原青龙寺,栽种一千多株樱花树。多年以后,我在日本高野山金刚峰寺的壁画里,又见到了青龙寺,那是空海大师的学法之地。跨越一千多年,中日之间的那种神奇的连接,几乎无处不在。
少年时代看动画片,有《铁臂阿童木》、《聪明的一休》、《圣斗士星矢》等,至今记忆犹新。多年前我第一次在京都闲走,在大德寺外觉得特别眼熟,似乎以前来过。原来那就是一休所在的寺院。
1984年,一部非常有名的日本电视连续剧《血疑》(赤い疑惑)在中国播出,主演为女演员山口百惠。她所穿的衣服被称为“幸子衫”,当时在中国各大城市风靡一时。山口百惠是我父亲心目中唯一的女性偶像。我小时候他还鼓励我说,长大以后去日本读大学之类的(没想到后来果然来了日本的大学)。当时最令中国观众震惊的是,在他们心目中的战败国日本,居然在1970年代,平民家庭就有抽水马桶、燃气灶、电视机这些很高级的东西,城市车水马龙,高楼鳞次栉比。
我看日本动漫的同时,也在接受另一种关于日本的叙事。这就是《地雷战》、《地道战》、《烈火金刚》几部电影。大概都看过七八遍,每年过年都会播放,有的台词也能背得出来比如那句“高,实在是高!”。那里面的日本人都是坏人。对于小孩子来说,人好像只分好人坏人两种。一休是好人、新右卫门是好人;毛利太君是坏人、何大拿是坏人,等等。
介于这两种叙事之间,于我而言,说不上对日本有什么仇恨,说有多少好感,却也谈不上。但来自爱国主义教育的素材实在是太多,各地的纪念馆,各种国产电影、小人书,以及电视上念念不忘的各式批判,至少没有增加我对日本的好感。这个国家仍然只是一个想象中的存在,略微带一点负面的感觉,但其实那是一种不自觉地向政治正确的靠拢。
1992年,我的中学语文老师要我写一篇作文,描写一组邮票:《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我是集邮的,但对这两张邮票实在无感,票面设计太差了。第一张是两只丹顶鹤,背景是富士山和长城,第二张是一个剃着“茶壶盖”的中国男孩和一个穿着和服的日本女孩相拥,背景是和平鸽。我那时只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不是日本男孩和中国女孩?老师就生气了。那篇作文后来还是没有写,因为我不知道“邦交正常化”到底是什么意思。
1992年的春天,中共总书记江泽民以及全国人大委员长万里,相继出访日本。江在日本时邀请天皇夫妇访华。这是中国政府当年尤为重视的“中日恢复邦交20周年”的大事件。我作为中学生所被要求的命题作文,不过是整个国家宣传计划中的一个小故事而已。
那一年的10月下旬,明仁天皇第一次访问中国,这不仅是日本天皇首次访华,迄今为止,也是唯一一次。明仁天皇特意去了西安,中国最悠久的古都。天皇所到之处,西安市民热情地挥手欢迎,人山人海接踵摩肩。天皇访华是当年的大事件,天天都在报纸头版头条,我记忆犹新。
天皇夫妇在西安碑林参观之时,在一面石碑上面,找到了“平成”年号的出处,是《开成石经》里《尚书大禹谟》里的话,“地平天成”。这在当年正是中日之间历史连接和邦交亲善的明证,曾被传为一段佳话。更不必说天皇在北京晚宴上表示,“曾有一段我国给中国国民带来深重苦难的不幸时期,我对此深感痛心”。
这一年,东京上野动物园的大熊猫“悠悠”和北京动物园的雄性大熊猫“陵陵”互换,悠悠回中国,陵陵则来日本。除了朝鲜之外,日本是获赠大熊猫最多的国家。整个1992年,在官方媒体的渲染下,中国沉浸于与一衣带水邻邦的真挚友谊之中。而整个九十年代,中日之间的高层互访极为频繁,几乎每年都有三四次。
1998年秋天,我负笈金陵,去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南京是一座刻着很多日本记忆的城市,我宿舍边上就是拉贝故居,他是南京大屠杀的见证者。故居破败不堪,我毕业很多年后德国西门子公司才出资修缮。大学图书馆就是战时国际红会的南京难民营,但也少有人知。从此时开始,“日本”开始频繁地在我的生活和阅读中出现。
也是在这个秋天,江泽民出访日本,虽然是他第二次访日,却是作为中国国家元首第一次访问日本。我当时对外交事务毫无概念,很多年后才明白,那一次访问之中,中日之间蜜月期各种友好亲密的表面文章,被深层次的意识形态及价值观冲突毫不留情地撕碎了。
后来揭秘的新闻报道说,日本试图在此次会谈中就侵华一事再次道歉,但条件是此后中国不得要求日本再就此事道歉,然则被中国拒绝。而“道歉”这回事,此后的十多年里,成为中国民族主义者念兹在兹的一项重要诉求。当然,这也是中国官方对日外交中主要的“抓手”。
靖国神社、教科书、U型锁:千禧年的冲撞与震荡
2001年的夏天,我在南京一家报社实习。一位在日本工作的中国人冯锦华,在靖国神社用油漆喷了“该死”二字——当下更为中国人所知的则是那个在靖国神社撒尿、涂鸦的叫做铁头的网红。当时身处南京这座在中日关系中较为敏感的城市,我在报社看到新闻时,隐约觉得哪里不对。秋天,小泉纯一郎作为首相访华,并参观了北京卢沟桥纪念馆,他也就侵华之事表示反省和道歉。但双方的芥蒂早在这一年的春天种下了。
当年春天,日本文部省放行所谓右翼倾向教科书,引发中方不满,半个月之后,退任的台湾前总统李登辉以治病为由访日,再次引起轩然大波。8月,小泉参拜靖国神社之后,即有冯锦华喷漆之事。年底,又发生日本海上保安厅在东海海域使用武器之事。
2001年中日之间接二连三的各种冲突,当时惘然,但事后看,那正是中日两国在历史问题、台湾问题、靖国问题、安全问题等各方面的立场冲撞,是在各个领域不信任对方的开始。这让即将到来的2002年蒙上一层阴影。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虽然获得中方极高规格的纪念,但在我看来,这时正是中日关系盛极而衰的拐点。
小泉在任的五年,或许因为日本国内政治的原因,对华态度逐渐强硬。日本当然是依据自己的原则处置对华外交问题,但对于中国来说,不论日本做什么,日本都与美国一样,是中国民族主义叙事中的“假想敌人”。对中国这样的政权来说,外部敌人的存在至关重要,这是现政权统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即北京政权可以保护中国人民——或者至少做出保护的样子。
毫无疑问的是,此时,官方主导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在民间亦获得相当程度的认可。在官方的仇恨叙事当中:日本右翼军国主义抬头、无意对侵华之事道歉、放弃了中日友好的外交方针、试图成为亚洲的政治大国等等。这些刻意渲染的夸大之词,在有着严密言论审查的中国,显然只能是官方塑造出来的。
还有一层原因,与中国官方交好的传统日本左翼人士,在对华交往中,为了巩固自身利益和地位,容易扩大日本右翼的实际影响力。很多在普通日本人眼里毫不起眼的右翼行动,在左翼人士的描述中被扩大化,从而让中国官方误判为那是日本的主流民意,进而极为警惕,对右翼思想的批判,亦成为意识形态宣传话语的一部分。
2002年夏天,中国的网络防火墙建成并开始试验运作,从此,很多港台及美国、日本的新闻网站就不能继续访问。我认为防火墙的效果,终于在二十年后的当下初见成效。2000年以后出生的孩子们,从来没有访问过外面世界的网站,同我们这代人相比,他们获取信息的渠道简单而可怜。如今中国大陆网络上小粉红现象更与此密切相关。(参见拙文《中国“粉红色”城市奇观与文化自信的跃迁》)。
2005年3月下旬,因为日本申请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事,中国至少有20个城市爆发了反日的游行或者示威,包括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持续多日不散。游行与示威活动期间的4月初,因为日本文部省审定扶桑社教科书之事,反日活动进入更频繁的阶段。
那一年的9月18日,我与一位上海的作家朋友在北京西单一家回转寿司店用完午饭,几个大学生在饭店门口指着我们骂:“汉奸!”朋友很愤怒,“我是满族!”我们当时都极为惊讶,因为我们成长的过程中,对日本几乎都是好感,这才没过几年,怎么吃寿司都成汉奸了?
2022年8月,苏州女生穿和服被报警,她不得不屈辱地脱下和服。很多日本人不能理解这件事。但是,在2005年的北京,吃寿司就是已经是“汉奸”了。这样的认知在中国至少持续了17年,而且还在不断被强化当中。但我认为,狭隘的民族主义不是对外的,而是对内的,是一种管治需要。
官方的反日意识形态也部分迎合了民间的反日情绪。很多中国人反日是有社会心理基础的。比如说,自日清战争以后,中国没有在战争中打赢过日本——日本是被美国打服气的。这就好比,一位血气方刚的少年在报杀父之仇的时候,发现仇人已经被他人正法,自己一身武艺反而无法亲自复仇。
此外,当年日本投降的对象是中华民国政府,并不是如今共产党的共和国政府。换句话说,日本从来没有真正向中国——中共治下的中国——认输。而日本拒绝更多的道歉,则成为北京对日外交中重要的筹码。在日本看来,中国的道歉要求犹如怨妇经年累月的哭诉。
日本很想解决历史问题,不论是面对韩国还是面对中国。可能对于韩国而言,历史问题只是外交筹码,但对中国而言,不仅是外交筹码,还是对内的思想统合工具。很遗憾,历史被工具化,这就是东亚三国之间的最大问题。
此外,中国从1992年开始的第二次改革开放,经过十年努力,终于获得进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入场券,获得了更大的世界市场,北京可能会判断对日本的贸易依存度会降低。在入世后的第八年即2010年的时候,中国超越了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成为亚洲第一,这有利于“中国崛起”的官方叙事。
对于所谓“亚洲第一”的国家地位的欣然自得,也助长了这种民族主义情绪。我们这一代成长的时候,中日友好固然是看得到的,而且因为中国当时的落后以及奋起直追的状态,我们这一代人是在“否定中国”的声浪中成长起来的。我们在日剧里看到东京的高楼大厦以及在好莱坞电影里看到纽约曼哈顿的夜景,那种羡慕和崇拜是无以言表的。
而我们的下一代人,则是在“肯定中国”的舆论环境下长大的。1999年5月美国轰炸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之后,有一份以商业民族主义为圭臬的报纸——《环球时报》——成为中国最主要的反美及反日媒体。这份报纸在审查部门的纵容之下,以挑拨反日排外情绪为能事,同时又频繁发表对“中国崛起”的溢美之词,是民族主义情绪的大本营之一。
也不仅是舆论的原因。中国城市里鳞次栉比的摩天大厦、广袤原野上穿梭不停的高速列车、每年7%的GDP增长,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这些被视为“中国崛起”的符号及暗示,令他们不必也不愿接受“中国不如发达国家”的陈词滥调了。和报纸上的“被侮辱和被损害”、“日本妄图挑战中国地位”等话语之间的巨大张力和冲突,构成新一代青年人心中挥之不去的梦魇一样的心理症结。
于是,在2012年9月15日西安爆发的反日游行中,一位叫蔡洋的河南青年,拿一把U形钢锁,砸在了一位开日本品牌汽车的车主头上。受害人颅骨被打穿,并失去行走及语言能力。蔡洋因此获刑十年,2022年8月才被刑满释放。蔡洋正是过去十年里在“中国崛起”与“民族屈辱”矛盾中辗转反侧的爱国人士的代表之一。
如对靖国神社的涂鸦一般,相似的袭击甚至也在以相同模式复制着:2024年6月24日,苏州一辆载有学生的日侨校车遭到歹徒用刀袭击,造成三人受伤,其中一人为中国籍,两人为日本籍。中国籍伤者胡友平在阻止嫌疑人犯罪过程中受伤严重,经送医抢救无效,于两日后不幸离世。
2012年8月19日深圳爆发反日游行时,正好我从香港到深圳访友,目睹了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从华强北步行到深圳体育馆。他们还掀翻了一台NISSAN(日产)的警车。在中国的反日游行中敢于对抗当局与警察,这恐怕是第一次。在广州,愤怒的人群包围了日本驻广州领事馆,并投掷石块。
日本对钓鱼岛的“国有化”,使得这一年的9月,两国关系几乎降至冰点。媒体称为“邦交正常化以来的最低点”。所谓屋漏偏逢连夜雨,在这样紧张且充满敌对的民间情绪当中,第二次安倍内阁上台了。
当年10月6日,我小时候常去看的西安兴庆宫公园阿倍仲麻吕纪念碑,被人泼墨破坏。这犹如一个令人不安的巨大隐喻。
这一年,正逢中日建交四十周年。
在“爆卖”与反日间的中国人
2012年年底,我从香港回到北京工作,却不小心又见证了一个“大时代”。那一年秋天,中国的新的领导人上任。一开始人们还抱有相当期待,认为会有所谓的政治改革。十年后再回看,这十年犹如摧枯拉朽一般。一切坚定的认为中国不断崛起并更加开放的观点,在这段时间里遭到了无情的嘲弄。
那一年,日本对中国的投资额到达历史最高点,112亿美金。此后的十年几乎呈逐年下降的态势,日本企业对中国的兴趣大大降低,尤其是新冠肆虐之后。虽然中国媒体声称中日之间是一种“政冷经热”的状态,但数字并不支持这一结论,只是媒体的报道在表面上显得很热络。
2009年元旦,由冯小刚和演员葛优合作创作的电影《非诚勿扰》上映,一年后推出续集。在这部电影里,主人公和他的爱人在北海道开始他们的爱情,并且他也计划在那里结束这段爱情。片中美丽的阿寒湖和道东地区的美景给中国观众带来了非常震撼的好奇感。
就在这一年,日本开放中国公民赴日个人旅行。但日本游真正成为风潮的,是2012年以后,并在以后逐年增加。疫情之前的2019年,赴日旅行的中国人已达900万人。有日本朋友问我说,为什么中国媒体上对日本表达出那么多的敌意,但是来吃来玩却一点都没有心理负担吗?
其实这个问题很好解释。在中国人海外旅行的选项卡上,从花销的多寡来看,首先是去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的海岸线景区,其次才是韩国、日本两个东亚国家,再次是西欧国家。日本的旅行消费水平大体上是东南亚的3-5倍。来日本的旅行的,几乎都是中国的中产以上阶层,或者说,从年龄上看,正是那些在童年时代受到日本文化影响的那一代人。这些人和近十年反日的小粉红并不是同一个人群及阶层。
我第一次来日本旅行是2014年,在奈良、冲绳、北海道,在任何日本著名的景区,都能遇到差不多同龄的中国人。在目黑川的樱花下以各种姿势拍照,一次买十包鹿饼在东大寺门口喂鹿,诸如此类。2015年6月4日,100日圆兑人民币为4.93,创下历史低谷,来自中国的游客在日本花钱看上去一点也不心疼。
起初是买相机、电饭锅、马桶盖,上野的电器店和池袋的百货店挤满了熙熙攘攘的中国游客。东京和大阪的各个店铺也开始接受中国的微信以及支付宝付款。后来,他们坐着大巴车在东京和大阪穿梭,豪掷亿万买下都内的临海公寓或者一户建住宅。有的中国富商的日本豪宅甚至就紧挨着京都御所。一到周末,浦东机场飞往关西机场的航班都是爆满。
2013年,中国境内的日本料理店大约一万间店铺,而2019年,全中国的日本料理店为7万间。就在新冠疫情的2020-2021两年间,单是深圳一个城市,日本料理增加了两千间店铺。比如长江以南最高的摩天大楼深圳平安金融中心甫一落成,即有一间高档日料店在云端开张,单次人均消费高达10万日元。
换句话说,中国民间的亲日和官方的冷淡在这几年形成鲜明的对比。而且民间的对日态度在过去的十年内分化为两个支线:即四十岁以上的中产阶级的亲日现象与二十岁左右的小粉红反日现象并存。这是值得玩味的,其根本原因在于过去二十年反日的洗脑教育已经初见成效。
在安倍晋三遇刺身故后,中国的互联网上出现了非常多奇怪的声音。一些网民为此喝彩,甚至诅咒日本再次发生类似“311地震”那样的大地震。这些匪夷所思的言论让人不寒而栗。中国互联网上的一些对日极端发言,某种程度上是被放纵的。道理很简单,如果在一个遭遇言论审查的舆论环境中,某些发言可以通行无阻,只能说明这是被允许和被鼓励的言论。
中国和日本对历史态度的问题正好相反。安倍在世时曾经表示过,绝不能让下一代背负历史问题的包袱。但中国政府的做作所为是,必须让下一代乃至世世代代牢记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中国年轻一代的网民,可能必须忘记贵州在2022年9月18日因为转运隔离而发生的大型车祸,但是必须牢记1931年的9月18日的沈阳。
很明显,历史就是一种控制当下的手段,中日间的历史被中方严重工具化了。一方面当然可以持续以历史问题为由,遏制日本的国家正常化诉求。但更重要的,历史问题是中国政府为了实施国内的思想控制而刻意设置的议题,就像中国互联网上所调侃的那样:“仇日是中国人的出厂设置”。
半藤一利在描述1941年秋天日本的国内舆论时这样说:“各式各样反英反美的讯息在国内到处流窜,巧妙地煽动国民的好战热潮。”(半藤一利《真珠湾の日》)中国当下对日本称不上好战,顶多算对台湾好战,但对日对美的仇恨宣传是无处不在的。而且短期之内完全看不到好转的任何可能。
由于言论自由的社会与言论管制的社会之间存在天壤之别的信息差,中国一般民众无法了解到中日之间的历史真相和细节,只能被动地接受媒体和网络上被放纵的谣言、谎言,那么他们无法心平气和地去接受中日交流这件事。所以目前存在这样一种极大的可能:中日之间只要增进交流,那么所引发的不愉快事件只会更多。不久前去世的著名记者、日经编辑委员村山宏先生便是持这一看法。
前不久发生的靖国神社被红漆涂上toilet的事件,正是村山宏先生这一观点的明证。从冯锦华到铁头,过去二十三年了,我一时之间都觉得无法描述这类现象。当然,我相信冯锦华是真诚的,那时候没有流量驱动这回事。
我看过很多中国人谈日本的文章,很多人还是北京和上海的“日本通”,但他们也完全无法理解日本深层次的国民心态。对我触发很大的一句话来自丸山真男先生:“自日清战争以后至现在的100年(1995年),日本便一直是亚洲的头号国家,以1945年的战败把日本历史分为战前战后,无益于理解日本历史。(大意)”但是从一般中国人的角度,是完全无法理解这句话的。不过,即便是亲如兄弟一般的朋友,都很难真正了解彼此,何况是两个历史交织的邻国呢。
末记:明月不归沉碧海
回顾过去四十年中国的道路,“改革开放”是一个颇能迷惑人的词汇。北京借着两次的改革开放以及加入世贸组织,建立了同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间密切的关系,并创造了从2002年到2012年之间骄傲的“黄金十年”。经过四十年的发展,他们总结了相当多的经验,有资金、有技术、有高超的能力继续维持高压管制,并且在意识形态上越来越以民族主义及狭隘的爱国主义为圭臬。
从1998年的江泽民访日到1999年的南联盟大使馆事件,中国对外部世界开始警惕起来,担心过度开放和及全球化会给中国带来政治危机,犹如十年前的六四那样。因而在加入世贸组织的第二年,便建立了所谓的“大防火墙”。此后并未实现入世的承诺,在嵌入全球经济之后,又在意识形态上与普世价值为敌。
是故,中国在对美及对日外交上此后呈现出来的警惕以及敌视的态度,完全是可以依据其管治逻辑去解释的。不论是华尔街、国会山或者是霞关,都曾经以一个虚假的对中国的期待作为对华政策的主轴,认为中国的发展进路是线性的、不断往上的,中国会不断保持开放姿态,这样的判断如今看来是错误的。
历史不会一直是进步的。从中国历史的经验看,反反复复的事情太多。当年义和团领袖朱红灯也是带着农民在山东推倒圣诞树及火烧教堂的。就像如今,在和服的起源地苏州,穿和服竟然会被警方问话并且被强制脱掉;安倍晋三去世的时候,中国国内互联网上一片欢腾之词,这在八九十年代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四十年来,其实中日之间积累了大量的交流经验,从生产、服务、到学术研究,本可以成为亚洲国家应对新纪元的良好伙伴。但事与愿违,让人扼腕而叹。我对未来的中日友好也不抱希望,心境犹如文首李白诗中所言:明月不归沉碧海。
(歪脑的专栏、评论和分析文章均属文章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