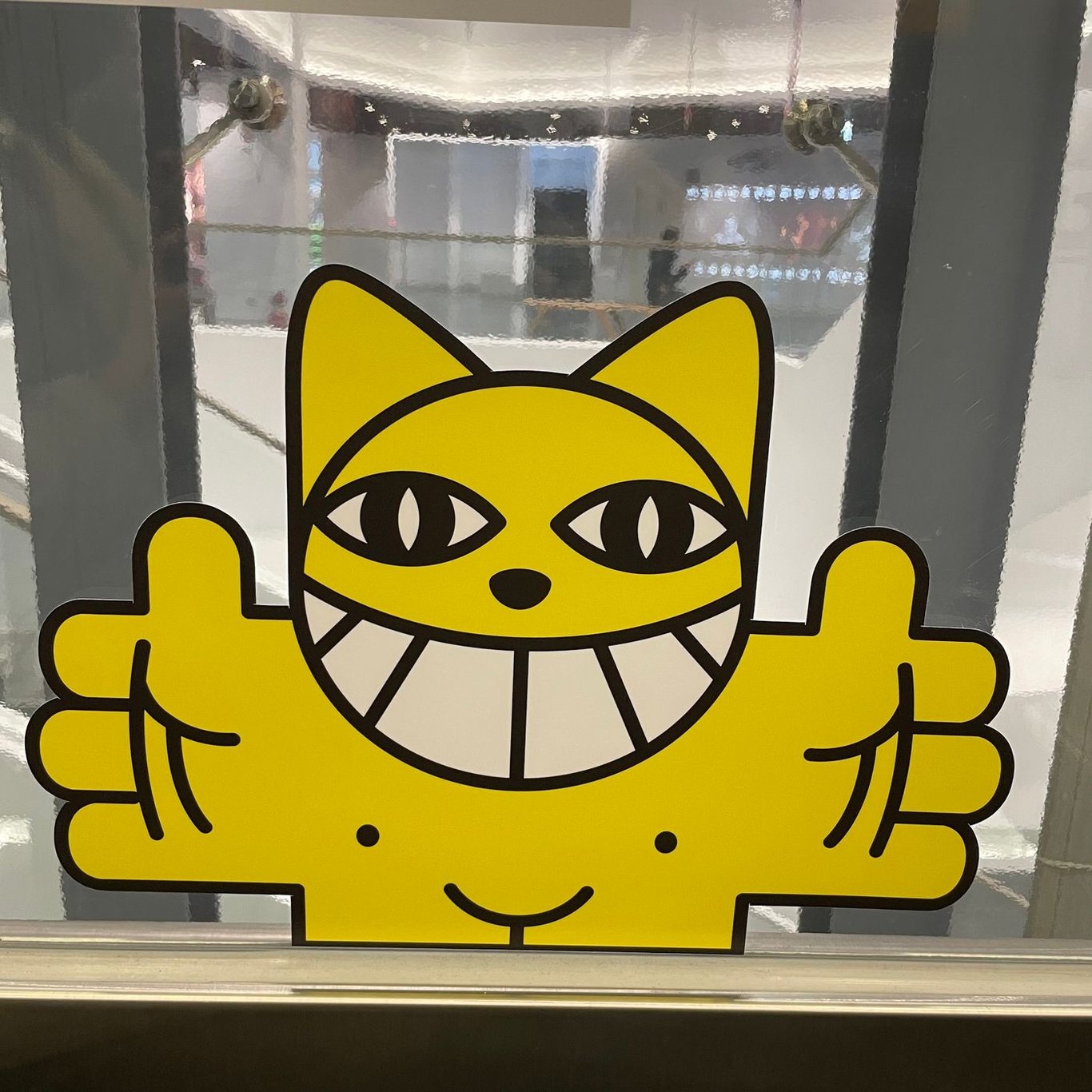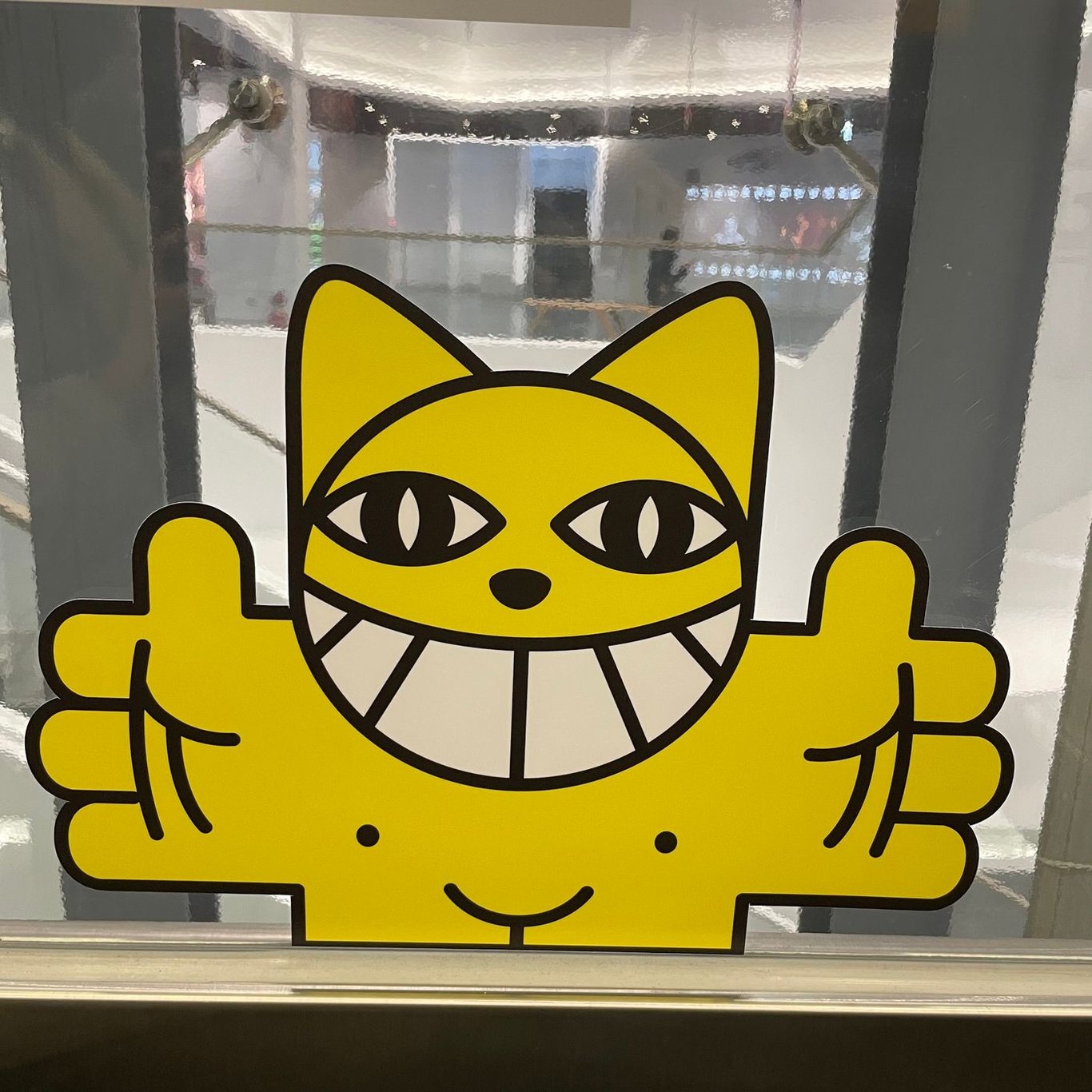年近半百的母亲决定开始工作
一
今年大年初一的那天早上,我问母亲在做什么,本以为她会跟着父亲回奶奶家过年,没想到她告诉我自己正在上线上培训课,然后拍了张照片发给我。我猜她肯定在朋友圈分享了这件事,果不其然,还是那张照片,文案是:“园所放假,我不放假,大年初一,坚持学习。2024深耕自己,让自己越来越优秀。”
我噗嗤一声笑了,这条朋友圈够感人也够矫情,母亲还是那个爱面子的母亲。我时常觉得母亲对工作的热爱像是在表演,因为用力过猛所以显得矫情。但如果这矫情从我读大学到现在,持续了十年,那就不能称为“矫情”了。
母亲从事幼教行业已经有十年了,从一个刚入门的幼儿教师,做到现在的民办幼儿园园长。她喜欢跟别人谈论自己的工作,常常把“我现在圆了自己的教师梦,觉得自己活得特别充实,特别有成就感”这句话挂在嘴边。说话的时候她的眼睛闪闪发光,就像满天繁星一样耀眼。
刚开始做幼儿教师的时候,她要带领小朋友们排练儿童节节目,早早地从寒假就开始准备了。那年她48岁,比不上那些年轻漂亮的老师们,招小孩子喜欢,学东西又快。“我要笨鸟先飞早入林”,她花费几天时间在网上浏览幼儿舞蹈视频,挑挑拣拣,选出最合意的两首。
母亲的节奏感和肢体协调能力都不好,自己一个人拿不下一首歌,就抓着我帮她顺节奏,卡鼓点,以及排练舞蹈动作。整支舞我都学会了,她还卡在开头部分的切分音,怎么都卡不进节奏里。我渐渐失去耐心,留她一个人坐在电脑前,一遍遍地听音乐数拍子,然后再跟着伴奏跳舞。
她对待工作任务有股执拗的劲头,相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真理,不怕苦累也不怕麻烦,真心实意地花费时间去做到最好,就算是一支简单的舞蹈,她也要想着在道具上玩点花样。当年她所在的单位组织了一场演讲比赛,从写稿、改稿到纠正普通话发音和加肢体动作,她足足准备了一个月,每天晚饭后对着镜子练习,最终她拿了奖,赢回一张棉被。
对于见过世面的人来说,乡镇幼儿园的诸般事宜看起来都不那么规范,不是所有的老师都有幼教资格证书,园里没有完备的游乐设施,各项管理制度也没有那么科学,每年的文艺汇演更像个土气的草台班子。家长把孩子送进幼儿园并不期盼他们能学到什么知识,或者增长什么技能,而只是把照顾孩子的职责暂时扔给幼儿园老师而已。
但母亲非常在意这份工作,她认真地挑选节目、排练舞蹈,用心地写教案、上课、批改作业,放学后热情地拉着家长们聊天。别的老师不愿意干的脏活累活,她却照单全收,比如给小孩子擦屁股,帮他们换尿湿的棉裤,每天早起跟车接孩子。
她的世界里没有职场的勾心斗角和尔虞我诈,没有甩锅接盘的概念,没有对付出和收益的斤斤计较。她真心喜欢孩子,热爱教师职业,就不太理会那些不重要的东西。
“有次一个小朋友一直哭,说身上有虫在咬她,我里里外外检查了个遍都没发现哪里有虫。最后我想了个办法,假装从她衣服里抓了一只虫,然后当着她的面踩死了,她马上就不哭了。”
我暗暗称奇,没想到母亲竟然懂得如何巧用心理暗示,她并不像我想得那样愚笨。
二
老板看中了她的能力和责任心,三年后提拔她做代理园长,放心地将整个幼儿园的运营交给了她。母亲的工资涨了一倍,逢年过节老板都要给她包个大红包,她非常开心。母亲也没有让老板失望,幼儿园的招生情况越来越好,最好的时候有200多个孩子入园,而彼时的公办幼儿园只有50多个孩子。
自从成了一名园长,她的工作不再是教学和排练节目了,园里的大小事情都要她操心,孩子们的安全问题,伙食改善,引进素质教育课,策划活动,每年两次的招生,定期家访,管理园内老师,跟教育系统的官员对接工作,还要挨家挨户地索要拖欠的学费。
每年放寒假前是招生的大好时机,光秃秃的乡间土路上,父亲开车载着她在各村各户间奔走。她要穿上最好看的衣服,蹬上高跟鞋,化好淡妆,用假发片遮住她头顶越来越多的白发。这让她觉得自信,也是她的骄傲,她看重自己作为园长的身份,一定要仪态体面地出现在众人面前。
她在家长面前侃侃而谈,从伙食夸到师资,再夸到教学亮点,她脾气急躁,说话时喜欢拧着眉心,扯着自己的大嗓门,即使哑了也不在所不惜,自信得像是在吵一场必胜的架。
那天她去索要拖欠的学费,一个人站在院里,从下午说到了天擦黑,孩子的母亲一直低头玩手机,只当她这个人不存在,母亲丝毫不觉得尴尬,最后孩子的爷爷交了学费。
母亲的工作没有那么多弯弯绕绕,幼儿园能提供更好的教学和服务,就是竞争优势,能招到学生就是胜利。面对北方粗粝的农民,她要大剌剌地说话做事,搞虚与委蛇那一套没有用。
我想到母亲跟我讲过的,她小时候去地里掰苞谷的场景。站在北方青中带黄的玉米地里,人得全副武装,然后麻溜地钻进去,一趟一趟地掰棒子,掰完棒子要赶紧剥皮晾晒,任何一点的迟疑都会拖慢进度,那些想象中的忸怩和困难就像青天白日下玉米叶上的露珠,一转眼就没了。
对待工作,母亲有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年纪越来越大,要趁眼睛还行多学点东西,已有的知识不足以支撑她的工作,于是她积极地去参加培训,内容有园长管理方法、儿童心理学、幼儿教育、活动策划……
翻开她的朋友圈,每一条动态都是关于幼儿园的,小朋友们吃了什么饭,学了什么手工课,做了什么游戏,园里举办了什么活动,她参加培训的感悟和分享,她对幼教行业的深厚感情,就连小朋友拉裤子老师帮忙清理这种小事也要发在朋友圈里。
她嫌老师给小朋友们拍的视频不好看,就自学了视频剪辑课,自己拍视频,再插入动画和音乐。我毫不客气地嘲笑她太过傻气,大小事情都要亲力亲为,这样当园长迟早要把自己累出毛病。但是我能感受到之前二十年她从未有过的开心和充实,像是放置多年的橡皮艇突然充满了气,即将开启一场惊心动魄的远行。
“今天培训我上台做了演讲,台下响起雷鸣般的掌声,从写稿到排练都是我一个人完成的,我觉得自己讲得真棒。”
“我做的元旦活动方案,其他园长都在借鉴学习。”
她爱慕虚荣,喜欢夸耀自己的成绩,做了三分要说成七分,做了七分要说成十分,团队成绩要强调自己的那一份功劳,别人帮她改的稿子要说成是自己写的。她从不觉得羞耻,被戳穿了就嘿嘿两声笑过去。但是不能当着别人的面戳穿她,有次我在外人面前说漏了嘴,回家后被她痛骂了一顿,她到底是好面子的人。
我有些不以为意,那些培训内容无非是从网络上搜罗来的各种工具性教程,被培训机构简单包装一下就拿出来售卖,有些课程更是洗脑工具包,不断重复“我感恩父母老师家长”的空洞词句,那些课程更像是流量时代的速成指南,教你怎么打造幼儿园品牌,吸引更多的生源,简单粗暴却有用。
母亲第一次接触这些东西,将其视若珍宝,郑重地将培训讲师的话抄写在笔记本上,照本宣科地将它运用在幼儿园的运营上,今天举办一个感恩节活动,明天搞个分享沙龙,还不忘录视频发在朋友圈和短视频账号,为幼儿园做推广宣传,忙得不亦乐乎。
她办活动写讲话稿时喜欢用些老掉牙又煽情的排比句,读起来让人忍俊不禁。
“不论是赤日炎炎的盛夏,还是滴水成冰的寒冬,我都奔走在幼教的道路上。幼教是我一生挚爱的事业,是我的指路明灯,是我的价值源泉。”
三
当我回溯母亲过往三十年的经历时,我似乎明白了为什么她对待这份工作有股过于热情的傻劲。
母亲只读完了高中,没考上大学,就接替了我姥爷的工作,成为乡镇道班的一名厨师,兼任出纳,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去县城的公家单位报销账目。那时她的工资还不错,时不时会从县城捎带回来好吃的零食、漂亮的衣服和新奇的玩具,这让我在其他小朋友面前赚足了面子。
很快她所在的公家单位转企改制,镇上的道班被合并到了别的镇,不得已她只能去其他乡镇工作。这让她陷入了两难,那时交通不便,最主要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车,两个镇之间的公交车程大概有一个小时,她不能每天往返,只能每周回家一次。
我年龄尚小需要有人照顾,但父亲平时忙于工作,无暇顾及我,他不会做饭,基本在学校的食堂凑合,有段时间我每天在邻居叔叔阿姨家蹭饭吃。母亲尝试过一段时间在别的镇上班,趁周末回家帮我改善伙食,但她终究还是担心我吃不好发育不良,便决定留在家里照顾我。
我读小学那几年,逢年过节她都要打只新鲜的羊腿去给领导送礼。领导家住县城,送礼那天要早早地起床,赶城乡公交去县城。柏油马路还没有修好,大雨过后,土路上满是纵横交错的深坑,人坐在车里,左右摇晃,像是在坐花轿熬。我吐得厉害,哭闹不止,两个小时的车程尽是煎熬,母亲哄我说,到了县城就给我买胡辣汤和小笼包。
母亲叮嘱我见到领导要有礼貌,要叫叔叔好,没问话的时候就安静地坐着。我像是下一秒要上台表演一样,紧张得手心都出了汗,怯生生地叫人。领导坐在沙发上,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视看,母亲像是对着空旷的山谷说话,许久才能听到回声。
我的注意力被一个年长我的大姐姐吸引,她一会儿对着空气大喊大叫,一会儿跑出去盯着天空看,一会儿又跑进屋里躲起来。母亲突然拉起我的手,我不明所以地看着她,她目光恻恻地看了我一眼,然后又乞求地望向领导。领导转头瞟了我一眼,叹了口气。就这样来回磨了几次,领导终于答应她暂时留在家里,但每个月要上几天班,工资只能发一半。
我读初中后,母亲重返工作岗位,但她错过了单位发展最快的那几年,也错过了她的事业发展黄金期。同期入职的同事大多已经当上了中层领导,唯独她还在基层道班做着最基础的工作,拿着最低的工资。
我去市里读高中,住不惯学校宿舍,母亲前来陪读,我们租房住。单位无法再忍受母亲不上班却领工资的无理做法,于是停发了她的工资。考虑到在原单位已无发展的希望,再耗下去没有意义,她在我高三那年办理了内退手续,退休金只有正常达龄退休金的一半。父亲的工资不足以支撑两处生活的开销,母亲说那几年家里总是缺钱花,拿着工资卡去银行取工资,却被工作人员告知账户余额为零,她尴尬得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我去外地读大学后,她的时间多了起来,开始打工挣钱。她做过饭馆帮厨和服务员,大冬天手泡在冷水里洗菜刷锅洗碗,坐月子时落下的风湿病复发了,手腕疼得她夜里睡不着觉。后来她又去做了服装卖场的导购,她爱跟人拉家常,也会给人挑衣服,忙起来甚至顾不上吃饭。她的销售业绩一直不错,但卖场开了一段时间就关门了,母亲又失业了。
恰逢镇上的公办幼儿园招聘保育员,母亲前去应聘,但做了不久又因为没有相关资格证书被辞退了。生活没有给她这样的女性太多的机会,她像是在一条没有边际的大河里游泳,她失去了方向,只能拼命地往前游,一旦停下来就会沉下去,她只能抓住她能看到的任何可以救命的东西。
后来镇上有家规模很小的民办幼儿园招聘幼儿教师,门槛低但工资也低,母亲没有嫌弃,她这辈子就想当老师,这下终于圆梦了。母亲在这家幼儿园一干就是近十年,把一家小幼儿园做成了一家大幼儿园,这是她人生中的高光时刻。
上半辈子她困在捉襟见肘的经济里,困在家庭和工作的两难选择里,困在厨房和一日三餐里,如今她有了事业,有了钱,有了时间,她还拥有了许多之前想都不敢想的漂亮裙子、旗袍和羽绒服。她不必再对谁俯首称臣,也不必再看谁的脸色,在自己建立的王国里,她就是自己的王。
四
也许她会在这家幼儿园一直工作到自己垂垂老去,但生活总是给她出难题。去年年初,老板忘了及时更新幼儿园牌照,批评通告挂在了工作群。这几年母亲所在的幼儿园一家独大,招来同行嫉妒,几家竞争对手因此拿捏到了把柄,四处散发传单,说母亲所在的幼儿园是非法运营的。原先的幼儿园办不下去了,老板盘下了一家即将倒闭的新幼儿园,之前辛苦维系的生源流失了大半,一切都要从零开始了。
那段时间,母亲瘦得像变了一个人,两颊凹陷,两条竹竿一样的腿更细了。她每天起得更早,下班更晚,重新修整了几近破败的幼儿园,升级了幼儿园的服务,重新招聘和招生。她有空便在村里奔波,试图劝回离开的孩子们。一年过去了,幼儿园终于步入了正轨,虽然新园的地理位置大不如前,但还是招到了不少学生,母亲的体重也慢慢恢复了。
当母亲告诉我今年大年初一她在上网课时,我有些疑惑,按照往年的惯例,每年过年那几天,父亲兄弟四人的家庭必要齐聚奶奶家,缺席的人会被大家说闲话,父亲也会不高兴甩脸色看,加上母亲是家里做饭最好吃的掌勺大厨,她是万万不能缺席的。
90年代中期,摩托车在乡镇还没普及,我刚上幼儿园。大年三十那天,跟奶奶住同村的二叔会开着那辆红色的手扶拖拉机来镇上接我们。我们把当时家里唯一的一台电视机搬上后面的平板车,置办的年货,在奶奶家过夜用的被褥和生活用品一并搬上去,隆重得像是搬家一样。
拖拉机突突突地行驶在乡间小道上,我躲在温暖的被窝里,看嫩绿的麦田缓缓地往后退去,幼小的心里升起一种踏实的感觉。小时候我喜欢在奶奶家过年,喜欢凌晨十二点准时响起的此起彼伏的鞭炮声,喜欢新年的第一缕阳光洒在那扇老旧木窗上,喜欢在雪堆里寻找还未燃放的鞭炮。
但母亲告诉我她并不喜欢在奶奶家过年,她择床,夜里睡不好,十几口人挤在一间屋子里,吵得人心烦,准备一大家子的饭菜累得她腰酸背痛。更难受的是,她不会哄人开心,奶奶也不待见她,言语中时常讥讽她。
近些年情况有了变化,他们只在大年三十和初一回奶奶家,吃顿中午饭就走了,母亲好几年都没再做掌勺大厨了,偶尔帮着大家包包饺子。想不想回奶奶家过年,回去了呆多久,全凭母亲的心意,父亲不敢再说什么,他像头衰老的牛,不敢再对着母亲颐指气使。
我想象着,新年第一天,她自己一个人在家,邻居们都回家过年了,屋子开着地暖,安静又暖和。像是在虔诚地进行某项仪式,她拉开书房的窗帘,戴上自己的老花镜,摊开笔记本,用鼠标点击电脑屏幕的播放键,开始了一天的学习。外面大雪纷飞,她的神情专注,天大的事情也不能搅扰了她。
她是我的母亲,一辈子都在用力生活的女人。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