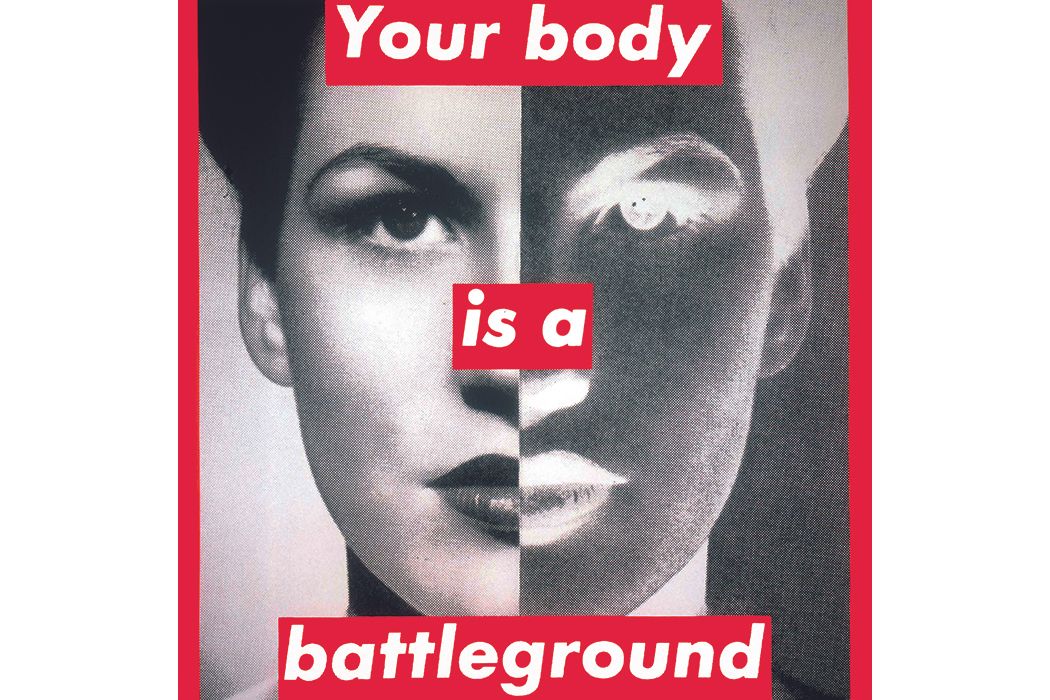瘟疫年纪事 | 这世上的路我们终究要再走一遍

1. 这个世界没有人类挺好的
在湾区的客居生活进入第三个月。后院的柚子落了烂了,月季花开了又谢了,早晨被热醒的次数多了,留海又长得遮眼睛了,冬末时带来的衣服也不再适合初夏穿。除此之外,日复一日毫无波澜地流过去,好像从未有意外。
小西本来买了5月初的机票回国,我还寻思着到时得准备收拾东西回纽约,但因为国内大幅压缩回国航班的五个一政策,她的机票都被取消,回国时间又调整到了5月底,于是我又得了个缓期执行。
但这整个春天已经荒废了,真是糟透了。
一直在观望着要回国的小老虎不出所料仍然滞留在日本,但我偶尔刷到他的微博看他游荡在山巅和海边,景色介于触手可及和杳无音信之间,他也仿佛一如既往地自得其乐,就觉得好歹我所知的世界的一角尚未崩坏。
幸好,不是所有人都在work from home、居家健身、看书、刷剧和听讲座。
大概三个星期前,我们又通了个话,他说:“和上次通话比起来,我感觉你颓废了很多。”然后他便怂恿我出门去海边走走,说:“只要你一去到那里,你立马就知道自己是谁了。”
我想,我们获取能量的方式有相似之处,虽然输出能量的方式不太一样,小老虎说他想记录一些事但不知道怎么下笔,我当然也不知道怎么创作一首歌。
第二天我就和小西就出门了,她在网上卖掉了一个东西,要亲自去送货,我从床上爬起来,十五分钟之内就穿戴好了行头。
加州的艳阳天把一切事物都照得鲜亮,也像激活了你的眼睛,好像看什么都更加深刻,细节毫发毕现,争相引人注目。小西说她都快忘记怎么开车了,好在公路上车流稀疏,畅通无阻。一路上我根本舍不得低下头玩手机,东张西望,连街边的树都老看不过来。
阳光晒到车里的皮革配件时的味道,车窗缝里吹进来的暖风的味道,甚至手上的防晒霜所注解的夏日味道,都令人心旌荡漾。
我望着湛蓝的天空发呆,阳光透过树影不断闪烁,像胶片电影的空白镜头般滑过,眼睛突然就湿润了。
我果然还是更喜欢这个世界。政治只是人类社会运作的一种方式,但世界远远大于它,不管是外部世界还是一个人的内心世界。
如果不是这次疫情,我现在应该不是去了日本就是欧洲。旅行早已是我生命不可分割的部分,至少从11年开始,我每年都有几个月时间外出游荡,18年后才变很少,因为没钱关注点转向了社会。但在19年底,再上路的冲动越来越强烈,也早已设想好怎样一边工作一边行走。
我想去到各种地方,和活生生的人见面、说话,不是在线上。在线上我没法交流,所以基于网络的人际活跃度已经降到冰点。
我对所有即时信息越来越失去兴趣,我不关心疫情的数字,也不再觉得新闻重要,这可能是丧失能动性后症状的进一步加剧,当公共空间消失,每个人都被迫更多地面对自我和关注内心,但关注并不一定产生正面效应,一个封闭的内心其实极易自我消耗。
在这种张力令人筋疲力尽的时候,外出真的变成一个很及时的出口。
我和小西在一个plaza找到了来接头的买主,在互相走近的过程中我们都同时戴好了口罩和一次性手套。
能够感受到他很想和我们多聊几句——这些天是个人都憋坏了。交易完后我们走去不远处的一个露天菜市场——这里竟然开着一个露天菜市场,商家们把蔬菜、水果和熟食产品摆在摊位上售卖。新鲜的花菜、油菜、菠菜、萝卜、西红柿、橙子、草莓、柚子……我们激动万分,边买边各种摆拍,像逛第五大道一样隆重。
买完菜之后,我提议去公园里走走。湾区的优点就是附近有山有海,开车走不了多远,就能接触到足够野味的自然景观。
我们去了一个湿地公园,在临近的地方,车行道被政府的路障阻断了,于是我们把车停在路边,拿了刚买的吃的步行进去。
踏着空旷的车行道进入一大片茂盛的杂草丛中,小径的另一侧,视线无比开阔,越过沼泽地,能够触及地平线上淡蓝色的远山。晴空万里无云,几声水鸟的鸣叫和呼呼的风声更显出空间的宁静致远。
那一刻觉得,这个世界没有人类挺好的。
我们不是从自己的空间里撤退,我们只是交还了本不属于我们的空间。没有人类,其他的生物就可以好好活了。想到这里,原本希望自己早日回归,就变成了希望自己的缺席会让它们得到足够的喘息时间。
我想起了那只奔跑在武汉二环线快车道上的野猪,还有世界各地进入城市活动的野生动物,山羊、猴子、狐狸、美洲狮……一些大城市的二氧化碳排放、空气质量和水质也因为大面积停工而明显改善,尽管这都是暂时的。
就像一个段子说:人类是地球的病毒,而病毒是地球的免疫系统。自然的智慧教给我们的,是辩证看待这个复杂的世界的重要性。这意味着如何用平衡、制衡和超越性的眼光来处理我们和“他者”的关系,是我们摆脱暴力链条的关键。如果为所欲为的占有、剥削和攫取就是我们爱的方式,那我们并没有准备好再次进入这个世界,而并不是这个世界在拒绝和排除我们。

2. 女权伙伴的婚礼
4月底的时候,我一个同样在湾区避难的纽约朋友Zoe准备和男友结婚,但因为加州的courthouse不营业,所以他们申请了DIY,想找我当下证婚人,像抓住救命稻草一般抓住每一次出门搞事的机会的我欣然同意。
我们认识,是因为同在女权和留学生的交叉圈子里,有两三个经常活跃的共同群,又是老乡,后来便发展成了线下的交情。我记得19年冬天的时候,我才在706纽约的聚会里见到她带他的男朋友来,说那天是他们在一起的第一天,没想到再见面时两人就结婚了。
我无比眷恋纽约,也是因为那里一直有很多华人女权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泛民主派青年,那是我的社群,我的同温层,这是湾区永远替代不了的。
正好在那几天,国内爆出了鲍毓明性侵“养女”的事件,一些女权主义者在网上征集签名并给加州律协写投诉信,呼吁取消鲍毓明的加州执业律师资格,Zoe也积极参与其中。她和另外一个女权伙伴顺遥找到我,说可以一起去邮局把投诉材料寄给加州律协。最后我们便决定两件事一起做,先找个地方为她举行结婚仪式,然后再去寄信。
为了躲避人群和病毒,当天的仪式是在顺遥居住的一片山头上举行的,山上能够俯瞰圣何塞。顺遥是念誓词的主婚人,我则负责用手机录视频。这场婚礼就只有我们四个人,大家一边进行一边打趣,随意却又不失亲密感。两位新人穿着日常的大红色情侣T恤和休闲裤,趁着背后的绿树青山也特别好看。除此之外没有什么特别的装备,但Zoe却十分周到地给我们准备了喜糖和红包。
就是这么简单的仪式,我也看得很感动,为两个客居异国的年轻人能够没有漫长折腾、没有反复游移地确认了彼此。
想起了我那场恍若隔世的婚礼,是国内喜闻乐见的风格,排场巨大,像个布景奢华的剧场,我们都是盛装的演员。今天变成无产阶级的我却感到一点羞愧,因为把资源浪费在了社会共谋的虚幻价值感上。
相比之下,离婚对我来说更意义重大,那应该是我第一次反抗命运。但我不后悔与爱过的人共度了一段人生,也不介意在年轻的时候排练了一遍主流安排给我的剧本,然后明白这不过如此。并不是它不好,而是二十几岁便到站的人生终点,再好也是个终点。

仪式结束后我们就地填好了申请结婚证书的文件,我也在上面签了证婚人的名字。之后他们需要把文件寄去当地的courthouse,才算注册成功。据说在疫情期间,为了满足民众对注册结婚的需求,很多地方政府都推出DIY选项,只要在网上交一百多美金,就能收到邮寄来的相关材料,“相当于借用一次政府机构的公权力来自主认证结婚。”顺遥说。
结完婚后大家迅速切换成了activist的模式,去了邮局打听打印、邮寄投诉书的事。不得不说美国的打印也太贵了,算了算一百七十多页材料的成本,不如去超市买一台打印机合算。
我们买好了打印机,偷闲去Zoe家吃了顿火锅(跟老乡一起吃火锅太省力了,什么都合口味),下午又去了邮局。在邮局门口,我们举出了顺遥做的几张标语,上面写着声援幸存者李星星、呼吁取消鲍毓明加州律师资格的口号,然后录了一段视频,介绍了志愿者们发起这个活动的诉求。

后来,这个视频在微博上被转发了近三万条,虽然我只充当了一个人型标语版,所有的工作都是志愿者们做的,但我很高兴自己能够被包容在内。
在我这几年资历尚浅的社会经验中,女权主义者是我见过的最有行动力、动员力、连接感和群众基础(并且尚有活动空间)的社会运动主体了,他们对强权的反抗是日常的,是普遍的。除此之外,大陆没有其他任何的社群有这样的能量,它的重要性值得被进一步看见和认可。
3. 自我与公共
16年来美国读书后,我也从私人生活走向了公共生活。是女权主义陪伴我完成了这个重要的蜕变——作为一种身份政治(在起步阶段),你无法想象它可以为一个脱离体制的女性提供多么关键的支持。
“个人的即政治的。”是女权主义对我影响至深的启发。
那段时间里我坚信,人生必须要向外寻找答案。内心世界大多是外部世界的反映而已,没有必要拘泥于前者,在向外行动的过程中,个体的很多问题自会迎刃而解。
可是久而久之,随着我认识到自由的真相,目睹公共空间的堕落,我又开始关注人的内心世界,并且不止一次呼吁大家向内看,去看见自己,进而从这片荒芜、暴力的土壤中解脱。
朋友嘉琪曾对我说:“有的人有望远镜看世界,但没有放大镜看自己;有的人有放大镜看自己,但没有望远镜看世界。你是同时拥有望远镜和放大镜的人。”
这就是我在自我和他者的反复交往中的洞悉:人的自我和公共性是相辅相成、又此消彼长,但终究不可分割的关系。你希望被一个怎样的世界对待,都会指向你希望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反之亦然。
可能瘟疫对我造成的影响并不是事故,而是对我早已开启的微妙变化的激发。我曾经非常忠于自己的政治身份,熟悉公共生活,但现在,政治变成了一个面向,而我更想离开那些快速变化着的表象,去了解人类本质的问题,这些问题既根植于个体,又在所有人的相似之中。
在湾区迄今两个多月的居家生活中,我恢复了对于日常的、私人生活的书写,就像我从初中时开始记日记那样。把重点转移到自己身上,一开始让我有点困惑,会怀疑我是否放弃了抵抗,转而只求个人的解脱?毕竟我曾经如此热衷参与公共事务,那是我很大一部分价值所在。
但是不书写,实在不知道如何纾解内心的苦闷。国内疫情高峰期间,包括我在内的海外朋友每天都在关注国内的情况,日夜不停,连时差都被无缝衔接,作息完全跟着东八区的节奏在走,我们会为每一个不公平的操作愤怒、为每一个悲惨的罹难者悲伤。但是等下半场疫情转移到海外,我们看到的国内信息大部分是宣传机器裹挟着民粹对国外抗疫的鄙视和嘲笑,连留学生群体都整个被划为“投毒”的敌人。
美国疫情控制的失败和感染数字的居高不下,我们也吐槽了不少。但真的,没人在乎我们怎么想,我们只是政治的素材。当然,人或多或少都会被政治当成素材,但在一个执政合法性不来自于人的地方,这显得更加荒诞。
我知道很多留学生(和中国的年轻人)是在这次疫情里遭受洗礼的,从而由衷生发出“原来我们这一代也会承受苦难”的感慨,但对于我来说,这一刻来得更早。去年夏天的香港运动给我带来的心理阴影才是决定性的,这次疫情反而让我恢复了一点对国人的信心,特别是那些积极互助,不懈问责的人,重建了我们的连接感。
我曾希望这次灾难会推进一些结构上的变革,然而一如既往,它再次被谱写成胜利,追责的声音几乎都烟消云散。但是,若它多少叫醒了一些人,那代价也不算是完全白费了。
就像之前说的,人的自我和公共性是不可分割的。反抗者天然会注意到她们的自我,因为叫醒她们的不是红药丸,而是在和体制碰撞时因痛苦而复苏的人性。但很快,这个自我就会不断折磨她们,因为她们只会从反抗中接收到外界变本加厉的负反馈,被污名、被割席、被边缘、被网暴、被维稳……直至伤害无法承受。但体制(以及体制内的螺丝钉)从不会注意到自我和自己的内心问题,体制的作用就是以一大堆章程制度、繁文缛节、宏大叙事来架空、剥离人们朴素的道德和人性。所以,他们只用说出“我只是在履行职责”、“这不过是约定俗成”,就可以卸下一切作为人类的道德义务,就可以让我们赦免他们的罪,就可以让人们以为道德和人性的妥协是理所当然的。
这就是为什么反抗者总是千疮百孔,歇斯底里,而体制永远完美无瑕,游刃有余。
对于反抗者来说,她的心和她的行动是同在的,这就是一个真实的人的回归,否则反抗何以生发?何以凭借?一个真实的人必然是更脆弱的人,因为所有的伤害都靠她以自我来承受,袖手旁观的社会没有资格指责这种脆弱。
但重要的是,这一切都指向于:在和体制差距悬殊的张力中,个体如何建立起内心防线?这一定涉及到我们如何去过自己的内心生活的问题,也是我试图通过写作来应对的问题。

4. 不要当这个对我们施暴的世界的帮凶。
小西做着国内外两份工作,从早到晚都有开不完的会,常常到了深夜时分我已经在刷剧摸鱼了,她还在和国内的同事视频。我难以想象,长期让工作占据整个生活,她怎么承受得住呢?我连每天标准的八小时工作量都很难达到。
我刚来湾区的时候疫情还不严重,所以经常和朋友们聚在一起喝酒,但现在都在保持距离。我是个老年人,怕喝多了难受,小西就一个人喝,然后喝个宿醉,仿佛是开心的。
我应该庆幸自己还可以写作,长期隔离的生活越到后面,心理危机出现的几率就越高。
直到有一天,她喝醉了酒,不慎吃抗抑郁药过量,第二天睡了一整天,唯一一次下楼的时候,走路摇摇晃晃,眼神也飘忽不定,说看什么都是重影。第三天她虽然开始活动,但药效还没退,整个人魂不守舍,也完全不记得发生过什么了。
因为察觉到她的心理压力已经到了一个极限,刚好遇到了周末,我叫上小明跟我们一起出门去散心,也不管什么居家令了。那天天气很好,我们翻山越岭,开了近一个小时来到海边,小明特地带了个遮阳帐篷,撑开在沙滩上,刚好够坐进去三个人。
我们说要吃零食,小明便跑去附近的超市买。面朝夕阳下的大海,不禁感到心胸开阔,我和小西便聊了聊最近的感受。我问她吃药过量是怎么回事,她慢慢说:“就是喝酒的时候,突然觉得很难过,不知不觉就开始吃,药很甜,也不知道吃了多少。有那么一刻,感觉和死亡很接近,一切都不重要了。”
我知道她遭遇过很多事,累积在内心的伤痛只不过是靠时间去掩盖,但并未痊愈。敏感又富有情感的人,在这个粗暴的社会很少会幸存,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她要拼命工作填满自己,然后把快乐的配额交给酒精。
我说:“你很重要啊,你每天都做那么多事,有很多人需要你。”
“可是都没有意义。” 她躺在帐篷里,闭着眼睛轻声呢喃。
我说:“别这样说,我很羡慕你的。你还这么年轻,一个人在国外那么多年,什么都是自己努力得来的,我到现在还什么都没有呢。”
停了一下我又说:“还记得上次火人节里我对你说过什么吗?如果所有的事情都不work out,我们就重新再来一遍。但其实,我也没有自信能够做到。”
她笑了笑。我继续说:“我最近也有特别难过的时候,跌入谷底,第一次觉得连写什么都没法解救自己了。这个时候我就干脆彻底躺平,干些特别废的事,刷剧、刷微博什么的,其实就是熬时间,等着把最难过的时候熬过去,然后慢慢就会恢复一点,可以继续做正事。真的,哪怕就当个废人呢,但是不要伤害自己,不要当这个对我们施暴的世界的帮凶。”

5. 我们注定要把这世上的路再走一遍。
某种程度上说,我确实把我的人生重启了一遍,但我根本不知道这是否work out,两个月后,我连自己会在哪儿都不知道。
我特别理解小西在美国生活十多年后,也即将选择回国工作,身边能得到更多支持,也许会让她状态好起来。
我没有后悔来了美国,但也从不能说我在这里就是幸福的,甚至都不能说是自由的,没有一个自由的人会担心回到自己的祖国(或者担心回不去自己的祖国)。
这次疫情里中美互扔泥巴的丑态,可能加重了我对政治的疏离感。主义可以变来变去,道理可以正说反说,但人心永远是那点人心,人的核心需求都是一样的:爱、安全感、归属感、尊重、自由、自主……
我想起加缪在他唯一一次造访纽约的演讲里,谈论起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被血与火蹂躏的欧洲,说:“我们走了一条远路,但人类的历史说到底是人类的错误史,而不是真理史。也许真理就像幸福一样,是简单而没有历史的。”
我想,当我明白了人类的历史,就明白了我的父母为什么曾经想要把准备好的答案送到我面前。
我妈过去非常反对我参与和讨论政治,并不是因为她不赞同我的观点,而主要是出于安全考虑,她说:“你以为这些事就你知道吗?我们都明白,都经历过,有什么必要再讲?”
那时我认为这是一种亲情绑架,后来当我走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我发觉他们未必不是看穿了历史的真相——那些令人疲惫至极的斗争,那些被狂热蹉跎的青春,所有无意义的牺牲,如果换不来后代命运的改变,有什么必要再讲呢?
所以在倍感失落的时候,我心中也有挥之不去的疑问,想知道,如果他们看到了我现在在“错误史”中重蹈覆撤,会失望吗?会为我不值吗?
可是,每一代人的疑惑都在重复,但却没人可以代答,如果不上路,就无法理解。无法理解的人会活在虚幻中,找不到生命真实意义的灵魂将不得安宁。我想,这是为什么那么多人会迷失在抽象话语所建构的宏大叙事里。
为了真实地活着,哪怕我们最后抵达的不过是一开始就存在的终点,我们也注定要把这世上的路再走一遍。
湾区的山林和海岸让我深深怀念起曾经和父母长途旅行的日子,所以我最近开始写“旧世界物语”,记录我们一路上的风光和轶事。
时隔一两年的游记并不好写,我需要登录自己之前被封的微信号,逐条翻看很久以前的朋友圈,挖掘出尽量多的记忆。然后发现,我妈虽然总说自己记忆力衰退,却能够补充很多我都想不起来的细节,让这些走过的路再一次焕发新鲜感,就像他们曾在那里重获青春。
旧世界就是新冠之前的世界,它将是我们所有人的乡愁,那里很有可能保留着我们这一代人最好的时日。其实,支撑着我们与这个社会做旷日持久的缠斗的,不过是这一点私人珍藏的幸福、自由的回忆。
最后想对父母说,就算我最后也没有到达你们为我准备好的人生答案——圆满的家庭、安定的生活和一帆风顺的体制内工作。
但终点不能定义我,定义我的是寻找着、渴望着、反抗着时,所一次次重现的,身而为人的价值——那些价值虽早已存在,却时常遭到遗忘和践踏。
想起我们的旅程吧,这条道路如此漫长。沿途的一切,都让我不断感受生命本质的幸福,因为你们让我成为了一个充分发展的人,一个值得穷其风景,走去世界尽头的人。